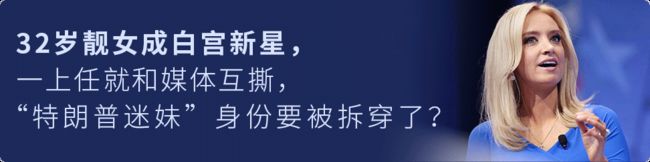专访 | 郑钧:心中的明月重新升起

30岁,他是华语摇滚的代表;40岁,遭遇中年危机;50岁,一首《青春的葬礼》唱哭“95后”。
|作者:余驰疆
很多人爱郑钧,因为他的帅,因为他的才,因为他的不羁。
高晓松早年给自己“约法三章”,不跟黄磊合照,不跟朴树合照,不跟郑钧合照。B站上一个1994年郑钧到香港演出的采访视频,他穿着牛仔的外衣,扎起蓬松的头发,鼻子高挺,嘴角斜翘,弹幕上齐刷刷:太帅了!
那个时候,人们喊他“摇滚界的木村拓哉”。
30岁,郑钧已是中国摇滚的代表人物:《赤裸裸》《灰姑娘》《回到拉萨》《私奔》《长安长安》……这些歌时至今日依然是各大选秀的必唱曲。40岁后,他有了更闹腾的世界,小说、动漫、电影一个不落,当“快男”评委有离席风波,参加亲子综艺有狼爸争议。外人觉得这些事儿跟他格格不入,他自己倒是乐在其中。
“我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5年前,《环球人物》记者第一次采访郑钧,在他家楼下的小花园里,他曾这般说道。
而今,早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人生轨迹似乎又有改变。他戒酒戒烟,打坐瑜伽,转山旅行,摇滚青年成了佛系“前浪”。这一次,他对记者说:“前半生是享受生活,是炙热的、充满贪嗔痴的岁月;后半生是享受生命,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但也特别美好。”
走到路口的瞬间
采访时郑钧正忙于爱奇艺《我是唱作人2》的作品创作。去年节目组就发过邀请,但他拒绝了,“因为对不了解的东西有抵触”。他基本不看综艺,哪怕是自己参与的。
“今年又来找,不去实在太不给面儿了,让人觉得我这人好像怎么着似的。然后周围的人也都‘忽悠’我,说这挺好的,我就来了。”
另一个原因,是他自己感觉到花在其他事上的时间太多。参加这样一个即时创作的节目,就能把写歌的问题解决了。过年期间,他写了两首新歌,就去录节目了。没有备货,意味着接下来的每个星期,他都得完成一首新作,包括构思、创作、编曲和表演整个流程。“下周要演了,这周还没写完。”
比赛胜负并不重要,借歌表达点什么才是正事。郑钧的每首都有不同主题:《刀》讲如何与尖锐的生活相处;《低空飞行》探讨对世俗成功的态度;《我算什么》则是对自己的各个社会角色的审视……
受众的反馈高潮出现在第四期,他唱了一首《青春的葬礼》。唱歌前,他在台上说:“献给晓松、老狼。”
昨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欢聚,
那更像是一场青春的葬礼。
朋友们来了哭着笑着又四散,
可你始终都没出现。
……
这期《我是唱作人2》播出几小时后,郑钧在半夜陆续收到家人、老友发来的微信,“这歌要听哭了”。很快,高晓松、老狼、那英、宋柯等十几位音乐圈明星转发,微博涌入大量留言,他这才意识到好像事有点大了。
“我第一次认真地看了微博留言,有‘95后’的小朋友,说听哭了,我觉得挺温暖的。我就重新放了一下这歌,结果把自己也听哭了。”
他落泪的原因并非出于歌本身:“我原来偏见地认为,这歌我这个年龄的人听会怀旧,会感动,看到特别年轻的朋友留言,我就觉得这种人和人之间没有偏见的时刻特别美好。有些东西,是大家可以共有的。”
“青春的葬礼”,这5个字来于高晓松。有一年郑钧生日,高晓松和钱实穆陪他喝酒。3个中年“老炮儿”聚在一起,突然想到以前总是一大堆人喝酒、唱歌、打闹,如今的生日显得格外萧瑟。高晓松说:“这太冷清了,哪儿像生日,这有点像葬礼。”
郑钧说:“也许有个时刻,就是你跟你的青春告别,把它埋葬的时刻。”于是,中年人走到路口的瞬间被他记下,诞生了一首歌。
唱歌时很多画面会涌进脑海。二十几年前的郑钧和高晓松,发疯似地跑到北大宿舍楼下高喊对方名字,瓢泼雨夜开车到十三陵游泳,在人民大学英语角傻站半天;郑钧和老狼,见面便是糙话问候,互称“禽兽”;宋柯羡慕郑钧每次出场就能夺走所有女孩的关注,“本来姑娘们觉得我啊,晓松啊,老狼啊都不错,郑钧一来,全都转向了”……
用高晓松的话说,那都是鲜衣怒马的“混账青春”。郑钧说:“那个时代,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没有那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也不怕失去,所以胆大包天地敢去尝试一切,这是青春最伟大的地方。”
后来,摇滚青年们变成了大叔,有了不一样的人生旅途。“默默祝福彼此,遥望他们。”高晓松最看得开:“如今大家都老了,不过没关系,我们会变成老朋友,老朋友是弥足珍贵的。”
长安长安,临安临安
如果给青春一个关键词,你会选择什么?
郑钧的答案是勇气。他觉得他的青春,就是在规矩和破坏规矩的循环里培养出来的。他生在西安的书香世家:祖父郑自毅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陕西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外公温君伟是留学日本的工程师,家里接通了西安第一根民用电线;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哥哥从小品学兼优。小时候每到周末,郑钧都得回老宅,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给祖先磕头上香。
“我祖爷爷是长安县人(现西安长安区),县志上记载长安人的特点就是‘性刚烈,好诉讼’。所以我们推崇的文化就是刚,谁打架厉害,谁就是英雄。”郑钧小学最崇拜的人是哥哥的一个朋友,一身军装,戴个军帽,打架时还能飞踹扫腿。“我是绝对的小迷弟,在后头偷偷跟着他,像追偶像一样追他,追了好几条街。”
“西安的底蕴,还有丛林式的童年生活让我变得很坚强。但是另一方面,西安人又是生冷蹭倔,人和人相处很生硬。我和我妈从来不会说我爱你。我考上大学,我哥也不是祝贺,而是说我们全家都是大学生,这没什么。其实我骨子里特别渴望温暖,所以报大学,我绝对不要去北方,我要去南方,去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那就杭州吧,古都临安。”
1987年,郑钧考入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业外贸专业。那个时期的杭电“星光熠熠”,除了未来的摇滚之星郑钧,还有未来的中国首富马云。后来,高晓松曾经问过郑钧:“马云那时候在杭电教英语,没教过你吗?”
郑钧回答:“没有,因为我是专业英语。”当年的工业外贸系是杭电最好的专业,省部合作,全员外教。郑钧清晰记得入学的场景。火车五六点就到了杭州城站火车站,公交车也没开,他背着行李就往文一路的学校走。城站到文一路八九公里,中途路过西湖。“我一看到西湖就惊了,这么小啊?那么伟大的西湖就这样?太失望了。”
系里外教多,天天给学生放欧美音乐,披头士、U2、枪炮与玫瑰,那是郑钧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摇滚。“我一听太喜欢了。” 他没有音乐基础,就从识简谱学起,然后再吉他、作曲、和声。别人去上课,他在宿舍里写歌,自己组乐队。
郑钧和乐队的第一次公开表演在杭电老校区的街心花园。人往那儿一坐,抱出吉他开始唱,一会儿就围上一堆人,顺利收割第一拨迷妹。后来,乐队买乐器,这拨粉丝做出了不小贡献。
最惬意的是晚上背把吉他,自行车骑到西湖边。草地上开两瓶啤酒,唱起崔健和罗大佑,累了直接躺下睡到天亮。夜间三潭印月,春末烟雨蒙蒙,冬时断桥残雪,他都见过。“所以后来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对西湖简直依依不舍。”
那个时期,摇滚乐从北京传来,流行歌从广东传来,杭州也有了浓烈的音乐氛围。杭州师范大学举办高校乐队汇演,郑钧和乐队收到邀请,心想:“这是出头之日啊!”结果郑钧得了急性阑尾炎,做完手术纱布都没拆。“他们问我能不能演?我说必须去啊!我让他们给我穿个军大衣,裹着纱布,用自行车驮着我就去了。”那是他们第一次在满座的小剧场表演。“唱了首崔健,唱了首英文歌,反正演完底下就疯了。当时的女朋友跟我说,你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歌手,然后我也当真了。”
就这样,郑钧下决心脱离“大学包分配”的传统。毕业后,乐队的朋友都干上了“正经工作”,只有他留在了音乐里。他说:“相信听《青春的葬礼》哭了的人里,一定有当年和我一起玩音乐的人,也一定有当年和我相爱的人。
·2016年,郑钧创作的漫画《摇滚藏獒》拍成电影,老狼到场助阵。
花10年让自己学会自在
离开杭电后,郑钧打算去美国,到北京办签证时因缘际会认识了黑豹乐队原吉他手郭传林,理想爆棚的他,又自断赴美路,成了北漂一族。四处借宿,睡过马路,800块钱过3个月。后来,郭传林把他推荐给发掘过Beyond、王菲和黑豹的知名经纪人陈健添。郑钧穿着破牛仔裤、烂球鞋进了陈健添住的松鹤大饭店。
套房里站着很多人,包括当时“范儿最正”的蔡国庆,人人都想得到陈健添在内地的第一份合同。最后,陈健添把合约递给了蓬头垢面但已写出了《赤裸裸》的郑钧,还预支了3000元港币的工资。郑钧拿着钱,一路骑回小破屋,兴奋不已。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赤裸裸》发行,既摇滚又诗意的词曲,配上爆发力的嗓音,郑钧一夜爆红,《回到拉萨》更是石破天惊,被视为革命性作品。接下来10年,用郑钧的话说,专辑出着,名气大着,和一帮朋友夜夜笙歌——下午3点喝到第二天早上6点,三里屯的酒吧成了家。2007年,郑钧的身体状况和个人生活都陷入低谷。他开始神经衰弱,每晚戴着耳机,听着重金属,整夜失眠。2010年起,郑钧戒烟戒酒,练习瑜伽,修禅打坐。他说:“这10年,我一直在学习,让内心达到宁静、平和、愉快。”
“对于这种青春的逝去,激情的退却,会有失落吗?”记者问。
“青春是不可替代的美好,但现在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我不再焦虑青春不再,辉煌不再,我花了10年时间,让自己学会放松,学会自在。”
所以,在《青春的葬礼》最后,郑钧写道:
不要诅咒你的过去,
至少它曾经因你而美丽。
不要只看这一时的凋零,
任何时候心中的明月,
都可以重新升起。
50岁时,家人给郑钧过生日,让他许个愿,他犯了难,觉得更有钱、更有名好像也没啥意思。“我说那就希望余生能做一点对别人有帮助的事,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吧。以我的创作能力,再写一些歌,如果还能让别人内心的明月升起,那我这辈子也算没白活吧?”
他说:“不用站在潮头,不用站在巅峰,一直低空飞行,也挺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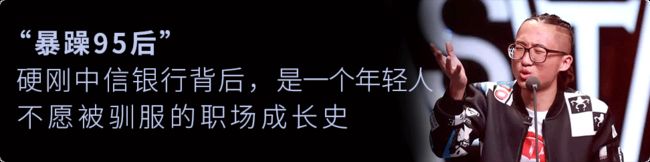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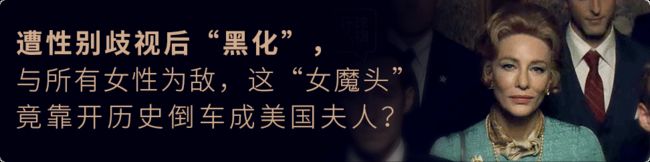


扫码进入人民文娱粉丝群
商务合作请联系
电话:010-65363483、65363115
QQ:3144809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