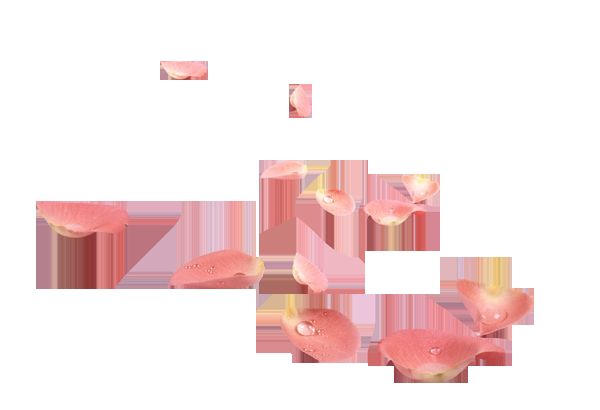文|汤谷虞渊
(一)
1945年8月。举国欢腾。15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条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中国战区也将陆续举行受降仪式。北平、天津、上海,都沉浸在莫大的欢乐里。
一声汽笛由远而近。白贤礼提着方头箱随着人流依次上岸。他抬头望着有些灰蒙的天,码头人声鼎沸,街上人潮拥挤,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
八年之后,他终于又站在故国熟悉的土地上。
八年时光,战火纷飞,白贤礼即使是在遥远的不列颠岛上也不曾有一刻忘记他多灾多难的祖国。如今,倦鸟归巢,他收起羽翼抖落一地风尘仆仆。不!他还不能停歇!
1946年北平报纸社会版上登有这样一则寻人启事:
侍农兄:
数载飘零,不知音信。如今我已归国,暂居于北平XX胡同XX号。望兄见此启示能告知近况,也好一叙兄弟之宜,我也能交还代为保管之物。
弟贤礼
短小的寻人启事如同丢进大海的一枚石子,没有激起任何大的波澜。偶有水花荡起,不是心有不轨的投机者,就是走投无路的城市饥民。白贤礼刚刚送走一名冒名顶替者,来人衣衫褴褛,只是口口叫嚣着要白贤礼把东西交出来,却具体连自己性甚名谁都含糊不清。
案几上的玉钗侧卧在一角,冷冷清清。定睛一看,可见钗顶的玉珠已失了一颗。那是炮火的印记。
(二)
1940年,战争的炮火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一直企图用绥靖政策置身事外的英国也无法再自欺欺人。
那是极为平常的一天。白贤礼梳洗完毕,刚刚要下楼同詹姆斯一家用早餐,詹姆斯太太那伴着笑声的"Good morning"还未传到耳边就被更为激烈的响声盖过。只听楼顶上“雷声”滚滚,整个世界瞬间东摇西晃。
是空袭!
电光火石间,白贤礼已经飞奔上楼,詹姆斯先生在身后直用英文喊着:“危险,危险!快到街道上的空地上去!”白贤礼恍若未闻,只是以极快的速度从行李中抽出一个精致的木制盒子。电灯晃得更厉害了,“咣当”,白贤礼同盒子一同跌在地上,一只玉钗从里面滚了出来。白贤礼不顾其他,一把抓起玉钗朝外面跑去。
1940年9月7日,德国对伦敦展开了大规模的空中袭击,不计其数的飞机从伦敦头顶飞过。大规模空袭一直持续到1941年5月7日,据统计,共有4.3万市民在空袭中丧命,伦敦也成为二战中被破坏程度最大的三座城市之一。
白贤礼自伦敦的废墟中站起身来,他想起了遥远的东方的祖国;想起了已经沦陷的华北各地;想起了同样身受空袭之苦的昆明;也想起了自己的承诺。他望着手中的玉钗,钗上尘土弥漫,一颗玉珠也不知道散落何处。就像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一样。
(三)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侍农兄依旧音讯全无。如果说之前还间或有一两个冒充者的话,那么现在可谓是门前冷落、无人问津。
再次回到北平的白贤礼重操旧业,在近郊的一处小学谋了个差事,负责教授小学的数学知识。战事虽说已停,但整个国家早被炮火侵袭地面目全非,百废待兴。况且国家的局势也不甚明朗,国共两党表面上和平无事,称要划江自治,但重庆谈判收效甚微,世界局势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明眼人一看就知内战已是在所难免。
内战?战争?不!不!白贤礼一阵心惊,他一定要尽快找到刘侍农!
君子一诺,重于千金。
(四)
1927年,20岁的白贤礼师范大学毕业后被聘为半草小学数学教员,负责全校的数学课程。刘侍农正是半草小学的校长。当时军阀混战,国内一片混乱,日本人盘踞在东北狼子野心。刘侍农是个颇有些爱国情怀的人,深知唯有振兴教育,从能从思想上拯救国民,挽救国家于水火之中,因此创办了这所半草小学。
刚刚毕业的白贤礼深为刘侍农的品格所感服,在交往之中,两个人的许多思想见解都不谋而合,深有相见恨晚之意。两名文弱书生常常在夜里秉烛夜谈,讨论国家前程,感慨乱世英雄何时起。
在大多数情况下,白贤礼都是一个倾听者,他年纪小,又刚刚毕业,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许多见解未免失之偏颇。但已过而立之年的白贤礼却在许多事上都有真知灼见,能够比白贤礼看得更清也想得更远。
比如说对战争的敏锐嗅觉。
自日本人发动“918事变”以来,刘侍农便知道日本人的胃口绝不是小小的东北三省所能填满的,华北即将是他的下一个目标。他的野心,是要吞掉整个中国。
所以刘侍农很早就开始为战争做准备,他加快授课进读,并一步步解聘教员,到最后,整个学校只剩下了白贤礼一个教员。
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彻底撕碎侵华野心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整个国家以一种疯狂的姿态进攻古老而衰颓的中国。不出几个月,华北各省纷纷沦陷。
白贤礼劝刘侍农和他一起暂时先到上海避避风头,华北眼看已经落入虎口。但刘侍农却早已另有打算。
“华北乃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侍农誓与华北同存亡。只是我有一物要托贤弟替我代为保管。这只玉钗乃是我的传家之宝,我不愿她随我一起毁在战火之中,失了先祖留下的遗物。我只愿战争结束以后,你我再相见,我能亲手将这支玉钗见到小女手中。”
1935年10月,白贤礼抵达上海。
1937年11月,白贤礼在家兄的安排下避难到伦敦。
(五)
这是1946年的冬夜,世界静得仿佛一点声音都没有。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划过静谧的长夜。
“找到啦!说是找到啦!”
白贤礼立即丢掉手中的笔。
来人是白贤礼的好友,自他回到北平之后,就一直帮助他大海捞针般地寻找刘侍农。
这是北平和天津交界处的一座普通村屋。天地漫漫,白雪皑皑。
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妇,她的眼神不大好使,待弄清白贤礼的来意之后便把人引进了屋内。
老妇坐在炕上,红着眼眶说着故事。
白贤礼走后,白草小学彻底解散,而刘侍农则褪去书生之气,一身戎装,投入到抗日的大军中去了。
老妇乃是刘侍农的结发夫妻,待她1940年得到丈夫早已战死的消息时,他的尸首早就不知流落何处。
此后她一直带着女儿在乱世艰难求生,逃难到这里后就一直定居在这里。
“不知道济兰这孩子现在在哪?”
老旧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一个女子缓缓走了进来。
白贤礼含着泪,把玉钗轻轻放在同样泪眼婆娑的女子手中。
“侍农兄,我已经把玉钗交还到济兰手中了。你若有知,我也可死而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