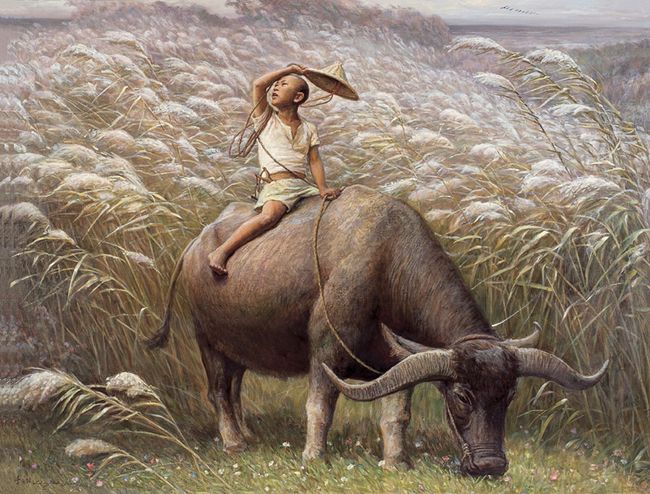我记得那是2014年的腊月,在外漂泊了两年的我,终于还是回到了那个曾经拼命想走出的地方——家乡。两年前,我的梦在山外头,而两年后,我的梦又重新飞回到了山里头。变化的是梦的内容,而不变的是,难以得到的东西便常常会去梦。诗人们常说,以梦为马便哪里都去得,但要是搁在我身上,这匹马怕也得累死。
那天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是我爸骑着摩托车接的我。这一路上,我爸没有问我的工作,只是一个劲的问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中意的女孩子,以及一些母亲为我准备的好菜。我坐在摩托车上,一边听着,一边数着他头上的白头发,仿佛觉得,他忽然在两年里就老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心里不停的骂自己是一个混球,但骂着骂着,我却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和我同村,小学和初中我们都在一个班里,后来上了高中也是同一所学校。我之所以会想起他,那是因为村里人也管他叫混球。混球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即使去问别人,我想也应该没人会知道。
想到这个人,我会立马想起两件事。第一件是,小学那会儿,上美术课,老师让画一朵小花,而他却在画本上涂了一个大鸡巴,最后被拉到操场上,揍了一个下午。第二件是,初中的时候同学欺负他,于是他便和那人打了一架;等到老师评理的时候,却说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个人怎么不打别人;犯浑的他,跳起来就给老师一个耳光,然后朝着老师吼道:“我这一个巴掌,到底是怎么拍响的”。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我读大二的时候。那一年放寒假,快要实习的我,却迟迟的找不到实习单位,怀着郁闷的心情,我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了他。那天他下身穿着一条牛仔裤,上身披着一件单薄的夹克;蓬乱的头发上,布满了灰尘,像是一个月没有洗过头。
我有些不确定的问:“混球,你是混球么?”
他转过头,看了看我说:“你是.......”
"我是王哲,你还记得我不?",我问。
他哦了一声,显然是想起了我。但我当时,却被他此时的模样,惊讶的差点说不出话来。那是一张蜡黄的脸,没有表情,呆滞的目光里全是浑浊,若不是哈出的热气,简直就跟电影里的行尸差不太多。
我有些诧异的问:“混球,你这是咋了?”
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问我:“大学里,好么?”
我说:“好,抽烟、喝酒、谈朋友老师都是不管的。”
“那学东西呢?”
我被他的话噎了一下,于是有些不好意思的说:“学东西也好,图书馆里啥都有,想学什么就去看。”
“哦”
他转身走了几步,又回过头问我:“你说,人要是死了,他犯的错是不是就清了。”
“这个........”,我知道他是在说他自己,但那时的我是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就会生了死的念头。于是我便骂他:“什么死不死的,活着才有可能恕罪的,死了只能是你自己舒坦了。”
他扭过头走了,再也没有给我说一句话,但我不知道的是,我的那一番话仅仅是让他多活了两年。那是大年三十的前一天,两年没有回家的我,正在厨房里帮着我妈摘菜。“哎——”,随着一声叹息,我爸从门外走了进来。
“爸,怎么了?”,我问。
“混球死了!”
“咋死的?”
“犯浑,跳崖摔死的;狗日的,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要过年了去跳崖,他叔叔些,这个年怕是过不好了”
事实上,我爸说错了。初一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到了混球家里,他叔叔们的年过得和以往没有什么差别。我背着我爸,去混球的坟前看了一下。说是坟,其实以前就是个冬天放红薯的地窖,把人往里一丢,垒上土便就成了坟。
这个春节无疑是单调的,我去到每一家,他们几乎都在聊混球的事;而我呢,则在他们的谈话中,将脑海里关于混球的片段链接了起来。
我小学三年级以前,是在我外婆家念的,后来家里条件稍好些了,才回到了父母身边。混球,则是我在新学校认识的第一个人。我对他的印象,和大人们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至多只能说是调皮了些。至于大人们说他是混球,我想这其中,应当是有着许许多多的误会。
混球的父母,在他读小学的时候,便外出打工去了。跟着奶奶一起生活的他,在同村人的眼里,就是地狱里跑出来的小鬼,自己混里混气不要紧,还带坏了别人家的孩子。我对这样的说法嗤之以鼻,因为混球是混了些,但也不是所有的混事都能扯到他的身上。
我记得有一次放了学,班上的人找到了混球,说是看着电视里拜把子挺好玩的,便邀请他,一起做个拜把子的游戏。混球一听,诶,这好玩,于是便答应了。没有香,就撕一页本子裹一裹;没有血酒,就捉了只鸭子,杀了放血,喝纯的,几个小子玩的是不亦乐乎。几天后事情败露了,那几个同学的家长找到了学校,口口声声的说,是混球带着自家孩子做出的混事;而那几个孩子也不说话,只是由着自家父母可劲的骂;混球解释,没有人相信,只是一个劲的挨揍,然后一个劲的哭。
混球背黑锅的事很多,同学们心里也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混球说过话,这其中也包括了我。后来他死后,我不止一次的感到罪恶,犹如是我亲手杀死了他。
每当过年他父母回来的时候,村里的人总喜欢去到他家,控诉些个混球干的混事。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只知道每当初一时候,我们一群小孩穿着新衣服,欢庆着新年的美好时,却总能听到混球挨揍的哭喊声。
我读初中的镇上,有一条小溪从街道上横穿而过,将街道分成了左右两部分;小溪上,则是镇头镇尾各横着一座石桥,分别唤作上桥和下桥。溪水很窄,桥很宽,看起来,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显得那么的不搭调。但事物,总有着他存在的道理,好的会变成坏的,坏的也能变成好的。就像这溪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其实是挺宽的;那个时候的她,就像是少女雪白的臂膀,深深的搂着这伟岸的石桥。
那个时候的溪水,是清澈的,是散发着体香的少女;而现在的溪水,是黑色的,是散发着恶臭的黑心妇。这一切的开始,还得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说起。我们暂且认为,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群人提着装满了毒药的药筒,从上游倒了下去。鱼儿们,不知道自己的末日已经到了,还是拼命的吮吸着河水里的氧份,直到他们像喝醉了酒的醉汉,一个个的歪倒在水里。
镇上的人疯狂了,他们仿佛看到了漂浮在河里的黄金,一个个的纷纷跳下了水。他们一手一条,若是发现更大的,便将手里的丢掉重新换过;更有的,甚至将裤脚扎了起来当做袋子,然后将鱼一条条的,塞进自己的裤裆里。但即使是这样,鱼还是多得捡不完;等到人都散了,河滩两旁,早已是雪白的一片。鱼开始慢慢的腐烂,一股子冲天的恶臭,充斥着整个小镇,一直臭到了今天。
我读初二的时候,镇上的同学欺负混球,混球也和他动了手。班主任把他们叫到了办公室,询问其中的缘由。
混球说:“是他先动的手。”
“那他为什么不打别人,一个巴掌拍不响”,班主任说出了他的至理名言。
混球涨红着脸,跳起来便朝着班主任脸上来了一巴掌,吼道:“我这一个巴掌,是怎么拍响的”
那时候躲在窗外的我,心里是激动的,因为混球做了我想过无数遍,却又不敢做的事情。但这样做的代价,却是混球的母亲跪在办公室里,痛哭的哀求了一个上午。享受完上位者的感觉后,班主任最终还是给了混球一个机会,只不过给了混球一个留校察看的处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混球的母亲,因为当天下午,她便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侧翻的装沙车给埋了。混球当天请了假,回了家;当我再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浑身都是伤,也变得不怎么说话了。
中考的时候,混球考了我们班的第一名;但班主任,却跟宣布最后一名一样,宣布了他的成绩。那时候的我,讲实话,心里是很不平衡的,凭什么混球不怎么看书,却也能考那么高的分。这一点我也是到了后来才释怀,因为学习,其实是一辈子的事儿,一次高分,并不能带表着什么。
读高中的时候,因为混球成绩好的原因,我的父母终于允许我和他一起去上学了;也正是这样,我每次去他家叫他的时候,总能听到他父亲含糊不清的叫骂声。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实人,但自从他母亲死后,便成天的醺酒,成了村里人口中的疯子。一个混球,一个疯子,在村里人看来这或许是最好的搭配。
高三的时候,混球辍学了,应了小学老师的那句话,“你个混球,长大了只有去挖煤”。具体的原因,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混球的父亲,在家里的楼梯上,上吊死了。
本该考上本科的我,因为玩游戏,最后考了个专科上大学去了;在老师眼里,只能去挖煤的混球,最后却丢下了优异的成绩,真的去挖煤了。我有的时候在想,好的或许会变成坏的,坏的也兴许会变成好的,如果不是我们早早的对混球下了定义,或许他真的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但这一切也只能是或许了。
后来我听说,混球在煤矿挖煤的时候,还救过十来个人;有一次井下瓦斯爆炸,有一个采煤小组被困在下边,没人敢下去,是混球舍了命把他们捞上来的。我对了对矿难的时间,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过后几个月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