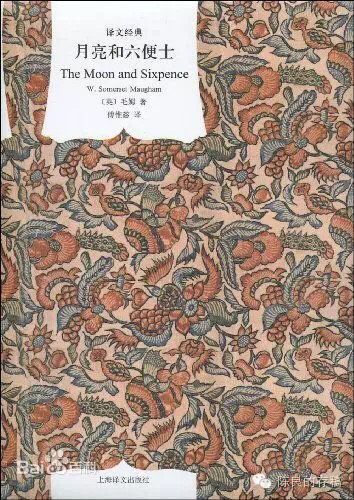我读了一本书,叫《月亮与六便士》,我没有怎么看懂。
读书的过程非常流畅,它既不如侦探小说一样引人入胜,又不像古典名作一样枯燥乏味,我仅用一个下午就读完了第一遍。这个故事以画家高更为原型,并不需要避免剧透。一个生活中枯燥乏味,兢兢业业的中年男人突然有一天想要学画画,抛弃了自己的妻儿和优渥的生活去巴黎过上了十分艰难的生活。他经历了不少困苦,终于在一个孤岛上活完了人生的后几年生病而亡,也达到了他艺术的巅峰的故事。
译作自然要看译者,我看的是李继宏先生翻译的,私以为不太好。李先生太过于执着成语,很多时候不免损伤了原意。就举结尾一处,“上帝的磨盘磨得很慢,但是磨得很细”一句译作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本来无妨,怎奈后来还有一句“我觉得他们肯定以为这是《圣经》上的话”。这样来看,翻译实在是有损原意了,如果不是我提前有所了解,一定会摸不着头脑。
如果你也认真的考虑过去写作一部小说,你会发现叙事角度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我”是主角,就可以更方便的去描写自己的心理活动;如果作者是游离于世界之外的,则可以跟随多个人物,写他们周边发生的事情;如果作者是全知全能的,所有事情所有人物的心理他早提前知晓了;当然还有今天所说的《月亮与六便士》的角度,作者作为出现在文中的一个人物,而他要讲关于他一个朋友的故事。但是只要你读了这本书,就不得不佩服叙事者的谨严和克制。他谨守着自己的视野范围,从不敢有一丝僭越。当他对其他人物有任何的评论或者判断时,常常会说出“我所做的的猜测都是毫无根据的”;没见面之前,他觉得斯特里克兰是“弱不禁风”的,之后才觉得是“魁梧雄壮”;之前觉得斯特里克兰太太“心地最纯良”,之后才觉得这个女子“竟然如此阴险歹毒”。我们看过很多作家,他们常常用这样的叙事角度,但却不能遵守叙事者的视角,这正是他们该学习和注意的。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是与本书相关的极有名的一句话,但其实与此书并没有太大关系。《月亮和六便士》的书名的来源是,毛姆的前一本书《人性的枷锁》出版时,有一位女评论家评论其男主角“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为天上的月亮神魂颠倒,对脚下的六便士视而不见”,毛姆很喜欢这个说法,就把它作为为了下一本作品的书名。很明显月亮代表了我们的对艺术和人生的理想,六便士则是生活中的蝇头小利。六便士是小额银币,所以我是不喜欢所谓“满地”的说法的,用六便士代表对利益的不屑,自然不用“满地”来增加其分量。
要读这本书,一定要先了解毛姆生活的时代以及背景,这是一本“私货”比较多的小说。作家很多时候写小说不仅写给读者,也写给自己;写给读者要让读者懂,写给自己的自然自己懂就行了;很多时候,作家的人格对作品有着极大的影响──就如读《红楼》不能不了解曹雪芹,读《地坛》不可不看到史铁生一样。毛姆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是狄更斯,在十八世纪风靡西方世界。但是毛姆却生活在十九世纪初,时代的变化让现实主义已经风烛残年,新的现代主义如日中天。于是你可以在文中随处看到作者近乎牢骚的自言自语,他了解时代正在前进,不可阻挡。但他也同时自信的表达,艺术的兴衰由于时代,但艺术的价值永不过时。如果读者在这本书中看到许多这样貌似无关的叙述,可以细细体味,你可以看到作者的心酸,愤怒和自信。这样的牢骚在结尾处达到高潮,我必须摘下来:
我的亨利叔叔在威特斯台柏尔教区做了二十七年牧师,遇到这种机会就会说:魔鬼要干坏事总可以引证《圣经》。他一直忘不了一个先令就可以买十三只大牡蛎的日子。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突兀的结尾,亨利叔叔在前文只出现过一次,也是在作者引用他的某句话的时候。再了解时,可知道作者在十岁即亡父,被他的亨利叔叔收养。其实作者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亨利叔叔已在十五年前亡故,他的叔叔不可能忘不了之前的日子。那忘不了那段日子的只能是作者,他是忘不了早亡的父亲,忘不了去世的叔叔,还是忘不了过去那个现实主义正兴盛的时光,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了。这句话可谓笑中带泪,不禁让人拍手叫绝。
我没有读懂这本书,这是我说这句话的第二次。我不是故作深沉,是真的没有读懂。其实我也想像其他书评或者推荐一样,一来就写写自己的感觉,讲讲自己的故事,这才是大家喜欢的豆瓣的模式不是吗。但是我在桌前坐了很久,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确信我是没有读懂,只好先讲讲译者,说说叙事,聊聊背景,其实我是不想讲这些的。但我又觉得这本书简直是有一种魔力,我觉得作者废话太多,却越来越想看那些废话;我觉得男主角简直是个恶棍,却开始幻想他在荒岛的日子。我们先骂骂斯特里克兰那个混球,顺便骂骂徐志摩与顾城。我想起过去的日子和悔恨,艺术和理想,我讲不来。
既然毛姆的小说里夹带了私货,请允许我也夹带一点,我想讲一个故事。郭小四写书,被网友骂了,我也跟着骂。他的粉丝回护说:“你行你来写啊!”网友的反驳很有力:“我说一个冰箱不好用,还要学会制冷?”我却不敢使用这个理由,因为,我本来也自以为是个冰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