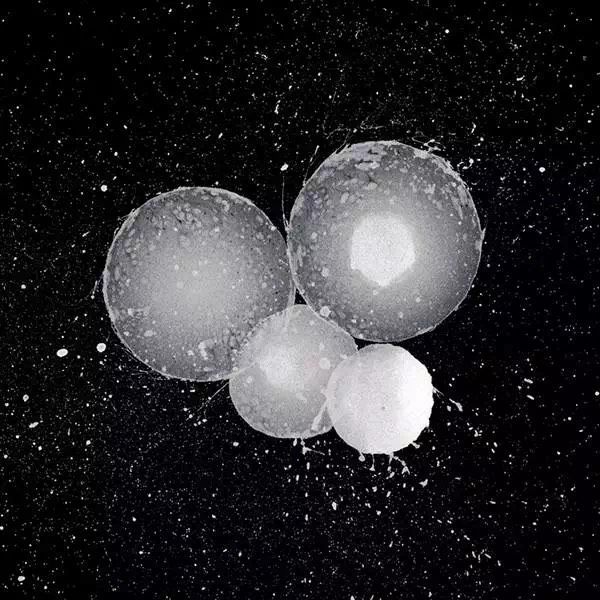在我飞速翻动画册,每张图片停留不超过一秒时,奇妙的事发生了:
我再也分不清巴黎圣母院、亚眠大教堂、沙特尔大教堂或者别的什么大教堂间的区别,只知道它们都是一处带尖顶的石质建筑物,附带一面花纹繁复的玫瑰窗。
也不是没有相似的经历:雅典卫城诚然是可爱的,但是看到爱琴海诸岛上不计其数的希腊柱时,总归要晕眩;特奥蒂华坎金字塔诚然是宏伟的,但是发现中美洲森林里密集分布着它的副本时,难免会疲劳。
然而最不可思议者,乃是在早已熟悉的罗马斗兽场之外,蓦然发现古罗马殖民地上处处有罗马斗兽场的精确复制品。同样的赭色背景和拱门廊柱堆叠而成的圆形结构,一时竟分不清哪个属于罗马,哪个属于摩洛哥,而哪个才是坐落于阿尔及利亚的。
于是我放下画册,遐想起两千多年前罗马帝国的盛景来:
每座城市,都效仿都城罗马,竭力使其风格与都城无异。标准化的宽敞街道上是标准化的奴隶和奴隶主。原共和罗马的居民,已然演化成了拿着国家津贴云游四方的寄生阶级。广场上,身着华服的雄辩家、大诗人、行政官们向追随者挥手致意。一切光辉已达到饱和,一切事物已极度圆满,一切,都不会比现在更好。
但是,任何一个细心的旅人可以发现:日耳曼族奴隶被禁止传授本民族神话,转而膜拜奥林匹斯十二神时,流下了怎样的不甘与恚恨的泪水;波斯诗人被禁止吟唱本民族叙事诗,转而谱写起帝王颂歌时,是如何用曲笔埋藏起辛辣讽刺;雄辩家用西塞罗式的华美严谨的措辞强调的,无非就是去前线征服并同化其它民族的伟业;诗人的维吉尔般优美的篇章,终归是没能跳出开国之初就已成型的格局。
罗马人凭借强劲的实力完成对欧亚大陆广袤疆土上诸部族的同质化,构筑起空前绝后的第一个“世界帝国”,却在下一个瞬间走向衰败。极成功的同质化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文化的精神内核单调而贫血,帝国陷入一场未来的意义被取消,一切无复可为的世界主义昏梦。
因此,濒死的罗马攀住基督教的青藤——尽管在帝国盛世它是被封杀的异教——并试图重新建构起帝国的意义,然而它失败了,留下鎏金的残片,和长达千年的政教争权的乱局。
以征服、掠夺和同化为核心的罗马文化虽有最最精美的法学、建筑学、文学与艺术的外衣,终是被野心反噬,归于崩塌。以致自诩罗马后人的近代西欧人试图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拾这层外衣时,不得不求助于以包容多元著称的阿拉伯邻居。
同质化的利刃吸干了罗马文化的血液,无独有偶,当这刀锋游曳,指向同一时期的中国,另一种灾难性后果整整延续了两千多年。
董仲舒和他的规模宏大的“春秋大一统”,已成为官方承认的唯一。他的继承者,并着规模日益扩大的太学与私学,抢占了本属于其它学派的全部空间。发轫于轴心时代的思想之舰停止航行,主动下沉。
也许魏晋时期可算作其后的唯一一次浮出水面的呼吸。但这场呼吸旋即被扼杀,其意义亦遭到扭曲和否定。嵇康的酒神精神的萌芽,很快被同为文学革新者的王勃斥为“穷途之哭”。玄学家的精神本质被抽离,其慢条斯理咬文嚼字的坏形式,倒被后来的道学家偷过去,奉为圭臬。
等到朱子写起《四书章句集注》,一切都在看似严肃的氛围里定格。之后种种悲喜剧的上演都不再令人惊讶:陆九渊与朱熹的鹅湖之会,前后七子复古派与力推唐宋八大家的唐宋派的争斗,状元商辂们和落榜生徐渭们的互相看不起……一切热闹,无论标榜得多么高尚,都离不开排斥异己的态度和把对方同化的野心。殊不知,最最成功的同质化,就是造就儒学独尊的狭小孔道的“春秋大一统”。多少风流俊彦大智大才,都在这孔道里冲撞奔突,党同伐异,愈斗愈挤,愈挤愈斗,终于斗垮,挤烂,生霉,发酵,飘出一阵迷人的腐尸味。
然后呢?在高处,有人闻到这味道,心下大悦,曰:“天下大同矣。”
可这儒教大同的中国,正是二十世纪初垂死待宰的中国啊。
同质化的刀锋虽助中国主流文化排尽可排之异己,芟尽可芟之反骨,终归败于自身的空洞无力。
同质化的刀锋,煽动起多少人膨胀的野心?葬送了多少种鼎盛的文化?刀锋无所不在,其毒害也无刻不存。
不要以为同质化只是末期才有的衰象。董仲舒之说即发端于汉朝的壮年,毕达哥拉斯学派因不承认“√2”而动杀心,亦是所谓“文明希腊”的往事。也不要觉得倡导多元与和谐的现当代就没有同质化的威胁。鲍林恃学界霸主之位排压谢赫特曼有关“准晶体”的研究来一统学界论调,正是上世纪的史实。
更不要以为,我举这么多事例证明的问题与我们学生无关。同质化的刀锋下,思想贫血匮乏,严重排他,引向一条死路的故事,正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轰轰烈烈地上演。
嚼食着同样的课本,追逐着同样的风尚,再不找一方属于自己的独有之地以抵抗同质化的威胁,那么,剥去名字与记忆等等细节的我们,和扎米亚京《我们》中的“人”们又有何异呢?
没有差异,都只是“列维坦”,都只是人群。而人群,如汤因比所言,“可以召之即来,可以挥之则去,可以拍照,亦可以屠杀。”
2012年2月
梁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