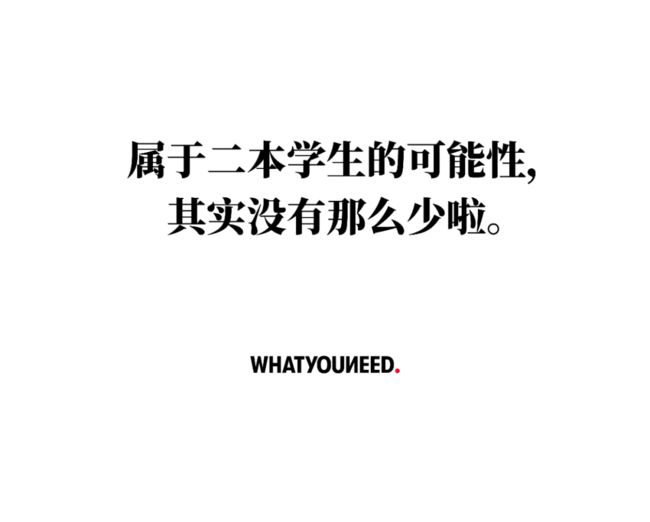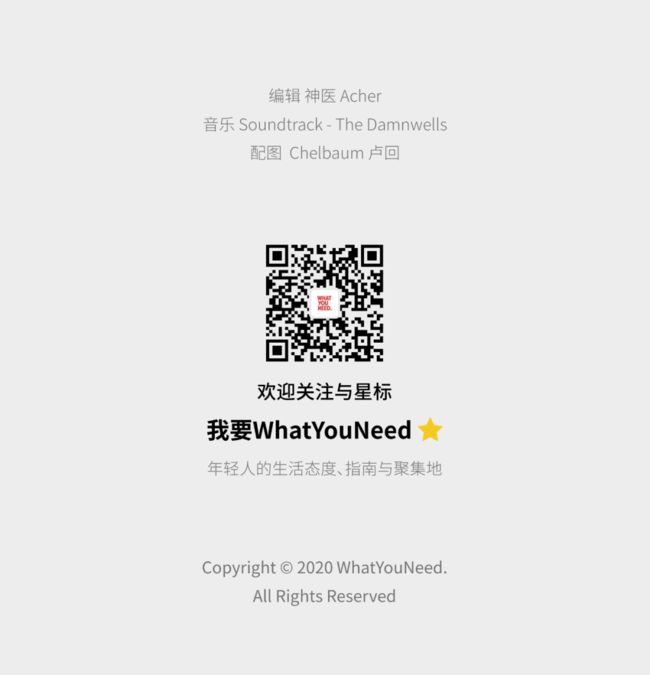我是二本毕业生,我觉得自己在走钢丝。
编辑按
最近在看一本新书,书名叫《我的二本学生》。
作者黄灯在书里说:
“二本院校的学生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年轻群体。
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即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
同为二本学生,我常常感觉自己是不好意思说话的。
这个社会上的话语权和聚光灯都会集中在更为少数来自顶尖学府的精英们身上。
如果真如黄灯老师所言,二本学生这个基数庞大的群体,会成为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那我认为,二本学生的样子、成长的环境和经历,至少要被更多非二本院校出身的人们看见。
所以今晚,我想以一个二本学生的身份,来分享我在二本院校四年里看见的事情。
「读书改变命运,但在 HU 学院读书,只改变了百分之五十的命运。」
我第一时间想起来的话,来自大三时考研认识的一位师兄。
当时我们正在一起排队,准备进入图书馆,开始新一天的备考。
考研、考公和考编,被许多人认为是二本生涯里,最好的结局。我也不例外。
师兄指着图书馆外这条长长的队伍,对我说:
「我们这群人,就是来改变剩下百分之五十的命运的。」
师兄目光如炬。
学校旁边的山(背影不是我)
一开始,
我满怀期待 。
我所就读的 HU 学院,位于深圳旁边的一个二线城市,是这座城市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相比起黄灯老师笔下的广东 F 学院,HU 学院的录取分数线要更低一些。
和我身边许多因为考砸了才来到这里的同学不一样,学渣如我,在高考时拿出了高中以来最好一次发挥,才堪堪到达了 HU 学院的录取分数线。
因此,拿到学校录取通知书那刻,我的内心其实满是期待。
满足感从到校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校内各色组织在迎新生的广场上搭起了五花八门的帐篷,猛烈的阳光下人们穿着不同的组织服装来来往往,一位高高瘦瘦的师兄来到我跟前,带我完成所有入学程序,一路上开朗地和我攀谈。
目之所及,朝气蓬勃。
确实是与以前的生活全然不同的样子:所有人都在谈论组织、谈论社团、谈论活动。
被这样的气氛包裹,我在加入社团后的第一次聚餐,拍下了餐桌上数不清的啤酒瓶,发了条朋友圈,深情告白:
「和你们在一起太开心了,喝多少都愿意!」
 和大学部门的同学在一起
和大学部门的同学在一起
他说这个社会最好的样子,
就是「全他妈装上我的电梯广告」。
想起来,这样的快乐应该是动摇在某天刷微博的时候。
那天我刷到了一条来自中山大学的同学的微博。他是理科生,他在那条微博里转发了他大学同学的一条关于某个知识点的讨论,然后他自己再在同学的基础上,补充了自己的思考。
具体内容我实在不记得了。但至今依然能想起看到这条微博的感受 —— 原来,别人的大学是这样子的。
在只当了大学生不到三个月的我看来,「大学」的样貌依然像是被一块布盖着,我每看得多一些,这块布就掀开一些。
但这一次掀开看见的「大学」模样,却似乎很难在 HU 学院里找到比对。
在 HU 学院里,人们讨论组织、讨论社团、讨论活动,也讨论哪个老师脾气好,哪个事情学分高。
但似乎很少很少,会听到有人在讨论知识本身。

我再次环顾四周。
我看见选课系统上,一门叫做「性社会学」的选修课,每年都是大热门。当选课通知发下来以后,师兄师姐们就极力推荐这门课,声称「抢到就是赚到」。
这让我对它充满了好奇,早早蹲守在抢课页面上,但抢课开启不到十秒,这堂课的名额就已经满了。
后来才知道,人们抢它的原因,大多数都不是因为对它有多么感兴趣,而更多是因为任课老师基本上不上课,抢到的同学相当于不上课就拿到了学分。
和黄灯老师总结广东 F 学院一样,「功利」二字从这时候开始,成为了我对这所二本院校的最大印象。
我隔壁宿舍的室友,通读《利维坦》、《社会契约论》、《人类简史》等多本艰涩著作,时常头头是道地在私下谈论他设想里的完美社会。
他只差 4 分就能考上目标大学。我问他未来想做什么,他说:「混啰。」
这个与更好的教育环境只差 4 分的男孩,接受了另一种人生。
后来他成为了一名电梯广告的招商代表。前阵子和他恢复联系,他说这个社会最好的样子,就是「全他妈装上我的电梯广告」。

第一次去学校时在路上拍的
不仅在学生身上能感受到功利,
在老师身上也同样感受到 。
不仅在学生身上能感受到功利,在老师身上也同样可以。两者之间,像是相互塑造。
记得是在一堂哲学课上,老师正讲到某个哲学家的观点,正当听得津津有味时,她却突然说了句:
「这个知识点就讲到这里,再讲深了你们也听不懂,也不会考。不过刚才讲的要记牢哈,会考的。」
难得的哲学思考,就这样戛然而止。
这样的事情也常常在我另一名同读二本院校的朋友的课堂上发生。这位朋友在高考时因为不够时间写作文,导致高考分数远低于自己的正常水准。讨论起来,她不免感叹:
「是不是就因为我写字慢了点,就没有深入学习叔本华的权利呢?」

回想起来,我记得我那位拿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的老师,在自行终结了讲解以后,脸上也闪过了一瞬的落寞,稍稍地摇了摇头。不知道她当时的内心想法会是什么。
其实,依然有学术追求的学生和老师,在二本院校里也不在少数。
但当学问与人之间横亘着「二本院校」所代表的某种固有印象后,我接触到的多数人,都倾向于接受,不想再与其抗争。
正如黄灯老师所言,许多人进入二本院校,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
“不敢去想自己职业的天花板在哪里,
毕竟揣着这个学历,
觉得每往上一步都可能就是天花板了。”
开头提及的师兄来自粤西地区的小镇,是家中长子。
高中时读了一篇关于山西煤矿的文章,立志要做一名调查记者。可惜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高考发挥失常,来到了这里。
几个月后,他通过考研,考回了自己高中时的目标院校,现在,他如愿进入了一家知名媒体,成为了一线记者。
几年以后,再次想起师兄的话,当时的场景还是这样清晰。这是他对于 HU 学院,或者说是整个「二本院校」的理解:
“读书改变命运,但在 HU 学院读书,只改变了百分之五十的命运。”
这么过了几年,我似乎也应该给出我自己的理解了。

我没有继续考研,拥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也过上了一部分自己想要的生活。饶是如此,「何时考公或考研」的讨论,依然是在家里的几乎每一顿饭桌上,需要拿出来的话题。
妈妈总说:「不要被现在的生活蒙蔽了,你的学历在未来会没有任何竞争力。」
黄灯老师在书中形容二本学历是「不牢靠的」,这份不牢靠落实到每一个二本毕业生的人生里就变得特别可感。
另一位二本毕业的朋友,如今已经在湖南电视台站稳了脚跟,成为了一位节目编导,按着自己读书时的愿望,每天见不同的明星。
这个常常让同学们羡慕的女生,却跟我说:「不敢去想自己职业的天花板在哪里,毕竟揣着这个学历,觉得每往上一步,都可能就是天花板了。」
你可以理解为,这种走钢丝的心情是许许多多二本毕业生正在面临的困境;但从另一面来看,师兄、我和我的朋友,如今都各自拥有着能让自己满意的日子。
在目前的社会环境里,二本学生要走到更大的舞台,固然还无法迈出非常稳固而有底气的步伐。
但至少,朋友们的例子,会让我看见,属于二本学生的世界,其实也没有那么狭窄。

最后 。
后来,那位做招商代表的同学告诉我,其实他有一个高中同学,考到了德国的波恩大学。
波恩大学,就是马克思和尼采念的那所大学。
招商代表偶尔会和他的这个高中同学通电话,向他请教一些在书里面自己不理解的问题。
我问他,那为什么在学校时你不会和老师和同学请教呢?
他说:「感觉在学校里就是做不出来这事儿。」
这件事让我仿佛看见了他的两张面孔,一张是给波恩大学的朋友准备的,一张是给二本院校准备的。
当他进入 HU 学院,就好像把自己置入了某种已经事先预备好的程式里。这条程式上写着「混」、「平凡」、「得过且过」。
不知道这样的同学,在二本院校里会有多少。
而我必须承认,在二本的四年间走过来以后,我似乎也长出来两张面孔。
一个我常常潜意识地缺乏自信,特别是身处一众名校出身的同事之中,在很多事情上,会很自然地怀疑自己的见解;
另一个我,则在用力地对抗这种低自信时刻,拒绝承认、更拒绝让人看见,自己也是一个会因为一纸文凭而自我否定的人。
如何好好地面对这两张面孔,我想这是 HU 学院留给我的最后一门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