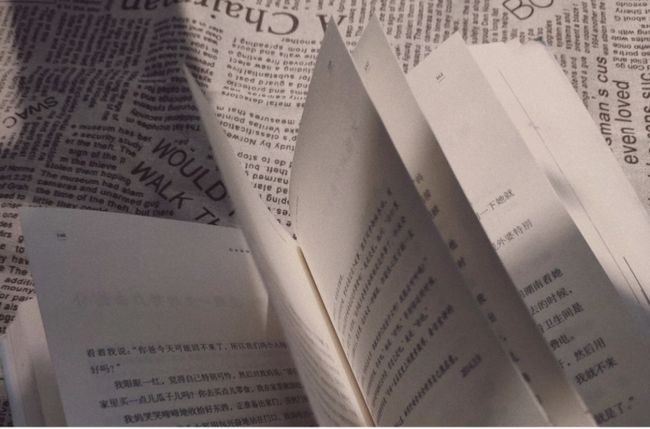这是这座南方城市最后一次接受阳光暴晒,再过几天,秋天就要来了。
走在依旧把冷气开得很足的商场里,穿着短袖连衣裙的女孩子们只能快步走着。逛街、试穿衣服都不失为一种取暖的方法。
商店是簇新的,尤其是节日来临的时候,到处是大块的干净到找不到一丝灰尘的玻璃。阳光穿过的时候,知不道什么时候就会在某一面墙上留下一个小小彩虹。
漆发现,她时间不够用是从有了手机开始:每次想看一眼时间都需要点开手机。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光是翻翻社交软件,时间就一下子没了。
明明只是想看一眼时间,怎么就能被这个小黑盒拽着跑了?
还有几次,这个小黑盒忽然没电了。她早上起来,完全不知道当下是什么时间。
在等待充电开机的这几分钟里,她几乎焦虑得抓狂。
现在,她知道自己是迫切地需要一块手表了。一个没有什么花哨功能的,却能告诉她明确时间的东西。
她朝柜子里看,一只只手表躺在精致的礼盒里面,金属壳子上泛着冷冷的光。
从三四千到上万,却无一例外的没有生命:你给出相应面额的钞票,它就是你的。没有例外。
涂着裸色口红,头发高高盘起的店员笑盈盈地走向她,挑了几只手表取出来。
从银边到金边,从镶着碎钻到镶着一圈钻的,飞进去的光被折射成炫目的一片,看得人眼花缭乱。
“是自己戴还是送人呢?”
“自己戴。”
“小姐,你自己买表的话我比较推荐这款……”她涂着裸粉色的大理石纹的指甲伸出来,点着其中一只,“你看这只是Gin牌的新款,这个色泽和手感绝对好。”
漆把手表试戴了一下,却发现表盘上面什么数字都没有,只有两根看起来静止了的时针和秒针。
“这怎么都看不清时间?”她疑惑地问店员。
“哟。”那女人笑起来,鼻子上的小褶皱出现在粉底微微卡粉的地方,“现在哪还有人买手表是为了看时间的呀,不都是为了搭配嘛。”
漆皱了皱眉,把手表摘下。
再次仔细看柜台机其他手表,有些没有数字,有些没有秒针,一个个都像是战争年代上丢了胳膊腿的人。
她说了声谢谢匆匆离开了柜台。
从商场后门出来,是一条幽长的巷子,漆捏了捏背包的肩带慢慢往里面走去。
她很少往这里来。她母亲常说那是个很脏的地方,鱼龙混杂,连一丝干净空气都呼吸不到。
今天她却像着了魔一样往里面走去,一群蓝眼睛褐眼睛的人出现在眼前。她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眼睛:他们穿着极其不讲究,有些人外套上的扣子都已经不齐全了,像刚才商场里的手表。
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像样的玻璃柜子装着,也没有人愿意花大把的钞票来买他们。
唯一让漆不理解的是,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好像生活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们。
实际上,他们作为外来人在这座城市生存,没有光明正大的栖身之地,只能常年在这幽深的巷子里呼吸狭窄的空气。
巷子里是一家家紧挨着的店铺,他们卖香料和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水晶球,占卜牌,油画,小的雕塑和挂件。
漆飞快地走着,忽然在一家店门口停下。
在一块被颜料弄脏了一角的玻璃背后,放着一排手表。
它们不像商店里的手表那般神采奕奕,夺人眼球。它们此刻正在黑色的丝绒布上安静地睡着,在周围扬起的点点尘埃里小声打着鼾。
“嘿,想看看手表吗?”站在边上灰色头发的老爷爷微笑着问她。
“我……我就是看看。”
“喜欢哪一款,我给你试试?”
漆盯着里面个色手表,其中有一只设计极其简约,白色的表盘,时针分针秒针都有,黑色的表带,像某种古老生物的皮。
正在想着会是什么动物,老爷爷已经把手表戴在她的手上。踢嗒踢嗒,秒针走过的声音却像是透过皮肤,一记记轻轻拍打在她的血管上。温热而潮湿。
这就是她在寻找的吗?这生的声音!
她几乎是脱口而出:“我能买它吗?”
“可以呀。”
“多少钱?”她忽然担心起它的价格。
“八百。”
竟然只要八百,漆急忙付了钱,像是生怕它下一秒就会被别人抢去似的。
“来,我把它的盒子给你。”
老爷爷递过来一只破旧的深蓝色盒子,虽然很久,里面却还放着一个完整的鉴定小册子。
她小心翼翼地翻开,像是打开一本尘封已久的秘籍。她认真地看着。
当看到“产于1989年”的英文字样时,她暗暗吃了一惊,没想到是一只比自己年纪还大的手表呐。
漆把手表戴起来,她的手腕很细,可以扣到最后一格。
表带已经松动了,某种生物的皮也有些开裂,在最后第二格的地方尤其明显。
可以猜想,它之前的主人总是扣在那一格。
不知道她现在在何方呢。漆轻轻地用指尖感受着表带,如果她已经不再世上,看见自己曾经的心爱之物找到了新的主人,是否会感到一丝欣慰呢?
在这么想着的时候,她忽然觉得有道光打在自己背上。暖洋洋的一小块。她站在原地,用力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把这巷子里的阳光全部浸入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