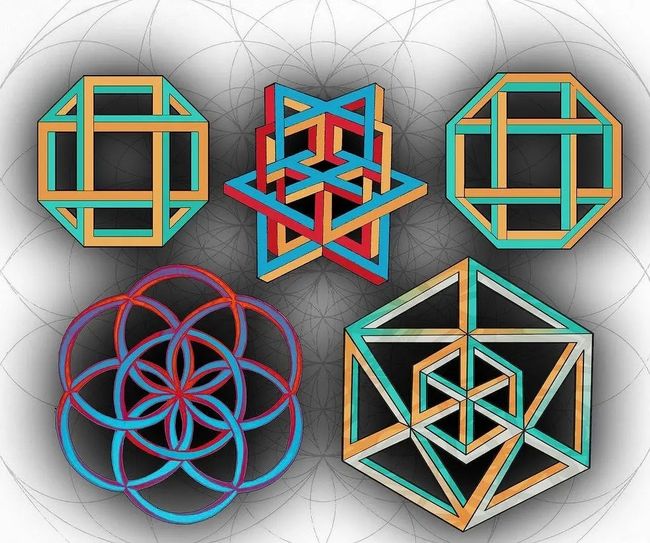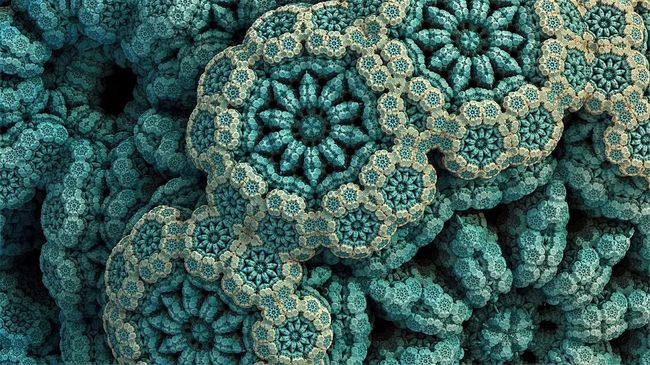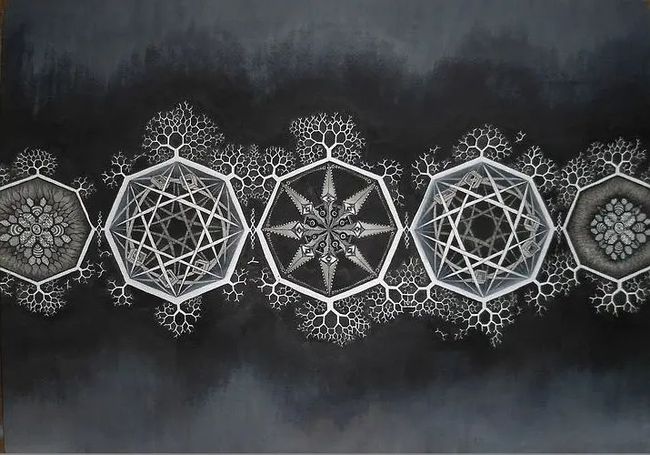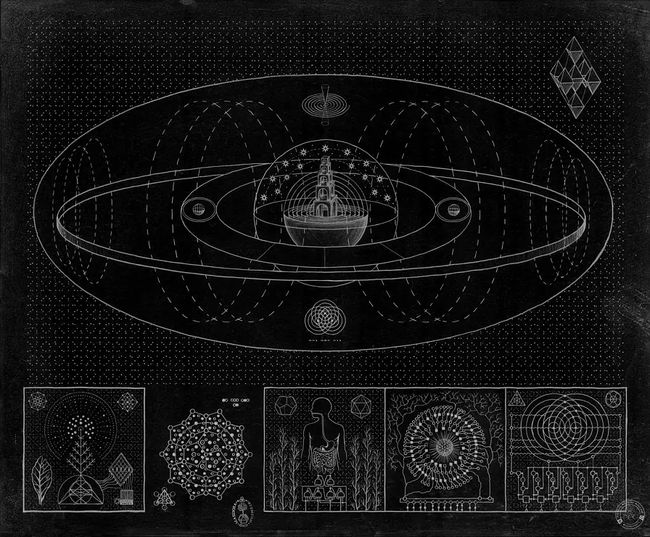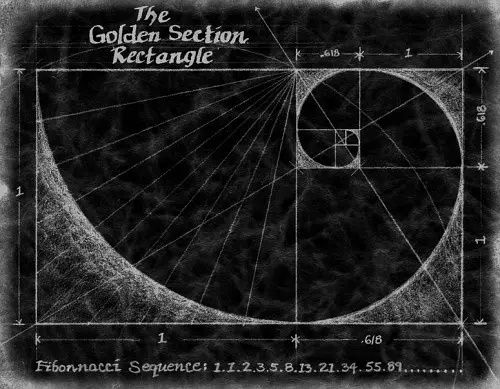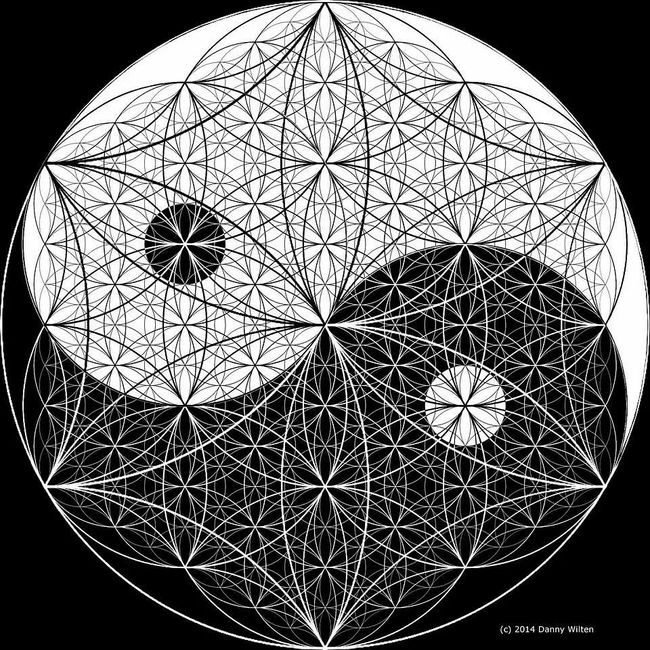阿伦特对于道德问题的反思,我们发现单凭理性很难应对道德困境。理性也无法单独解决价值难题。在人类三大永恒主题,真、善、美,之中,好像只剩下“求真”这件事,毕竟,搞科学研究,总归还是理性最擅长的事情。
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对这块阵地也发起了冲击。在科学活动中,理性难道就没有局限吗?波普尔的质疑直接指向了科学理性本身,他的思想成果,改写了启蒙传统下的科学观和真理观,影响极其深远。
这种影响还不仅发生在科学领域。很多人都知道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但他还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其实他的政治理论和科学哲学一脉相承,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洞见:人类是容易犯错的物种,这是人类固有的特征。不管是在科学还是在政治经济活动中,我们都摆脱不了“可错性,就是说人永远可能会犯错。
为什么科学的正确永远是不彻底的正确?
先说说波普尔最著名的“证伪主义”理论,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科学理论的标志不是它能够被证明是对的,而是它可以被证明为错的。这种概括基本正确,但容易引起误解,好像波普尔是在主张,科学事业追求的不是证实而是证伪,科学家好像都变成了“独孤求败”的武林大侠。
科学家当然会努力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波普尔也从不反对这一点。但他进一步追问:科学中所谓 “正确”究竟是什么意思?
波普尔给出了回答:科学的正确永远是一种不彻底的正确。要理解这个“不彻底”,我们看看波普尔思想的起点,看看他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1919年,那一年波普尔17岁,遇到了两件事,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件事,波普尔遇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大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成为了他的助手。但他很快发现,精神分析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实证据,都能自圆其说。
比如,一个人把别人推到河里,这是他性压抑的表现;如果这个人把一位溺水者救上岸,又可以解释为性压抑的“升华”。无论发生什么,性压抑理论本身都不会出错。这种总是正确的理论是真正的科学吗?波普尔产生了怀疑。
第二件事,也是在1919年,波普尔开始热衷于爱因斯坦的理论,两年之后还去听了爱因斯坦在维也纳举办的讲座。要知道,广义相对论刚提出的时候,只是一个理论猜想。为了检测这个猜想,爱因斯坦提出了三个推论,根据其中一个推论,在日食的时候,通过观测太阳附近的光线,就可以来检验广义相对论的预测究竟对不对。
1919年,检测的机会来了,在5月29日的日全食中,英国科学家观察到了预测中的所谓“红移现象”,广义相对论第一次得到了经验证明。这个事件轰动了整个世界。但让波普尔感到震撼的不是实验结果,而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态度。
在实验之前,爱因斯坦明确表示:首先,如果观察的结果和理论预测不符合,那广义相对论就错了。而且,即使观察结果符合理论预测,也不意味着广义相对论就是绝对正确,无法超越的理论。
爱因斯坦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理论被否定,但他不仅没有回避经验检测,还明确提出了被经验证伪的可能,而且他绝不言称自己的理论是真理。这种态度,与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让波普尔无比钦佩,他认为这种理性批判精神才是科学家的典范。
波普尔并不是说科学理论必定会被证伪,而是说理论本身必须包括“经验上被证伪”的可能性,就是你不能事先就排除了任何出错的状况。
我们先做个猜想理论,或许更能明白这其中得道理;
第一个理论:说地震是因为大象崴脚引起的,大地被一头大象驮在背上,大象一崴脚,人间就会发生地震。这个理论是不是很离谱,但这个理论是可以被证伪的:只要挖到地底下,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头大象就行了。这当然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但却符合科学理论的条件。
第二个理论,说地震是阴阳失调引起的,而且它有一套非常系统的论述,能讲出很多道理,但是呢,你就是没办法检测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哪怕是正确的,也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
所以,一个理论算不算科学理论,首先不是看它的对错,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够接受事实的检测,是否可能被证伪。波普尔认为,这才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理论的试金石,他把这叫做“可证伪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科学理论就不会是“彻底正确”的,因为它自身就包含着被证伪的可能。
为什么科学无法获得真理?
刚才讲到爱因斯坦还表达了一个想法,说即使观察结果和理论一致,也不能证明理论就是绝对正确的。波普尔从中得到了启发,意识到证实和证伪是不对称的。什么意思呢?你看,一个理论被证实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也不能证明它绝对正确,但只要被证伪了一次,它就被推翻了。
这种不对称性,就对科学传统的“归纳法”构成了挑战。
所谓归纳,就是从已知的事实中总结出普遍的规律。比如看到一只天鹅是白色的,一百只、一千只、一万只天鹅都是白色的,于是就归纳总结出一个普遍命题:凡是天鹅都是白色的。但其实谁都无法保证,会不会在某一天遇到一只黑天鹅。
这个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从哲学家休谟到罗素都质疑过归纳法的可靠性。罗素很幽默,他说,一只每天被主人喂食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有一天自己会被拧断脖子。维特根斯特也曾说过,我们之所以采用归纳法,是因为它是和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但它并“没有逻辑基础,只有心理学的基础”。
如果归纳法不可靠,那怎么解释科学知识的成长机制呢?难道要把被反复验证过的科学知识全部推翻吗?
波普尔提出了一个解释方案,妥善处理了这个麻烦。波普尔说,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靠归纳,就是观察事实-归纳理论-证实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猜想。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就保留这个猜想,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一直维持这个猜想的暂时有效性。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构想新的理论,进入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
波普尔就这样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避免了归纳法来动摇科学逻辑的基础。
同时也意味着,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理论始终都没有被证伪,能不能说它就是真理了呢?不能。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未来会不会遇到反例,会不会遇到那只黑天鹅。所以,就算某个理论猜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
就这样,波普尔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理论不是真理,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
科学并不是“正确”的代名词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但并不是启蒙传统以为的那样,能够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有些思想传统虽然不是科学,但本身有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还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灵感来源。比如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包括之前说到的精神分析学,都属于这一类。
所以,波普尔其实是科学至上论的批判者。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并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也不是“正确”或“真理”的代名词。
当这种思想延伸到社会政治理论中,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形态呢?当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转过身,展现出政治哲学家的一面,我们又会看到怎样的洞察呢?这就是后面需要探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