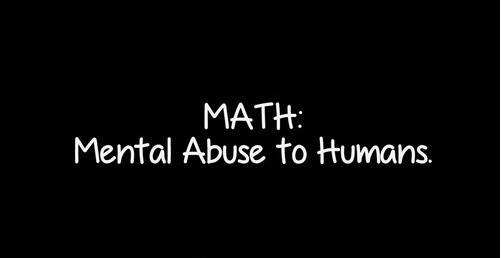上大学的第一节高数课上,首先引我注目的就是陈柯西。那日课堂上睡觉的睡觉水手机的水手机,同样无聊的我随意环视教室,看到前排一个穿黑色衬衫的女生,头发随意绑成奇怪的样子。她身板修长,轮廓明显,表情冷漠,眼睛透过面前的黑板,仿佛在看很遥远的地方。
当然我识得陈柯西,是后来的事了。另外这堂课上我还记住了一个人——钱泰勒。
钱泰勒是我们的高数讲师,年纪不大,但却颇为沉稳宽厚。平心而论课讲得很不错,但良师未必出高徒,钱泰勒的班上有两个天生的数学白痴,那就是我和陈柯西。所有的课堂小测和作业题,近百人的班里,永远有两个醒目的不及格。
陈柯西什么都好,就是数学不开窍。至于我?我没好过什么,数学不好也很自然。
后来次数多了,我们也甘做落后分子,反正数学差劲大多被归因于先天,先天不足我也自认倒霉。但是,同样是不及格,我也能感觉到,陈柯西的不开窍和我的不开窍不是一个概念;我是真的不聪明,无法使用有逻辑的思路;陈柯西却仿佛是在刻意回避什么似的,拒绝使用逻辑正常的思路。
但结果是一样的,我们什么题都做不出。钱泰勒发下精心挑选的习题,我们以惨淡的得分回礼。
终于,礼尚往来数次后,钱泰勒熬不住了,主动找到我和陈柯西,要求伸手拯救后进生,以免我俩挂科拉低班级均绩。
“周六早上?真有意思。”陈柯西坐在我对面翻小说,抬抬眼皮。
“大学里能遇见这么负责任的老师已经不多了啊,抓点儿紧。挂了也不好。”我试图说服陈柯西。
“从小到大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不怕。”
“可是……还是去吧。”我承认我比陈柯西多点儿上进心。我倒是真不想挂科。
最终陈柯西还是被我拖着去补课了,也可能是因为她无聊,也可能是因为想见识钱泰勒到底有几把刷子。在数学方面我们都是响当当的铜豌豆,蒸不烂煮不熟,且看他能奈我何。
我们在东二教学楼找到了早已等候在教室的钱泰勒,他抬抬眼镜,搓搓手,单刀直入主题。
“来了?这是几道极限的题目,来做做。”
毫无悬念,陈柯西和我面对着那张纸陷入了漫长的沉默,仿佛一场无言的僵持。二十分钟后钱泰勒的表情终于挂不住了——于是陈柯西适时地抓起了笔,假装认真地写起了字。
我也学着她的样子,装模作样地写了几行。
……当然什么都没有写出来。陈柯西比我写的多点儿。
钱泰勒收卷,搓搓手,轻声叹口气。我差点没憋住笑,我觉得他搓手的动作像一只苍蝇。陈柯西站起来,面无表情地去倒了一杯热水,双手捧着回到座位上。
“你基本功不扎实,以后要多练。”他对我说。
然后他转向陈柯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做题的人。”
“柯西,真是可惜了你的好名字。”
我偷眼看她,陈柯西懒懒散散,并不说话。
“你喜欢数学吗?”一次补课期间,钱泰勒试探性地想从我俩身上寻找出学不好高数的心理因素。
“不喜欢。”陈柯西干脆地回答到。
“为什么不喜欢?”
“没什么。我家里曾经有很多竞赛课本,一看到它们我心烦。”陈柯西顿了一下,自言自语。“竞赛课本?”
陈柯西以为他想嘲笑自己,张口就想怼回去,突然看见面前钱泰勒露出悲伤眼神,猝不及防,把到嘴边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这个沉稳淡定的人脸上从未有过这种表情,浓厚的深沉的悲伤,令人吃惊的痛苦。
那悲伤只是一瞬,转眼间钱泰勒恢复如常。钱泰勒清清嗓子,开始搓手:“反正……反正你们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学好的。我们这所大学,虽然不是清华北大,但在国内也是能排的上名号的……你们都不笨!但是……”
陈柯西什么也没听进去。我也没听进去,他搓手的动作总让我联想到苍蝇,忍不住。
陈柯西想要一探究竟。
一周后陈柯西突然电话我,语气严肃:“小艾,晚上有空么?出来楼下咖啡馆。”
我收拾收拾出了门,陈柯西穿着一件黑色长大衣,严肃地抬眼看看我。依旧没有废话,依旧直入主题。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柯西?”
我这才知道陈柯西有个当数学竞赛专家的父亲,在五年前因酒驾车祸去世。那是一次数竞国赛的前天,同组的另一位专家被市委书记买通,请陈父喝酒,欲把他灌醉从而拿到存放试题房间的钥匙,泄题给市委书记的儿子。陈父嗜酒如命,自然中招。但即便醉意和困倦浪潮一般袭来,他仅存的意识仍然挂念着试题。没等酒醒彻底,他就上路返回。
于是车祸发生了。相撞的是一辆载着一家三口的车,据说他们那天就是送儿子去参加这场数学竞赛。那孩子热爱数学且聪明有恒心,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一定可以通过决赛,拿到名额,去到最好的地方去。
可那场车祸毁了一切。那对父母身亡,那孩子身负重伤。
那场车祸也几乎毁了陈柯西。
陈柯西知道残酷的真相后,第一次在黑暗中感受到深深的无力。市委书记的儿子成功了,不仅拿到了题目还失去了最大的竞争对手,他没有理由不成功。所谓象征真理的数学,竟像废品,甚至夺走父亲生命。陈柯西从此从心理上拒绝数学,最开始有意识地表达厌恶,到后来,便真的封闭了所有对数学开放的感官,一切与数学有关的事情再也做不好。
“还有。当时那场车祸中重伤的孩子,是钱泰勒。”陈柯西平静地说。
我一惊。
车祸之后钱泰勒心灰意冷,他放弃了自己的数学生涯。但他足够坚强,两年的痛苦过去后,他转去教书。他的水平还很高,基础也很扎实。他如愿以偿教起了高数,成了这所大学中年纪最轻的数学老师。他依然持续关注每年的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他已经走下了这个舞台,但仍充满着留恋与不舍。
“那你准备怎么办?”
陈柯西不说话,目光幽幽地看着窗外。
陈柯西想要帮助钱泰勒实现愿望。
当我察觉到这一点时,吓了一跳。以陈柯西的水平,求个简单极限都困难,别说去考竞赛,不够丢人的。
但是,陈柯西是一个极其有执念和极其疯狂的女人。
陈柯西开始疯狂刷题,我相信连高三最紧张的时候她都没这么用过功。她开始整个下午坐在自习室后面积分,积到日头偏西,积到我受不了了喊她吃饭。她去修微积分和数分的课,作业和考试照例痛苦不堪,但就是有一股子拼命的劲儿。她解矩阵,草稿纸上密密麻麻一片“1”和“0”,不知情的会以为来到了二进制的世界。
我站在她面前,悲悯地看着她。她摇摇头,我陈柯西有什么事儿做不了。
后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只知道现在不及格的人只剩下了我一个。陈柯西开窍了,在某一个不知名的晚上。
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陈柯西的突然开窍,我不知道她从数学中究竟窥见怎样的奥秘,因为这样的顿悟我不曾体验过,更无法得知陈柯西的心理。这种顿悟胜过佛祖,佛祖只是从混沌中寻得本质,而陈柯西可以解开纷繁困扰的谜团。昔日毫无头绪的符号和数字突然在她眼前变成了一条色彩斑斓的河流,如此通畅和干脆,充满着完美的巧合。
陈柯西的数学天才在疯狂显露,像一颗钝了头的锥子重新变的锋利无比。陈柯西从一团乱麻的数学题中揪出一个个线头来,扯着它们将整道题肢解。她的解题招数很霸道,很凌厉。她过关斩将,势如破竹。
一年后。
我早已不学数学,心中大快,但还留着钱泰勒的电话,偶尔聊聊天。陈柯西还像以前一样风风火火来去无踪,只有一点不同,如今她的数学,已经好到可以手撕大部分数学专业的学生。
陈柯西雄赳赳气昂昂去参加比赛了,临走不忘嘱咐我向钱泰勒保密。
一个早晨,我迷迷糊糊刷牙的时候接到了钱泰勒的电话。电话那头他激动万分,连声喊:“小艾你知道吗!发榜了!发榜了!我看到柯西,柯西了!”
我一个激灵,披了衣服跑下楼。钱泰勒等在楼下,兴奋地搓着手,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个动作。一种年轻的属于梦想的光彩,重新绽放在这个人脸上。
我看到陈柯西映入我的视线,穿一件灰色的长风衣,手上烫金的证书在阳光下分外耀眼。可真行啊!我心想。果然不愧是陈柯西,有什么事儿做不好。
陈柯西把证书交到钱泰勒手上,眉眼弯弯。
“谢谢老师了!多亏了你。”
钱泰勒激动地说不出话,只好更加兴奋地搓手。
这次我没有联想到苍蝇。
我联想到一个摩拳擦掌的勇士,以及为他实现梦想的守护者。
阳光下这样的故事,干净饱满像一颗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