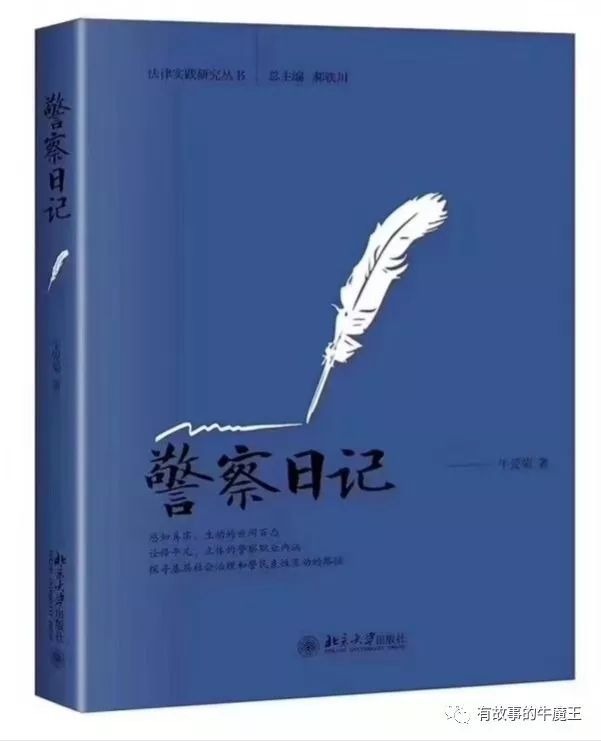1
我和方芳的故事,要从二十年前讲起。
过完十八岁生日,我给我妈留了张纸条,拖上行李离开家,用高考入学通知书,花三十二块半买了一张开往西安的火车票。
一座绿皮火车载着我,缓缓驶向未知的世界。这是我宣告成人的第一步,斩断脐带。我想象着我妈拿着纸条跟我爸絮絮叨叨抹眼泪的情景,心中充满窃喜,忍不住嘿嘿乐了。
我辈羽翼已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广大有志青年要到更广阔的天地施展才华。
西安的初秋,白天依旧带着夏日灼热的余温,夜晚却已沁凉入骨,我啃着白吉馍夹肉,在校园里四处闲逛。这是八月底,校园里四下无人,寂静无声。
我嗅到空气中丝丝绵柔馥郁的甜香,狠狠吸了两下鼻子,怎么北方也会有桂花?这难道不是我们江南的风物?东南形胜,三吴都会,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嘛。
我循着香气走过去,几株桂花树掩映在两幢灰色教学楼前,月色下影影绰绰,风吹过,细小的黄色花瓣飘落,夜静校园空,人闲桂花落呀。
且慢,花树下有人!还是俩人!还是一男一女俩人!还是俩大忙人!俩人正在忘情拥吻!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学啊,我吐了吐舌头,果然是兼容并包敢为天下先,我踮起脚,悄悄撤退。
我将手里最后一口肉夹馍吃掉,舔舔手指头,慢慢逛回宿舍,窗户大开着,风从对面的水房吹过来,将蓝布窗帘吹得飞起来。
后来的四年,我在这个水房看见过很多故事,有穿着民族服装的维族少女唱着情歌儿洗着冷水澡,有陷入爱河中的纯情小伙儿隔着铁窗将刚从食堂打回来的饭情意绵绵地递给意中人,有为情所伤的失恋姑娘在搪瓷脸盆里烧情书,......
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回味着肉夹馍的香味儿,考虑要不要在睡觉前刷牙这个世纪难题。
这时,门开了,一个穿黑色连衣裙的长发美女哒哒哒走进来,天哪,她居然穿着将近十公分的大红色细高跟鞋。我默默地看了一眼我的白球鞋,捋了捋我的小熊T恤,用崇拜的眼神儿看着她。女神就是用来崇拜的,不是吗?
“你睡我下铺?”美女撩了一下大波浪,一朵黄色的细小花瓣掉落下来,刚好躺在我的球鞋里。
“啊?”我欠起身子,勾起脑袋,往上看看,点点头,“啊。”
“方芳。你呢?”美女挑了挑眉,漫不经心地踢掉高跟鞋,染着大红蔻丹的白嫩脚尖从我的床底下,勾出两只拖鞋。
她的眉很浓很黑,眉峰高高的,有股男人的英气。“我叫米粒。”我看着她艳光逼人的大眼睛,有点眩晕,她居然还化了妆。
我被她强大的气场死死地罩住,心想,活了十八年的我也许需要找个男人确认一下自己的性倾向究竟有没有问题。
“你肯定是个乖乖宝,你妈很疼你吧?怎么舍得让你自己来报到?”方芳一边说话,一边交叉胳膊将连衣裙从下往上脱掉,浑身只剩下纯黑色的缎面文胸和丝质内裤。她在我面前那么自然地裸露自己,没有半点儿不自在。
她腰腹线条流畅,小肚子紧绷绷的,皮肤是成熟的小麦色,灯光下看来有淡而油润的光泽。
我想到自己小熊T恤下的卡通纯棉运动背心和短裤,决定周末去学校旁边的贸易市场给自己置办两套内衣,真正的女人穿的那种,海绵厚点也不要紧。
“嘿,这不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一唱雄鸡天下白嘛!自由都是争取来的!”我咧咧嘴。
“我是继院的,应该比你大几岁。你是法律系的吧?”
“妓院?”
“哦,继续教育学院,我们都叫继院。”方芳脸上绽出一个疏离的微笑,从枕头下摸出一根簪子,将长发松松挽了个髻,淡淡地说,“你挺好玩。”就套上一件吊带睡裙,端起搪瓷脸盆,去水房了。
我打量着白球鞋里那朵黄色的桂花,有点儿失神。
2
熬到国庆节,我妈还是憋不住了,跟我爸打着旅游的旗号,坐着火车来到西安。
“哪,熏鱼、酱排骨、马蹄酥、卤汁豆腐干、杨梅干,都是你最爱吃的......”这个中年妇女一边叨叨,一边从行李箱往外掏,好像那是杜十娘的百宝箱,怎么掏也掏不完似的。
我偷偷望一眼方芳,脸憋得通红,她又该说我是乖乖宝了,“妈,我不吃,你统统都拿走!”
“咦,你看你这孩子,好好的又闹脾气!”我妈摸摸我的脑袋,“该理发了哇,看这头发长的,都盖住耳朵了!”
“妈!”我使劲儿甩开,不耐烦地叫,“你能不能别啥都管啊?”
我爸拍拍我妈的肩,“行啦,闺女大了,由着她吧!”
“唉!”我妈叹口气,把行李箱拉上。
“走吧,跑了一天,你还不累?咱们回宾馆歇歇。”
“囡囡,你要不要跟爸爸妈妈去住宾馆?”
我看看方芳,她正气定神闲地端着大茶杯喝茶呢,氤氲的水气蒙住了她巴掌大的脸,看不清表情。
“不要不要,我还有好多事儿呢!”我拉着她就往外走。
送走这对离不开孩子的中年男女,回到宿舍,我看见方芳正在打电话。
我还以为她在跟男朋友煲电话粥,刚想怎么打趣她,却见她对着听筒吼起来,“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你什么时候相信过我,支持过我?我到底是不是你闺女?......你以后别给我打电话了!......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从我十三岁那年,我就没妈了!......你放心,我自己能养活自己,这几年,我不都过得好好的!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别被那老男人骗得找不着北!”
“啪”地一声,电话挂上了。红色塑料电话机挂在墙上,像个大大的铅笔盒。半晌,我的耳朵还在嗡嗡响。
我提起热水瓶,给她的大茶杯倒满水,小心翼翼地问,“你,还好吧?”方芳的塑料太空杯就像太上老君的宝瓶,少部分时间她用它来喝茶,大部分时间她用它来喝酒,啤酒。
她常常买两瓶宝啤(宝鸡啤酒)灌进去,刚好满满一大杯,她就那样提着它在校园里闲逛,哪怕是在马上要考法医学的中午。
学校图书馆后面有条所谓的美食街,其实也就是天南海北的小摊贩支着摊,贩卖各色家乡小吃。我和方芳最常吃的是油泼面,又宽又厚又筋道的面盛出来,洒上葱花黄豆芽,辣椒油烧得热热的浇上去,嗤喇一声响,香味儿就跟着响声出来了。那么大一海碗,只要两块钱。我吃完面喝面汤,方芳吃完面喝啤酒。
老板娘鸭蛋脸,头发挽得高高的,风情十足,有点儿像《武林外传》里的佟湘玉,每次我和方芳一去,都笑盈盈地招呼我俩:“两位妹妹,今天吃啥?还是油泼面,多要辣子?”我吃了两年油泼面,方芳离开以后再没吃过,被油泼面滋养出来的银盆脸,后来又瘦回了瓜子脸。
方芳若无其事地摇摇头,浓黑浓黑的眉毛挑老高,“没事儿啊,能有什么事儿?我好着呢!”
方芳将头发扎成高高的马尾,换上运动鞋,朝我歪歪头,“跑步去了啊。”
月满中天,我站在窗前,看着她窈窕的背影融在夜色里,觉得她真是一个谜,就像一个山洞,让探险的人想走进去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3
4月末的一个清晨,方芳用她的大长腿敲敲床板,“懒蛋,咱们去翠华山?”
我不耐烦地翻了个身,“哎呀,下午还有课呢,去什么翠华山?睡觉!”
“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爬起来,我去借自行车!”
我还没反应过来,方芳的大长腿已经踩到我的床铺上了。她身手矫健,每天拽着扶手,踩着我的床铺翻上翻下,像个跳高运动员。
“快点洗漱啊!”
“不上课啦?”
“不上啦!”等我迷糊过来,她已经洗漱完,从饭盆里拿出一个剩烧饼,啃着走了。
“说风就是雨!”我嘟囔着,弯腰找我的运动鞋。
路上我俩买了一兜桔子,一兜梨,两瓶水,两根火腿肠,两个烧饼,一边骑,一边吃,一路呼哧带喘的,到了翠华山,除了矿泉水,别的都消灭光了。
山顶有个湖,当地人美其名曰“天池”,我没去过新疆,但在我的心里,这个天池比新疆的天池更美。晚霞火红,湖水碧绿,映出天上洁白的云朵,方芳的眼睛泛着湖水的光泽,我很想问她和那个男朋友进展地怎么样了。
“米粒,你哪天生日?”
“六月二十三,温柔的巨蟹座。你呢?”
“今天。”
“啊?”同居这么久,我还是对她一无所知,“怎么不跟男朋友一起过,把我拽出来?”
“早分了。”方芳挑挑眉,她好像特别爱挑眉,一副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男人嘛,就那么回事儿。”
不到十九岁的我无言以对。
“你不会还没谈过恋爱吧?”方芳看着我,像打量外星人,眉飞色舞,“真是个纯洁的小白兔。”
我从没见过她这么快乐,“切,德性!”
方芳从车后面的大包里,变戏法一样掏出个帐篷来,“今天晚上咱们露营,明早再回学校。”
我第一次在家和学校以外的地方过夜,看着满天的星星,激动得结巴起来,“老天爷,真是,唉,真他妈的浪漫啊!”
方芳大笑,“哈哈哈,乖乖宝也会说脏话呢!”
“嘿,你别说,脏话说起来还真是爽!”我用胳膊肘碰碰方芳,“哎,说说,那个,谈恋爱是啥滋味儿。”
“哈哈哈,这个呀,你谈一回不就知道了?”方芳眨眨眼,两颗眸子像暗夜里的宝石一样,幽幽地放着光。“这水真他妈干净,我想跳下去洗个澡。”
“你疯了吧?这么凉,那边还有人呢!”
“怕什么?都睡着了!”方芳说着,就开始脱衣服,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穿着黑色文胸和内裤钻出了帐篷。
“靠,真是个二愣子!”我跟着钻出帐篷,看着她在湖边扭腰蹬腿。月光下的方芳,美得像美人鱼,那是一种最纯洁的美,让人一点邪念都没有,让人屏心静气,连呼吸都觉得是亵渎。
噗通!这只美人鱼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湖面上溅起大大的水花,一圈圈荡开去,我不由得叫起来,“当心啊你!”
有人从湖对面的帐篷里钻出来,搞清楚状况后,吹起了口哨。尖锐的口哨声划破夜空,惊飞了树梢栖息的鸟。
未几,美人鱼湿漉漉地爬上岸,双手捋了一把头发,朝我走过来。闪闪发亮的银河就在她的头顶,漫天星宿全都看着她,好像要哗啦啦地流泻下来。口哨声又响起来,跟着“啪啪啪”有人鼓掌,“漂亮!”
方芳像没听见,弯腰进了帐篷。
“水太凉,冻死我了!呼呼!”方芳迅速地把内衣脱下来,套上睡裙,“不过还真他妈过瘾!”
“浪漫!贼他妈浪漫,浪漫死了!”我激动地语无伦次,偶像就是偶像,我毫不掩饰对她的崇拜。
“今天真开心,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方芳伸出冰凉的手,摸摸我的脸颊,“谢谢你,米粒,我永远不会忘了今天。”
夜静春山空,我好像能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么安宁,又那么澎湃。那是我这辈子最浪漫的夜晚,春风沉醉的夜晚,恣肆浪漫的青春。我用半生的时间去回忆那个夜晚,将它在回忆中一遍遍发酵,一次次珍藏。
4
方芳神出鬼没,总是很晚才回宿舍,有时甚至夜不归宿。我不知道她天天在忙什么,有时问她,她也不说。有一天晚上,我上自习回来,她翘着二郎腿,坐在我床上抽烟,红色高跟鞋前面咧着嘴。
我在她旁边坐下来,轻声说,“买双鞋吧。”
方芳娴熟地吐出一个烟圈,“没钱了。律所把我辞了,让我考到证再去。”
“我借给你。”
“呵,小家伙儿。”方芳揉揉我的头。我的头发已经长长,清汤挂面一样披在肩上。
方芳到底没肯用我的钱,她说她有办法。
国庆节又到了,我俩决定去爬华山。“就咱俩行吗?最好有个男生帮咱背包。自古华山一条路,听说险着哩,万一咱俩有个好歹,也有人帮咱收尸不是吗?”
“这个好办,交给我。”方芳打开电脑,在校园BBS上发了一条招募男旅伴的动态。
出发那天黄昏,我在学校大门口见到了方芳招募的旅伴,是个帅哥,经济法系的师兄。他反戴着一顶李宁的红色帽子,手插在牛仔裤兜里,书包随意地搭在肩上,闲闲地站在那里,夕阳温柔地打在他身上,使他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温柔的气质。
我的心怦怦地跳,像要跳出胸膛。我张了张嘴,发觉嗓子有点干,拧开矿泉水瓶,咕咚咕咚胡乱灌了一气。
方芳走过去,挑挑眉,“马骏?”
“是。方芳?”
“是。呵,我们是不是该对个暗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之类的?”
帅哥笑了。夕阳暗了。我的嗓子更加干,干得我说不出话来。后来我回忆从前,好像我和马骏在一起那大半年,我总是会紧张,有时紧张得不知道说什么好,生怕一说出口就错,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浅薄。那是我的初恋,像一颗酸涩的葡萄。
马骏很自然地把我俩手里的包接过去,我们仨上了去华山的火车。
从火车上下来,天已经黑了,那么大一轮月亮挂在天上,黄黄的,像观音菩萨的脸,悲悯地看着人世间。那年的国庆节,刚好赶上中秋节。
一条小溪顺着石板路边的凹槽从山上流下来,我们沿着溪流一路往上走,瓶里的水喝完了,就灌满溪水。越走包越轻,腿却越沉,路上有商贩叫卖红绸带,马骏买了一条,系在脑门儿上,“不到华山非好汉”几个大字赫然在目。
“像日本武士。”我说。
“什么?”马骏看着我,眼睛亮亮的。
我指指他的脑门儿。
“哦,哈哈哈。”他笑起来,一口整齐的白牙看得我眼晕。
到了天梯脚下,一条长长的铁锁链从上面搭下来,有人拽着锁链往上爬,锁链就离开山体,悬在半空中,看得人心惊肉跳。马骏回头看我俩,“我先上,你俩跟上?”
方芳不在意地点头。我的双腿开始哆嗦,后悔答应方芳来爬华山。
他俩都上去了,趴在崖上喊我:“牛,快上来!不怕!”
不怕?鬼才不怕呢!
我咬紧牙关,拽紧锁链,死死地瞪着眼前的天梯,一格一格往上爬,默默地数数。数到第九十九,终于到顶了,马骏朝我伸出手,我把自己的手放进他的手掌里,翻了上去,瘫倒在地。
“吓坏了吧?”马骏脸上露出关切的神色。
我咽了口唾沫,没说话。
“我俩在上面猜了半天,看你不上来,还以为你要返回去呢。”方芳冲我眨眨眼。
经过“鹞子翻身”,方芳想去,被我死死拉住了。
到达山顶的时候,忽然飘起雪花,马骏从背包里拿出一件羽绒服,递给方芳,方芳又递给了我。羽绒服温暖干净,有主人的气息,我穿在身上,身体被包裹住,有种小时候穿爸爸衣服的错觉。
下山时,步子轻快很多,我们一路跑下山。到了火车站,刚好一列绿皮火车冒着气鸣着笛进站了。
车上已密密麻麻载满了人,车门刚开了三分钟就关上了,我们根本没上去。“怎么办啊?”我都快哭了。
靠车窗的一个中年男人看着下面上不去车的人,幸灾乐祸地笑。
“爬上去!”马骏把书包扔进去,扒着车窗钻了进去,朝下面的我俩伸出手,“快点儿!”
方芳看着我,“你先上,我托着你屁股!”
我咬咬嘴唇,事到如今,只能豁出去了。我双手扒着车窗,方芳在下面托着我的屁股,马骏在上面拽着我的胳膊,愣是给我拽进去了。方芳倒是身手敏捷,跟爬上铺一样爬进来了。那个幸灾乐祸的中年猥琐男,看着我们仨,惊得目瞪口呆。
火车鸣响汽笛,缓缓驶出站台,载着我即将开始的初恋。
5
从华山回来以后,我无心学习,每天都在苦心钻研泡男大法,废寝忘食,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我让方芳教我化妆,问她怎么让男人爱上自己。
“不知道啊。你是不是看上谁了?”方芳轻描淡写地说。
我脖子一梗,“才没有呢。”
话虽这么说,还是挡不住我偷偷跑到马骏他们系上课。我对方芳说我要考经济法系的研究生。“刚大二就考研,你可真是未雨绸缪啊。”方芳头也不抬地刷着律考真题,心不在焉地说。
我在校园BBS上搜到经济法系的课表,对马骏的行踪了如指掌,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深秋的太阳从窗户洒进来,老教授低沉嘶哑的讲课声实在太催眠,为了抵制睡神的诱惑,我在板凳上扭来扭去。突然,崩的一声巨响,凳子不知怎么断掉了,我整个人猝不及防摔了个屁股蹲,坐在了地上。
虽然我那天挑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全班几十个人的目光还是齐刷刷落在了我的身上,紧接着,雷鸣般的笑声响起来。最悲催的是,马骏的目光也从教室那头穿过人群,落在了我身上,当然,又迅速收了回去。
他竟然假装不认识我!
老天爷,他一定觉得我太丢脸了!
哦,老天爷,我也觉得我太丢脸了!
可恨的是,慈祥的老教授还不肯放过我,“快起来,这位同学,你不要紧吧?”
我迅速立刻从地上爬起来,坐到了旁边的座位上,并且假装无所谓的样子,镇定地上完了一堂课。虽然,我的脸已经烧到了脖子根儿。
下课铃声响了,我迟迟坐着不肯动,一直等到全班同学都走了,我才四下望望,慢吞吞地收拾书包站起来,咦,怎么马骏还没走呢?
他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走到我旁边,“给,帮你抄的笔记。”
我像坐上了直升飞机一样,从地狱窜到天堂,他竟然真的以为我要考研?!嘿嘿嘿!阴谋得逞!
我和马骏肩并肩走出教室,走过操场,小伙儿在踢球,姑娘在跳操,夕阳温柔地将我俩罩住,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这段路不要那么快走完。
经过一个小水坑,马骏朝我伸出手,温柔地对我说,拉你过来。
他的眼睛那么亮,他的牙齿那么白,他的声音那么温柔,我恍惚又回到了华山那个中秋夜。
那天晚上,我激动地睡不着觉,终于等到方芳回来,迫不及待地跟她分享我的心事,“你第一次和男朋友牵手是啥感觉?”
“第一次牵手?忘了,几百年以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方芳迷迷糊糊地说,“我忙了一天,累死了,快睡吧。”
我心灵澎湃的波涛撞到了冰冷的礁石,恨恨道,“哼!”
我终于迷糊着,却被一个毛烘烘热乎乎的东西吓醒了,它从我手上爬过去,吱扭一下不见了!
“啊!”我尖叫着从床上跳到地上,气冲丹田,直刺九霄。
“受啥刺激了?大半夜的!”方芳被我叫醒了。别人也许也醒了,却都继续寻觅周公,对我的悲惨遭遇不闻不问。
“老鼠!老鼠刚刚从我手上爬过去!”
“哦,不就是个老鼠吗?”方芳轻描淡写道。
“你到底有没有点儿同情心啊?”我委屈地扁着嘴。
方芳已经从上铺翻下来,打开了灯,拿起了扫把,“别委屈了,我帮你抓老鼠,这个我最在行了。”
方芳把褥子一层层卷起来,又把门缝下面的小洞拿一团团的棉球蘸饱了水堵上,“这个洞做个记号,明天去宿管处找工人用水泥堵死。”
老鼠到底也没抓着,方芳却从我床底下变出两罐啤酒来,在唇边竖起食指,小声道,“反正也睡不着了,咱俩喝酒哇?”
我俩一人一罐啤酒,走到水房。
“我老家在乡下,9岁的时候,我妈跟我爸离婚了,我爸爱喝酒,一喝酒就打人,打我妈,也打我。我妈带着我搬到镇上,借钱开了家小餐馆,我放学在餐馆的桌子上写作业,晚上桌子擦干净,拼起来,铺上被子就是床。餐馆油多啊,老鼠就成了我的小伙伴儿,我常常被老鼠吓得睡不着。我妈累死累活挣到的钱,也仅仅只够给我做学费。”方芳幽深幽深的大眼睛,像两口深井。
我不说话,安安静静地听。
“我妈年轻时长得很好看,老有男人借着来吃饭,揩她的油。我12岁那年,有人给我妈介绍了个男人,是镇上税务所的,老婆出车祸死了。男人长得还不赖,对我妈也不赖,常常带客人来店里吃饭,男人把铺子连同楼上两间都买下来送给我妈,我妈就嫁给了他。男人脾气很好,对我也很好,给我买巧克力,辅导我功课,从不打我。我都开始叫他爸爸了......”方芳说着说着,突然停住了,仰头咕咚咕咚喝起了酒。
我听她没说完,忍不住问,“后来呢?”
“后来?哼!”方芳冷冷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森森的冷意,让我在深夜里不禁打了个寒颤,“后来啊,他们又生了个儿子,我也慢慢长大了,长成了叛逆少女,离家出走,到处瞎混,混到了今天。”方芳将喝光的易拉罐使劲儿一捏,那声音在深夜里听起来格外刺耳,易拉罐已经被她捏得变形了。
“我们每个人就像这易拉罐一样,被生活强奸得面目全非。”方芳把易拉罐往墙上狠狠掷去。
“咣啷啷”,瘪易拉罐在地上转了几个圈。
6
我不知道我和马骏的关系算什么关系,普通朋友?好像不止;男女朋友?好像又算不上。我约他打球看电影,他也去,可是我们却从没说过太私密的话,更别提特别亲昵的举止。我和他最亲密的身体接触,还是那次过水坑前他拉我那一下子。
都说女追男隔层纱,可我怎么总觉得我是在隔靴搔痒,挠不到地儿呢?而且平时伶牙俐齿的我,不知怎的,一到了马骏面前,总是笨嘴拙舌,不知道说什么。太在意时,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唯恐不小心打碎了手中的琉璃,其实,时过境迁才发现,那不过是个自己给自己编织的绮梦。
过完春节,我坚决拒绝了我妈的美食诱惑,提前一周返回西安,不知道方芳过得怎么样,她这个春节又没回家。她已经顺利通过了律考,找了个律所打工,过完这个学期,她就要毕业了。我总觉得她的身上包裹着一层厚厚的铠甲,那是她不愿提及的过去和伤疤。
回到学校,已经快半夜了,我背着沉重的背包,蹑手蹑脚地走到宿舍门前,想给方芳一个惊喜,背包里装的全是妈妈给方芳带的好吃的。你那个好朋友,还怪让人心疼的,妈妈听我说了她的身世后,长吁短叹。
我拿出钥匙刚要开门,却听见里面传出奇怪的动静,好像是女人的叹息声,可是那声音听起来却又压抑又难受,末尾还带着拐弯,像一个低音迂回婉转后,又挑高了上去,想要迎合什么。
我心里嘀咕着,难道方芳生病了?可是这跟她那次发烧的呻吟声也不大像啊。我轻轻转了转门把手,门竟然没锁,这家伙,怎么忘了锁门,也不怕小偷进来。
两双鞋躺在我的床前,一双红色高跟鞋,一双黑色皮鞋,男式的。我认识那双鞋,黑色系带的,男生都那么懒,只有马骏才会喜欢这种系带的。我往上看,酒红色的帐子围出一个独立的国度,我终于明白过来,那个国度里,正有一双有情人在做快乐事。
窗帘没拉,白月光洒满一地,我静静地站在那儿,闻到空气中浓浓的情欲。
那叹息声越来越细,越来越高,高得像喘不过气,高得像要断了,中间夹杂着低沉的男人的喘息声,上下铺微微地有节奏地晃,终于,叹息声到了最高潮,缓缓地舒了一口气,潮退了。
原来,他对我若即若离,只是因为,他的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而那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偶像。
我将背包卸下,转身跑了出去。
“米粒,米粒......”我听到方芳在后面喊我,我没有回头。
天空不知何时,飘起了雪花,洁白的雪花刚到地上,就融化不见。雪越下越大,地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雪,车轮碾过一道辙,把雪碾成了污泥。林黛玉想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多么可笑啊,这世界有干净的东西吗?
方芳试图想接近我,都被我拒绝在无形之外了。那夜之后,我们已经很久没再说过话。
有一天我回宿舍,她们几个本来正聊得热火朝天的,突然看看我,都不作声了。
“米粒,你那个万人迷好朋友咋不见影儿了?”
我冷冷打量一圈,没说话。我讨厌背地里嚼舌头的女人,太俗。
“哎哟,你还不知道吧?人家跟继院院长搞上了,都被院长夫人给抓着现行了!”
“真的真的?”
“不对吧?好像是说她想勾引继院院长,没勾引成呢,就被院长夫人给发现了,扼杀在萌芽中了!”
“妓院?呵,那儿能有什么好鸟?男男女女都是考不上大学的混混!”
“就是!怎么还让咱们跟她一个宿舍?真是恶心!”
“哎哟,人家可是万人迷呢!知道咱们系多少男生追过她吗?”
......
“行了啊!菜场大妈才背地里嚼舌头呢!”我冷冷地甩出一句,转身出去,“咣”的带上门。
我在我俩常去的河边找到方芳,她坐在草地上,脚边扔了一地的烟头。
“她们说的是真的吗?”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有时候,我觉得一点儿都不了解你。”
“我是院里的教学秘书,他让我去帮他做课件,我还没做完呢,他就对我动手动脚,我刚要走,他老婆就来了。”方芳狠抽一口烟,“他对他老婆说我勾引他,他老婆就抓我脸,然后就给院办打电话要求开除我。”
“我相信你。”
“米粒,你是蜜罐里泡大的孩子,你永远不会知道,生活有残酷,人心有多龌龊。”
“会过去的。你不是已经拿到律师证了吗?”
“嗯。没什么大不了的。”方芳扭头看着我,“你喜欢马骏?”
我咬着嘴唇不作声。
“他不适合你,米粒,你会遇到真正爱你的男人。”
“你爱他吗?”
“爱这个字对我来说,太沉重了。我只是需要温暖。”
我们望着天边入血的残阳一点点隐去,天空从粉紫变成深蓝。三个月后,方芳毕业,离开了校园。
7
起初我还能断断续续接到方芳的邮件,后来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她带我去逛商场,“马上要毕业了,好好捯饬捯饬,别老跟个小孩儿一样。”
我看着镜子里她捯饬出来的我,清新如朝露,那真的是我吗?
我真的考上了研究生,来到了北京,遇到了爱我的男人。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方芳,她在哪里?还在西安吗?她过得好吗,有没有遇到她爱的人?我还能再见到她吗?她没给我讲完的故事,什么时候会给我讲完?
方芳说,世界是一个圆,而她是残缺的。谁能给她圆满?还是,这世界从来就没有圆满?
周末我带儿子去五道口上画画课,上厕所的时候我一个没注意,就听见儿子跟谁叫起来了,“我没碰她,她自己摔倒的!”
这个臭小子,一会儿看不见就出状况,我赶紧提上裤子跑出来,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儿坐在地上哇哇大哭,一个衣着入时的妈妈蹲在那儿耐心哄她:“囡囡不哭哈,小哥哥也不是故意的嘛,你就原谅他好了?”
我慢慢靠近,细细端详,“方芳?”
她慢慢抬起头来,看定我,半晌才缓缓道:“米粒?你真的是米粒?”
方芳还是那么美,却美得更加厚实了,眼睛不再像深井,眼神柔和了不少,眼角的细纹让她看起来更加有烟火气。她是个中年妇人了。
我紧紧攥着她的胳膊不敢说话,生怕还没开口先掉下泪来。
小女娃看着我们忘了哭,儿子如释重负,拉着女孩儿跑一边儿玩去了。
“这么些年,你跑哪儿去了?我还以为再也不会见到你了。”
“你儿子都那么大了?你还是跟从前一样,一说话像个长不大的小孩儿。”
“九岁了,你闺女呢?”
“6岁半。怎么你自己带孩子出来?你老公呢?”
“加班。你老公呢?”
“离了,没有。”
我停住,看着方芳略带沧桑的脸,那美丽的脸孔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受了很多苦?”
“嗐,都过去了,现在还好。所里有我一点儿股份,我没有那么辛苦了。晚上有没有安排?去我家?”
那天晚上,方芳将她没有讲完的故事讲给我听。
“我十五岁初中毕业考上中专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边打零工边上学,当自己是哪吒,自己把自己重新生养一回。那个我叫他爸爸的继父,在我十三岁那年强暴了我。
妈妈出去进货,我在楼上睡觉,睡到半夜,一尺多长的大老鼠从我脸上爬过,吓得我尖叫,他就从隔壁跑来哄我,起初是抱着我,后来就开始摸我胸,说要好好疼我,我懵懵懂懂就被他破了处。他说他是真心疼我,跪下来求我不要告诉妈妈,不然这个家就毁了。我哭了一夜,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后来只要妈妈不在家,他就哄骗我,说只要我答应他,他就一辈子对我们娘俩儿好,不让我们娘儿俩受委屈。
我看着他人前人后两张皮,各种花言巧语哄我妈,变得越来越暴躁,我妈还动不动骂我不懂事儿,不知道惜福,逼我叫他爸,逼我给他端饭洗衣服,我终于忍不住,在跟我妈吵架时全说了出来。我妈不相信,打了我一巴掌,骂我小婊子,小小年纪不学好,净学别人勾引男人,说我见不得她好。
我离开了家,再也不想看见这两个人,不想看见我妈,无论如何,只要她过得好,就好吧。她打听过我的下落,给我寄过钱,我都没去取,原路退给她了。”
方芳平静地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我觉得脸上麻痒麻痒的,伸手一摸,手上却湿乎乎的。
“什么时候来的北京?怎么会离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你不好?”
“来北京也有十年了吧。他是原来律所的同事,在一起工作久了就有了感情,他想来北京闯闯,我就跟着过来了。反正那么多年我天南地北也跑习惯了。他自己创业,越来越忙,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少,就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这么美,会有好男人爱你。”
方芳哑然失笑,“我不会再结婚了,囡囡那么美好,我害怕人世间的任何风险降临到她的头上。”
我知她的意思,喉头一热,半晌不语。
她看我眼眶红了,反倒笑了,“我现在真挺好的哇,你看,我再也不会为钱发愁,不用穿开了胶的高跟鞋了。”
我想起她那双咧着嘴的红色高跟鞋,笑了。
“你比以前快乐了。还抽烟吗?”
“戒了,对身体不好。活明白了,不跟自己较劲了,就快乐了。你不是别人,我也不瞒着你,我有一个男朋友,不过囡囡不知道,我从不带他到家里来。”
“他是做什么的?人怎么样?你会跟他结婚吗?”
“也是律师。他很爱我。”方芳挑挑眉,“不,我不会跟他结婚。我不会再跟任何人结婚。”
“方芳,你还是你。”
方芳摸摸我脑袋,“你也还是那个你。我们,都还是从前的我们。”
“米粒,你还记得马骏吗?”
“嘿嘿,怎么会不记得?那可是我的初恋啊!”
“上个月我在国贸看见他了,手里推着婴儿车,怀里还抱了一个!老婆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数落,那样子真是狼狈透了,你知道吗,他现在头顶都快秃了,肚子也那么大......”
“哈哈哈,是吗?幸亏那会儿没成,我最受不了男人大肚子,干那事儿都不利落!”
方芳目瞪口呆看着我,“老天!我们的纯情小白兔啥时候变得这么豪放了?”
我俩哈哈大笑,笑得俩孩子直瞅我们,还以为我们神经了。
春天的阳光洒满宽敞的大厅,将屋里照得明亮耀眼,像金灿灿的青春岁月。我俩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看着旁边搭积木房子的孩子们,絮絮叨叨,说着过去和现在,任凭地老天荒。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时光在变老,我们在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