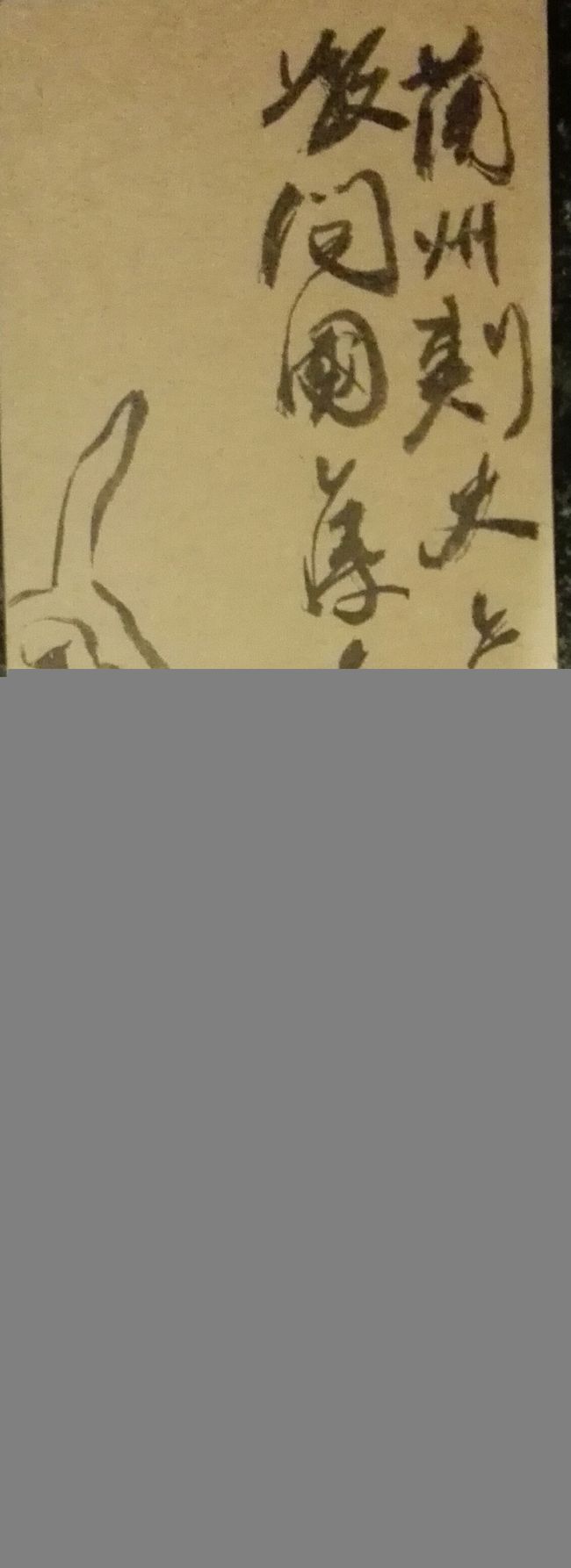引论:铁打的文吏流水的官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但衙门里的文吏变动不大。自古文吏与文人、官僚与大儒之间,存在着思想和行为的矛盾冲突。
文吏是现今的公务员。官僚依然是官僚。大众的日常社会活动与公务员的行为相互作为,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文人,与大众互动很少。因此,我们大多数人的思想来源,都被改造成了“文吏的哲学”。
本文以王充关于文人、文吏之辨入手,讨论被文吏偷梁换柱的儒生社会群体的问题。
许多人指责的儒家思想,其实是“文吏的哲学”。中国千年的历史,改朝换代都是浮云,独独有那些文吏坐着铁打的衙门。
是故,不该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而该是“文吏不死大盗不止”。
(一)王充的“文吏与鸿儒”
儒学的具体思想,不能脱离具体历史现实中的社会阶层这一思想载体来讨论。
儒生是儒学的主要传承者。然而儒家思想的影响范围却不仅限于儒生。儒生阶层在“独尊儒术”的统治策略的确立下逐渐形成。儒生的社会群体伦理规范在与文吏的群体矛盾中得以明确。
王充《程材篇》针对时弊指出“世俗共短儒生”。因为“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所以,以现实的政治活动与行政工作对于统治阶级成立的功利标准加以衡量,世俗“归非于儒生,付是于文吏”。
尽管如此,“儒生治本,文吏治末”,儒生所能够发挥的“轨德立化”“移风易俗”的社会影响,确是文吏不可能做到的。文吏只会对官僚一味顺从,迎合,苟且。所以为官者好文吏而不喜儒生。
《说文》解“吏者,治人者也。”法家韩非有“吏者,民之纲本也”“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汉朝独尊儒术被人视为“外儒内法”。所以有观点认为,儒生与文吏的社会群体矛盾是政治上礼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之争。事实不尽然。
文吏的存在会放大“人治”在“治人”上的种种弊病。而儒生则以“治世”为指向,以“文治”矫正人的行为。
王充著《问孔》《刺孟》《书虚》等章,提倡“非圣人教告乃敢言也。”并针对当时儒生群体的堕落与对权贵的附庸,提出“文人”与“鸿儒”的概念,强调鸿儒当“著书立说”。这些观点,对统治阶层通过“经学”迂腐儒生治世意识的手段是一种思想上的反抗。
因此,儒生的社会定位,本质上是以一种“古代社会的民主”来权衡官僚与大地主的阶级统治对社会和谐带来的破坏。儒生群体的存在对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巩固作用正是在于儒生群体对大官僚大地主的制衡作用。
(二)天下何以无道?
社会的综合治理,在文吏的参与和儒生的缺席的前提下,只可能因为“道”的缺失而自行衍向乱世的衰亡。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文吏与官僚构筑的政治文化彰显着人性最为不堪的丑恶。只是任何社会群体所必然具有的行为规范,在古代“外儒”与“尊礼”的氛围里,被熏染出符合“孔教”的伦理道德。
文吏与官僚也有属于他们自己阶层的“礼义”与“道德”。他们的礼义不过是牟取更多利益的幌子。
然而统治阶级并不会因为儒生能够具有的对社会和谐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而积极推动儒生自身所潜在的这种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
儒生的仕途被纳入官吏制度之内的过程,就是儒生阶层被剥夺社会独立意识的过程,也是儒生阶层沦落为附庸阶层的过程。
汉朝面临历史遗留的贵族威胁中央集权的问题。汉朝的发展遭遇了士与宗族结合形成的士族的壮大带来的威胁。士族门阀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
儒生在权贵官僚的政治博弈中被制度化。班固曾对儒相与儒师做出过一针见血的评价:
“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士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直至唐朝科举制度的建立,士族门阀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然而士族的传承并未根除。
寒门与士族之间的斗争在士族之间的政治斗争面前微不足道。朋党之争的本质仍然是士族之间就科举问题的利益冲突。
士族对文化知识的把持使得佛老思想在享乐与庸俗的格调里泛滥。正是因为这一文化危机,韩愈才会提出儒家“道统”的问题,以此抵御佛老思想对儒生群体的侵蚀。
由于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进而对思想界话语权的垄断,儒生逐渐在思想文化上暴露出成为士族附庸的趋势。
晚唐那些轻浮的诗人大多靠在权贵的宴席上吟诗以博得名声。
从朱熹到王阳明,再到王夫之,他们的思想无不针对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文化中儒生阶层的堕落化与庸俗化所产生的落后思想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然而他们各自的思想最终又在儒生阶层进一步的堕落与庸俗中被消解得变了样子。
统治术的关键,在于将所有的异己纳入自己的体制内。这个措施的实施,在社会心理上,首先要认可异己的存在。认可的程度,是将自己与异己做出矛盾的协调与本质的混淆。混淆的基础,就是自己社会利益在分配环节对异己的接纳和让步,简而言之,就是用经济手段。这个方法不仅被用于儒学,也被用于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学不再是儒生的社群文化标识,儒生反而是儒学的阶级人群载体。随着群体社会功能的明确和社会地位的稳定,儒学因儒生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性质,而成为社会文化中具有反思社会、改造社会的潜质的要素。
也同样因为儒生社会群体的明确与稳定,儒学因儒生的附庸阶级的性质,而沦为虚假的空谈。其对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被话语的空谈而切断,其内涵被悬置于社会现实的生活之上,而不得不遁入祠堂忍受香火。
儒学的遭遇与儒生的命运,在儒学的思想内涵里已然存在。
统治阶级通过推崇儒学的政治行为,将儒学变成一个符号。这个符号,经由民间文化中的传统道德为媒介而被民众接受;经由仕途的科举制度而在读书人群体中成为了内涵里只是现实政治要求的符号。儒学是统治者用于对读书人示好的符号。
取仕的读书人在对儒学风潮的主导中,潜意识地为儒学植入了统治者的政治要求。在儒生作为取仕的读书人这一群体时,儒学只是儒生不断在以文化阐释的政治利益。
因此,儒学的历史,是儒学的符号化与儒学的归本相斗争的过程,是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儒生与作为政治附庸的儒生相互斗争的过程,是阶级统治干预社会进步文化与社会文化核心反抗社会异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