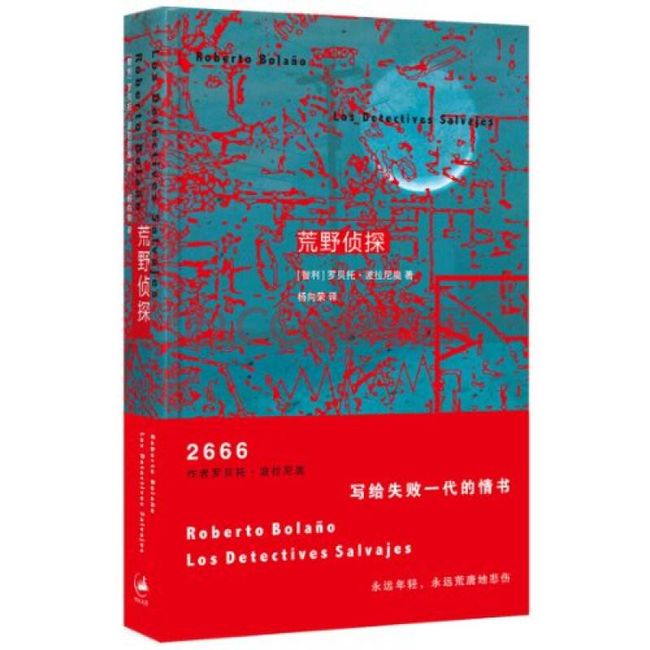他是拳击手的后人。拳击手擅长使用拳头,擅长在拳台上挫败对手,但他将整个生命意志转化成拳头,与独裁政治势力搏,与魔幻现实主义斗,与超现实主义诗人拼,与旅途一切牛鬼蛇神争,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他才是真正的拳击手,才是真正的骑士,像极了唐·吉诃德。
1.
有时候你会被你喜欢的东西吓着。罗贝托·波拉尼奥与我而言,便是如此。
作为普通读者,我被他的《2666》和《荒野侦探》吓着了,被他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和《美洲纳粹文学》吓着了,被他字里行间的诗意和幽默和醉意和灵魂起飞吓着了。
他手中的笔和脑海里的念头转得一样飞快,我怕这一辈子都跟不上了。
我所着迷的只是一种凝视他灵魂起飞后的附着物的虚拟状态。
他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所走过的路,在于他在这些陌路和生死路上所享受到的刺激和快乐,他的身体从来不是静止状态的,正如我们的身体从来没有真正意义飞扬起来。
他将灵魂安放在脚下的世界,而不是被水泥磁砖钢筋地板和设计师泥水匠建筑起来的房子;他是宁愿做星空下跳舞、葡萄架下睡觉、建筑工地守夜的流浪汉,也决不会做五星级酒店泡牛奶浴的花花公子或精致利己的中产之徒。
他选择一种生活,并选择将这种生活进行到底,并选择将选择的生活奉为信仰,其他的,见鬼去吧。他可以活在风里,活在寻找诗歌的醉生梦死里,活在大地的荒芜和天空的无常中,活在病魔的肆虐和折磨中,也不会躲在某个角落慢慢呻吟,慢慢腐烂。
他是拳击手的后人。拳击手擅长使用拳头,擅长在拳台上挫败对手,但他将整个生命意志转化成拳头,与独裁政治势力搏,与魔幻现实主义斗,与超现实主义诗人拼,与旅途一切牛鬼蛇神争,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他才是真正的拳击手,才是真正的骑士,像极了唐·吉诃德。
2.
七十年代的智利政变是他一生当中的核心事件。他一生都没有从中走出来过。这既是他流亡的序曲,又是他命运的原声。
聂鲁达是他诗歌的领路人,精神之父。他怀念他又憎恶他,他敬仰他又摔碎他,他吟诵他又背叛他,他曾躲在他的诗歌王国里,又想一念之间将这个王国摧毁殆尽,就像艾青之于北岛,北岛之于韩东们。
他们是路标、灯塔、丰碑;他们又是风的阻挡、海的监控、刀斧的禁区。他们的叛逃之路,流亡之路,革新之路,你可以理解为:狂风刮倒路标,海啸淹没灯塔,刀斧砍向丰碑。
他走向老路,也是走向新途。这条从拉美出发的漫路,从前有聂鲁达、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帕斯、略萨,如今有安布埃罗、波尼亚托夫斯卡、伊莎贝尔们,而后面的追随者依然如流水奔腾。波拉尼奥只是这条流河里最受伤的一条鱼。
3.
有时候你会被你喜欢的东西吓着。我确实被他吓着了。
去年我几乎读完了他所有的小说。(这里指读书市场能买到的中文版本。)我想写一篇关于他的东西。想写得很长很长,写得很好很好,将所有的热爱都倾注其中,将所有的发现全盘端出,将肺腑凝聚的力量全部用上,我想写得对得起《2666》《荒野侦探》这样堪称鸿篇巨制的文字。
但随即我却陷入了“杰夫·戴尔定律”。正如孔亚雷在《极乐生活指南》介绍杰夫·戴尔定律所说的那样:
“我是那么地渴望写好这篇文章,以至于不可能写好这篇文章。”
我几次动笔,又几次搁笔。动笔和搁笔之间,多了一些碎片,一些慰藉,但离一篇成型的文章,好像还隔着巴拿马和地中海。
我一次又一次重读,一次又一次死灰复燃。但想得越起劲,后面将这种劲压抑后,就越痛快。我几乎开始绝望。绝望后,我开始读点其它的东西来转移视线。
等灰烬余温尽消之后,那种杰夫·戴尔的魔咒又涌上心头。我开始想着,还有一篇关于波拉尼奥的长文等待我去完成。
4.
从前是在读《护身符》,突然想到北岛的《蓝房子》,赶紧将它找出来;从前是在读《邀舞卡》,觉得有必要读点聂鲁达,又赶紧将后者的诗歌、随笔、传记找出来;从前是在读《荒野侦探》第一部分,觉得有点像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随即,又从书架上将它拨拉下来;从前是在读《美洲纳粹文学》,看了篇书评谈及博尔赫斯和他的有关作品,又开始读起《恶棍死传》。
一次次沦陷,又一次次逃离。
因为他是智利人以及译者同是赵德明的缘故,我找到了智利作家罗伯托·安布埃罗的《聂鲁达的情人》《希腊激情》和《斯德哥尔摩情人》;因为他鄙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我又找出《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和马尔克斯的旧作来读;因为他说自己是诗人,自己的诗人比小说要好,所以又想,我应该读点拉《拉丁美洲抒情诗选》这样的作品。
书越堆越多,人越陷越深。
我逐渐感觉自己从波拉尼奥的漩涡逃脱,又陷入另一个“拉丁美洲”的黑洞。我啃着《拉丁美洲文学简史》和《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的时候,我发现,我用大堆大堆的作品名称和拉美文学史上的作家名单以及文学史家枯燥无味的海量文字,来替代和弥补因为写不出那篇关于波拉尼奥的文章而引发的“后遗症”:焦虑、半焦虑、三分之一焦虑、无影无踪的焦虑。
后来演变成另一种情况。
我几乎读什么都会想到他。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作品,散文还是诗歌,我会以他的眼光来评价,这个他肯定会喜欢,那个他肯定会鄙视。这部书或许会写进他的下一部作品;那部书他说不定会朝它吐上几口浓痰,还大大咧咧地说:
“我真写不出这种让人脸红的东西。”
如果是小说家,我会以他为标准,絮絮叨叨,比他差一点,比他差一大截,比他差了不止是一大截,而是一万光年;或者,比他好一点,比他好一丁点。比他好一大截?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文艺青年,我会以他作品里的人物为标准,这个像谁,那个又像谁,这个有点贝拉诺的影子,这个有点利马的味道。
即便是那些喜欢旅行的作家,我也会拿他当把尺子。
迄今为止,村上春树、科尔姆·托宾、扎蒂·史密斯,这些喜欢旅行的作家,也喜欢从一个地方归来后随手写点游记随笔这类作品的大家,他们应该还没有像他那样跑过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地方;亨利·詹姆斯、杰克·凯鲁亚克、V.S.奈保尔这些旅行作家,或许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中文作家里,北岛和阿城在世界版图上留下的里程,减出他在拉美、在欧洲、在非洲的人生旅程总和,应该还有余数。
5.
他一生看起来很短,五十出头就走了。但你读他的作品,了解他的人生种种细碎的话,又感觉他这一生,过得真是丰盛而漫长呀,过得真是够本了。
他从智利到墨西哥。在墨西哥,从东部到西部,从中心之城到沙漠边陲。
从墨西哥到欧洲。大大小小的国,大大小小的城,招之即来,呼之就去,坐地铁,开汽车,搭便车,哪种方便,就选哪种。没钱买机票了,就在巴黎的老乡家,蹭住、蹭吃、蹭书读,管他春夏秋冬与成家立业。
从一国流浪到一国。他这一生,做过船工,做过守夜人,做过采摘葡萄的短工,做过酒吧服务员,做过流浪汉,做过记者,做过赚取奖金的文学奖投稿人,做过文学研讨会上的嘉宾,做过医院里的病人,做过被异国女人深爱的男人,做过两个男孩的父亲,做过被电视台采访的作家,做过文学大奖得主。
他和凯鲁亚克和考布斯基和卡佛拥有一样又不一样的人生。
正如杰克·凯鲁亚克在《孤独旅者》中自述:
从美国南部到东海岸再到西海岸再到偏远的西北部,足迹遍及墨西哥、非洲摩洛哥、巴黎、伦敦,乘船横渡两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遇到各色各样有趣的人们和城市。
铁路工作,海上工作,神秘主义,深山工作,好色滥情,唯我主义,自我放纵,斗牛,毒品,教堂,艺术博物馆,城市街道,生活大杂烩,一个独立自主、受过教育、身无分文、四海为家的浪子所过的生活。
北岛写于世纪之交的随笔集《青灯》和《午夜之门》,书里也谈到了他的漂泊人生。他穿行于纽约、巴黎、布拉格、拉马拉、加沙……游走于各种国际诗歌节,遭遇到身份各异的诗人、学者。书评人为此唏嘘:
北岛描写了他与世界的相遇,有见闻、有人物、有故事,信笔写来均轻松诙谐,超然跳脱,宛如简笔勾勒的素描;而他对生命与世事的慨叹却如影随形,有时尖锐的疼痛又会不期而至。
深夜人静时,我会忍不住一次又一次问自己:对北岛、凯鲁亚克、波拉尼奥这些“如野兽”般活着的孤独旅者、流浪汉、诗人来说,家乡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波拉尼奥如是说:“恐怕我必须给你个多愁善感的答案了。我的两个孩子——劳塔洛和亚历山德拉,他们是我仅有的家乡。之后,也许有一些瞬间、几条马路、几张脸或者几个场景或者几本书驻留在我身体里。我总有一天会忘记的,这是我对家乡最好的解药。”
当《荒野侦探》的英文翻译者莫妮卡·马里斯坦问他:“你是智利人、西班牙人还是墨西哥人?”诗人回答:“我是拉丁美洲人。”
6.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最终会写多长,但它肯定是篇长文;我暗示过自己:必须使尽全力(那种由无数块碎片堆砌起来的力量,不知道这种力量究竟是大是小,究竟有没有凝聚力,究竟算不算尽了全力)来书写它,写出一定的长度(同时也希望具备一定的深度,但我明白,这不是件一厢情愿的事);究竟有多长,像树根那样,长到哪里去,只能顺其自然了。
我去逛百度波拉尼奥帖吧,去看豆瓣波拉尼奥小组,去波拉尼奥读书会(但没有发言),偷偷地去看那些书迷在说什么,在做什么,在交流什么问题或心得。
他们有的说自己的车牌是RB2666,有的说他有一只名字叫齐亚的猫,有的说他想去西班牙XXX地区拜祭他的墓地,有的将他接受海外记者采访的原文一字一句地翻译过来(原文可能是西语或英文)——他们翻译时会情绪失控而默默流泪吗?我好想当面问问他们。
这些年,全世界有许多像我这样的读者,他们一本接着一本读着波拉尼奥,读着他写的小说,总盼望着永远不要结束。永远不要从波拉尼奥那个世界走出来。永远不要知道波拉尼奥已经不在这个星球上。
西班牙小说家写超级微型小说:“当我醒来的时候,恐龙依然在那里。”我想当然地以为,这位小说家所写的主人公就是波拉尼奥。
7.
一段关于《荒野侦探》的话:
我喜欢这本书,一次次合上又一次次打开,每一次合上都会从心底浮现出波拉尼奥年轻时的模样,每次打开都会想象他狠狠吸一口香烟然后写出一长串长得像紫葡萄的句子,可能比诗句长或短,轻或重,但它们跟那些昔日在旅途中写下的诗歌一样,有着甜蜜和苦涩,有着忧伤和激动。无论是对作者还是读者来说,对拉美文学还是世界文学,《荒野侦探》不仅仅是本厚重的小说,它的意义更远甚于此。对波拉尼奥来说,它既是诗人日记、文学回忆录、旅行记事本,也是自传和遗产、忧伤和歌声,它是交响曲,有更多超越其上的意义。对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或有志于创作的文艺青年来说,它是镜子,在那些与青春与诗歌与生命渐行渐远的本能现实主义诗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曾经、现在和未来;它是利刃,既剖开了我们年轻时又傲娇又放荡又不羁的本能,又戳中了我们在生活锅钵蒸煮下的不甘于平庸的挣扎过的伤口;它是海盗船,载着我们这种恋宅在城市钢筋水泥搭建的盒子里而失去灵魂深度感动的躯体在波涛上、在暴风雨中、在沙漠荒野中航行;它是铁锚,锚在贫瘠、坚硬、滚烫的泥土里而坚持绽放的红色花簇;它是标尺,帮助我们丈量伟大作品和其它小说的之间鸿沟或微距。毫无疑问,它们(与《2666》)是拉美文学的新高峰,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利奥·科塔萨尔、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大师曾经抵达的高度,可以等量齐观,并肩屹立;对世界文学来说,它是世纪末文坛的重炮,是世纪交接之际的华彩,它是从20世纪初叶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伍尔芙,中叶海明威、福克纳、帕斯捷尔纳克、川端康成等小说大师手中接过的旗帜,继续高扬的旗帜,荡开21世纪文学伟业的旗帜。
8.
初读他的小说《荒野侦探》让我想起了几个往事片段。
几年前某个下午,我读到一首非常有趣的小诗(诗的作者现在想不起来了),也写了首短诗,将它们分发给了大学时期的师弟师妹,想征求他们的意见。其实是想做个小测试,测试他们毕业多年后还有没有读诗的兴趣,写诗的冲动。
他们大多是我在大学期间(2000-2004)做校园文学刊物时的编辑,或多或少都写过诗和小说,毕业之后分散在各大城市中谋生,有做网页编辑、新闻记者、广告创意的,也有做自媒体运营的、人才资源、中学老师的,大地方的,小地方的都有,他们的回复没有出乎意料,基本上不写诗,也不看诗了,他们在为大都市的房子和车子忙碌而焦虑,已经没有闲情顾及风花和雪月了。
可悲的是,他们开始认为写诗只是件风花雪月的事。
有天突然收到小师弟从上海寄来的一份礼物,他毕业之后一直在媒体做新闻记者,同时也坚持写诗,只是产量与大学时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写诗的激情淡退了好多。
礼物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自费印刷的,1/32开本,不太专业的小字号排版,纸质还可以,但有点偏灰,行距太窄,读起来有些费力。
我还是坚持从头翻到尾,集子里有诗、随笔、短篇小说,大多是之前读过的旧作,他曾在大学时期就写下的。有几首是他女朋友的。我拿起手机准备拔打他的电话,后来想了想,又放下了。
我好像也没有太多聊诗的心情。
这样的书我还有几本。其中有一本是我前同事的文集。也是自费出版的。这本文集相比前面师弟的小册子,要厚得多,我花了一个星期的空闲时间大致浏览了一遍,发现好几处错误。书中的文字大都是他在发表在QQ空间里的,我之前多多少少读过一些,他喜欢写有关月和夜的古体诗,很短,很好读,但那些冷清清、空荡荡的诗意或古意,好像是仿古瓷器。
书里面有很多插图,都印成了黑白效果,可能是因为图片质量太差的缘故,印刷效果不太好,有些地方黑成团了。我花了大半个上午,写了篇短文,发过去给他,他好像非常开心,正式印刷时放在文集的开头,被当作是序,还署上了我的名字。
我承认我也发过他们这样的诗人梦。大概是十七岁上高二的时候,我已经写满了整整一本记事本。我现在还记得那记事本,封皮是绿色塑料的,小开本,可以捏在一只手掌里。但我从来都不敢拿出来给同学看,我甚至将它藏在课桌的角落里头,掩饰自己写诗的行为。
后来,可能是或许是渴求得到认同的渴求战胜了羞愧心和胆怯心,我偷偷将它拿给了当时年届五十已白发初露的语文老师,期待他只言片语的回应。接下来有将近两周的时间,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我等待他的回应,关于那些等同于我的青春秘密的诗的回应。
我的老师什么也没有跟我说。他可能只是略微翻了翻,并没认真读过,哪怕其中的一首。他将记事本还给我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表示,甚至连个点头或露出一丝赞许的微笑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极度失望。以致记事本被藏得更加隐蔽,后来连我自己都找不到了。
我把它遗失了或是故意开丢了。
我们长成路上难免会丢失很多东西,甚至会丢失那些日后回想起来感觉意义重大的东西。后来,我还是坚持偶尔写写小诗,或即兴作些情诗。自娱自乐的成分居多。大学时期,我负责主编校园刊物的时候,每期收到的来稿中有七成以上是“诗作”,大多是打油、搞怪、造作的句子,或是分行的文字,梦游式的段落,偶尔读到一二首不错的佳章,像发现粒珍珠。
我至今仍保持阅读珍珠质感诗行的习惯——那些散发或幽深或明亮的诗行。初读《荒野侦探》唤醒了我这部分关于诗歌的记忆,美好而短暂,纯真而感伤,像玉石。我潜入书中的文字,让他的字行与这种记忆交织缠绕,互相映照。
9.
波拉尼奥真正的身份是诗人。
但现代诗人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在权力与资本合谋、消费与娱乐联姻、文化与流行交媾面前,现代诗人的存在显得无比尴尬,不合时宜。
他们本来的声音——纯粹的、自然的、精神性的、诗意的、不被污染的声音,被众声喧哗淹没,被时代泡沫覆盖,被全球化浪潮边缘化。
正如诗人北岛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一个需要不断追问和质疑的时代。”一种诗,穷人的诗或来自底层的声音,革新的诗或带有反抗意志的诗,它们要么变成一种武器(如余秀华的诗),变成改变生存面貌和阶层属性的武器;要么变成一种墓志铭(如许立志的诗),变成慰藉身体和自由意志的幻乐;要么变成一种民谣(如鲍勃·迪伦的诗),变成流行音乐被异化、被膜拜、被消费或被误解的力量。
另一种诗,学院的诗或来自象牙塔的钟声,精致雅皮士酝酿的酒,流浪之歌或生命意志践踏出来的烙印,它们像种子、橡木塞、护身符、迎向暴风雨的经幡;它们变成诗人们互相取暖的柴火,变成诗人们慰藉心灵、对抗物质时代的信仰。
北岛、于坚、韩东;W·H·奥登、约瑟夫·布罗茨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这些物质时代的现代诗人们,他们的敌人不是诗歌,而是阿堵物。
在现代社会,诗人凭借写诗很难赚到养家糊口的阿堵物,也就只能另辟蹊径——写散文;写剧本;写书评;在象牙塔教书;在拘留所做心理学家——一言以譬之,为钱折腰。
诗人奥登在自己编选的随笔集《染匠的手》中写道:
“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一个可悲的事实:诗人写诗,远不如书写或谈论他如何写诗来得更有钱赚。我所有诗都是因为爱写才写的;很自然,我写的时候也希望能把它卖出去,只不过对市场的预期并没有影响到我如何写它。可另一方面,除了受旁人之托准备讲演稿、为书籍写导读、写书评等等,我从未自动自觉地写过一行评论文字;尽管我希望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能多少有点发自内心的喜爱,但我动笔写这些,只是因为我需要钱。”
北岛也遭遇过跟奥登类似的情况。他曾在五年时间内,流浪了七个国家,搬了十五次家。因为生活拮据,他不得不接受“美国之声”的邀请,像奥登一样写起了随笔;后来,他开始接受美国高校的邀请,去象牙塔里讲授诗歌创作,回归领薪过活的日子,为此,曾经说过“野兽怎么活,诗人就该怎么活”的他自嘲道:我也被圈养起来了。
还有一种诗人,他们开始写诗,后来写小说,最终却以小说家闻名于世。像查尔斯·布考斯基、雷蒙德·卡佛、罗贝托·波拉尼奥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诗人,他们斩露头角的时候,凭借的是写诗的才华和热血引人注意:考布斯基继续出版《花朵、暴头和野兽的哀号》(1960)、《难以成功的诗献给一文不名的懒汉》(1962)、《从8楼的窗子跳下前写的诗》(1968)等诗集之后,才得以出版小说;卡佛最先发表的作品是诗集《离克拉马斯河很近》(1968)、《冬季失眠症》(1970)。
波拉尼奥十几岁开始创作诗歌,四十岁才开始创作小说,但他最终是凭借长篇《荒野侦探》《2666》而不是诗歌,登上文坛巅峰,确立二十一世纪小说大师的地位。
相比石黑一雄三十年创作七部长篇、乔纳森·弗兰岑十年出版一部《自由》(2010),波拉尼奥简直就是位宇宙爆发型的作家,他的十部长篇、四部短篇,只用了十年时间。而且这些作品(包括一千一百多页最终没有完成的鸿篇巨制)是在最恶劣(婚育一儿一女)、最糟糕(一贫如洗)、最绝望(肝功能衰竭)的环境下创作出来的——也许用“逼榨”或“倾泄”来形容他的写作更为合理一些。
10.
最后关于波拉尼奥的话:
他是诗人,也是小说家。他是写诗的小说家,或者写小说的诗人。他在诗人群体中很容易辨识出来,因为他写诗,他一生都在写诗;像苏珊·桑塔格,写小说之前,大家都知道她是著名的文化批评家。有些标签被帖上后想撕下来不太容易,世俗的眼光和评价很容易粘在艺术家身体上。撇开诗歌不谈,将他的非诗歌写作切割出来,单纯从他的小说来看他,他又是怎样的小说家?通常来讲,有这样几类小说家:公共知识分子型小说家、职业型小说家(含类型小说家)、爱好型小说家。公共知识分型小说家又可以细分为教授型、新闻记者型、文化观察型、独立作家等。按照严肃文学或纯文学类型的小说创作来看,每个小说家身上都有自身鲜明的风格,光靠这种教条式的切割划分其实是很难界定清晰的,或者说部分作家是很难界定的。相对而言,爱好型小说家比较好归纳,他们本职的工作不是写小说,可能是唱民谣的歌手,可能是做生意的商人,可能是文笔好的企业家,只是偶尔跨界的这边,即兴创作了一二部作品,尝尝其中滋味就游离开了。但公共知识分子型小说家和职业型小说家界线就比较模糊,就拿村上春树来说,从他身上的特征来看,他是蛮符合职业型小说家的范畴,他也曾自署为“职业小说家”,但当他就某些公共事件、公共问题发言时,他又摇身变成了公共知识分子型小说家。而像布洛克、东野圭吾、罗琳、刘慈欣这一类型的作家,比较好界定,他们就是类型小说家。波拉尼奥呢?我也不认为波拉尼奥是个真正的意义上的小说家。他至始至终是个诗人。或写诗的作家。或写小说的诗人。但不是小说家。他从骨子里鄙视写小说的自己。他或许自认为从写小说那刻起,这个世界上的波拉尼奥就不存在了,他成了贝拉诺,他成了利马的朋友,他成了XXX的男友。那个追逐灵魂的感动的诗人波拉尼奥消失了。他成为关在屋子不停地写,写小说的贝拉诺。正如他在最后一次接受访谈时所说那样,喜欢自己的诗歌多过小说,因为——“我通过拿起一本我的诗集和小说哪个更让我脸红一点来判断。诗歌让我脸红得少一点。”
【Written by : 唐 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