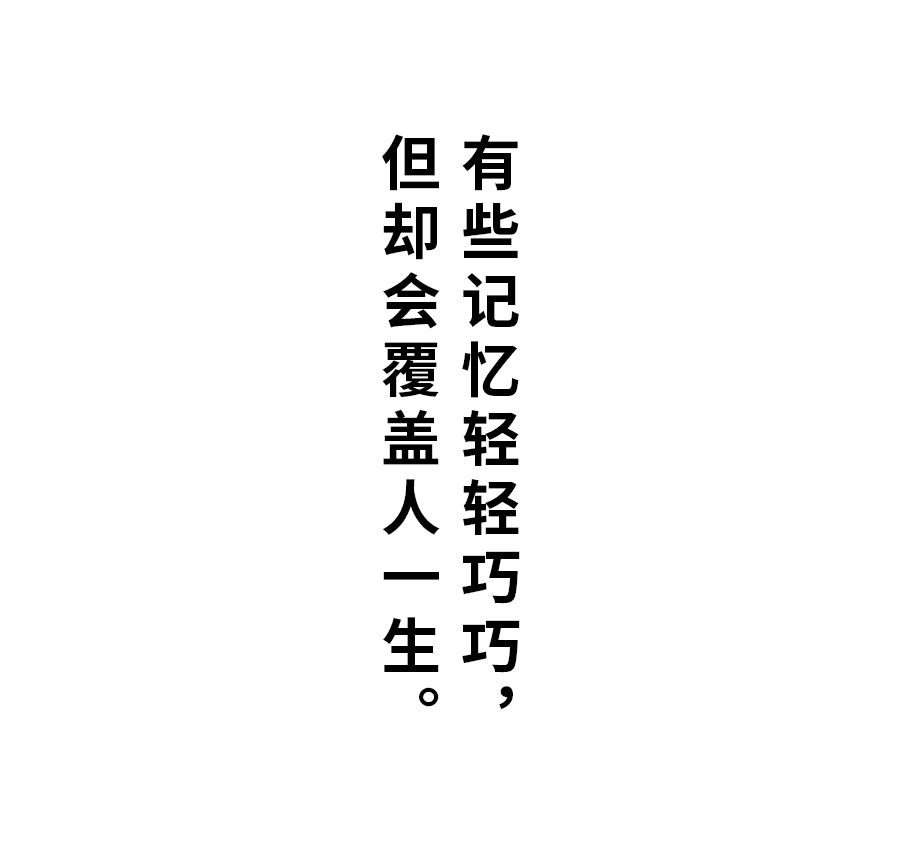我小巧、精致,又过于丰满的性启蒙。
时值初夏,麦子成熟,天气一天天热起来。高大的杨树遮盖住房屋,房屋间有条小河,河旁的树荫下有一堆几米高的麦秸垛。
两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在大麦秸垛脚下堆起一个小麦秸垛,然后把它拨拉成一个圈。
她们笑着迈进去,一屁股坐在干净的麦秸上,拥吻在一起。
十几年来,这个场景几乎天天在我脑子里面闪回。
Music.G'Night Stand - Leavin' tomorrow
要过年了,我抢到了回家的动车票,又能见到发小茜茜姐姐了。
茜茜大我半岁,是个从小爱躺在被窝看修仙小说的文静女生。
她把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马尾,冷白色的脸上有一些淡粉色的痘印,两根细腿撑着过大的上身骨架,不显瘦。
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淡漠的、生怕引起谁注意的美。这跟小时候的她不同。
六七岁时的她伶牙俐齿,永远要在吵架时占我上风。
打架互掐时,她一定要瞪大眼睛,在我手背上掐出更深的印子逼我先放手。
玩跳皮筋、捉迷藏、跳房子,或是其他游戏,也必须由她决定。
长大后每次见她,我都会想起文章开头的画面。
系列记忆就潜藏在我们的目光之下,但我们从不提起——小时候我们最爱玩的游戏,是拥吻。
记不清是在哪天,茜茜姐姐发起了接吻游戏,当时我满脑都是电视剧里的接吻画面。
第一次接吻后,我即刻陷入恐慌——我怕自己会生小孩。
当时我问过茜茜姐姐,她睁着大眼很确定地回答:不会。
于是,我们便经常玩起这个游戏。
茜茜姐姐家里没人时,我们窝在卧室里扮演医生和病人。
我们也会学着电视剧里的样子,跪在床上拜天地,她喜欢蒙上纱巾扮新娘,我扮新郎。
相约春游时,我们会抓着折下来的花枝,爬进公路底下长长的水泥管道里扮仙子和仙女。
这样的Cosplay 游戏,结局都是拥吻。
我从没跟人讲过,我的初吻在幼儿园时就真切地没了。在茜茜姐姐的言传身教下,到一二年级,我的吻技就比电视剧上的接吻镜头更优秀了。
游戏进入下一阶段。
有个暑假,茜茜姐姐趁爸妈不在家,又把我叫到她家。
她跪在地上,神神秘秘地从衣橱里面垫的报纸下掏出一张碟片。看完卡顿的碟片,我认知的新世界打开了。
大我半年的茜茜姐姐就这样成为了我的性启蒙导师。
那个年纪的我们并不觉得拥吻、抚摸是禁忌的,只因VCD 里播放的是异性性爱视频。
你有没有一段遥远的、关于童年的隐秘记忆,你从没跟人提过,便也没人会知道,跟他们进行日常嬉笑怒骂时的你,上一秒回忆过什么样的画面。
有些记忆轻轻巧巧的,却会覆盖人一生。
看完碟片之后不久,我们升上三年级,附近村庄的小学校经历合并。
到新的大校园后,我跟茜茜姐姐被分到了不同的班。课程增加了英语、品德和科学,学业重起来。
我爸担心我的安全,掏钱租了一辆面包车,让我跟七八个小孩挤车上下学;大一点的茜茜姐姐则是步行。
我们见面的时间和心思都少了。
不知从哪一刻起,我们意识到接吻游戏的微妙,但谁都没言语。有了更多两性认知后,茜茜姐姐和我心照不宣地,把游戏关在了过去。
越长大,我们越当游戏没有发生过。
那些画面浮现时,我只当在看朴赞郁的电影——清冷的,拉扯的,禁忌的。
不知她怎样想。
多年以来,茜茜姐姐做过我无数次幻想的对象。她在带给我兴奋、冲动的同时,也带给了我自我怀疑。
在遇到男友之前,我困惑于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定位中。说出来可能没什么,但很多个夜晚,我都兀自在渴求和蔑视、批判爱情与性中挣扎。
读再多弗洛伊德,都不能用客观理论击溃主观矛盾。
成长是个异常复杂的命题,因果交错。一种挣扎牵扯起很多过往不忍卒读的经历,我在对抗抑郁情绪的时候,最常想起我的茜茜姐姐。
她对我而言,像一朵白色的棉花,柔软,洁净。我企图从她身上获取安全感。
VICE 近期有篇文章,叫“我从小被长辈‘弹小鸡儿’弹到大,但没受半点心理创伤”,讲的是一个男孩子小时候被男女长辈们用脚、手抚触性器官的故事。
但跟很多人的认知有出入的是,直到长大,作者都没有完全把这种行为定义为对自己的侵犯。
他犹疑的是,这是因为在他生活的环境中,这般逗乐小男孩的“陋习”太过普遍,还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彼此其乐融融。
我的性启蒙导师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两个女孩在童稚之时,过早经历了性体验的愉悦。
两个小女孩躲避得很好,也没有恰当的教育及时阻止她们。
而当时两人也不会思考,阻止这种行为的必要性有多大。
那篇文章下还有一条留言:
小时候接触的性模式,会很大程度影响一个人的性观念。
就像小时候为了玩上泡泡堂,只能被邻居小哥哥“把玩”,长大后我成了Gay 。
我没办法结合我的经历得出一个这样确切的结论,我小巧、精致的性启蒙,无法用标准、对错来界定。这确实,也困扰了我许多年。
陈述完这些,我舒了口气。
茜茜姐姐念完大学后,在大学所在的城郊租了一间小屋子。
闲时她会去药店打工,一个月1500 块的工资,足以让她生活三个月。不谈恋爱,也不喜欢与人交际,她还是喜欢窝在被窝里面看修仙小说。
棉花一样的茜茜姐姐开心么?
她在想些什么呢?
她将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她也,爱过我吗?
今天,我们分享了一篇来自 Wendy 的朦胧的童年记忆。在编辑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编辑部好一些人都想起了自己童年有过的类似经历。让人遗憾的是,我们都没有在恰当的年纪获得恰当的性教育。
如无意外,明天我们将会分享一篇有关粤语歌的文章,记得回来看我们。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