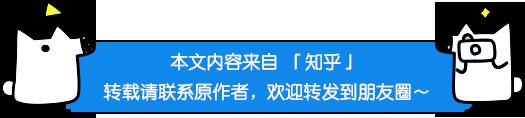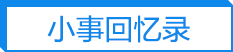小事 | 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爱情刚开始生发的时候大都包含想象,你爱上一个人,是因为他引发了你的某种遐想。没有人真的是神明,你所谓的神明只是自己的迷思罢了。然而,唯有用你的手触及神像,才是破除这迷思的唯一魔法。
这是知乎君分享的第 878篇小事。
题图:《堕落天使》
女生怎么追男生?
知友:陈醉
与男神是校内 BBS 上认识的,慕其学识,时有请益;不过他的发帖口吻很端肃,叫我觉得有年纪了,像个师长的架势,不由地敬而远之。
有一回提及我是茶社社长,他起了兴趣,说有活动通知他。我以为是客气话,没想到他真来了。
那是五月初的一天,是个没有风、空气黏腻、像裹了一层蜜的日子。社里约在校门口集合,我有点紧张,刻意收束着视线,人很近了才看到。他身架高且宽,笔管条直,但又显得放松,仿佛这副好站相不是被规矩绷出来的,而是天生如此,用不着费劲。肤色和发色较一般人浅,在日光下明晃晃的,像戈壁里的盐湖。拎着一本书,大概刚从对街书店出来。
我伸出手去:师兄,幸会。
他有个比例偏大的方下颌,鼻梁直挺,以至于蓝色半框眼镜滑下去了一截子,透过镜片垂目看了看我,然后也伸出手来。
体温比我高。
第一面没觉出他多么英俊,倒是意外的年轻。好言笑、能交际,完全是个少年人的风度。我发现自己在有意无意地拿捏自己的言行。这种表现欲真是久违了。
结束以后我发消息给他:师兄原来你这么能说的,以后多来玩哦。
等了半日他没有回。我也就冷却下来,忘掉了这件事。
到了差不多五月底,突然有一天,周五或是周六,他发信来托我帮个忙。聊了好一会儿。最后他说:周一去你实验室讨论,顺便请你吃个饭吧。
我开始期待,但并不急于兑现,生怕惊醒了自己。我停留着,享用这期待,它强烈而含混,如仲春夜里的花香。或许我是在期待自己将起的心跳声;像等候一头巨兽从地底苏醒。
他大约是那家店的常客,老板娘的眼睛在我身上一转,取笑地望了望他,一阵甜美的窘迫令我微微发僵。我们不算熟,不过我对他的专业一直有兴趣,选修过他导师开的课,能找到些话引子。男神博学善辩,有问必答,词锋简利,态度和悦,只是不大体贴——老让我感觉自己很蠢。偶然讲了句聪明话得他肯定,便受宠若惊,像得了块怎么吮也不会小的糖。
之后就经常聊天,乃至一聊一通宵。其实我长相乏善可陈,也就身材尚可(幸好这是个能穿热裤的季节;以色事人虽无荣誉感,倒也无耻辱感,好似我在使用自己的一把漂亮剪刀),才识阅历亦不足与男神并论,只能支着勤敏好问的学妹人设。
在受欢迎的异性面前,过早暴露意图是个忌讳,因为他们对追求者习以为常,容易失去对你的好奇;或者更糟,轻视、反感、退缩、逃跑。较明智的做法是装作对他感兴趣的事感兴趣,而不是对他本人感兴趣。
这个阶段我的判断是男神不讨厌我,但也仅止于此,拿我解个闷罢了。有一回我借东西给他,他趿着拖鞋下楼,还提了袋垃圾。我递过东西,看他没有急着走的意思,脸皮一老,就问你晚上干嘛呢,他迟疑了下,说,没什么事。
我趁势道那去酒吧玩呗,上次讲过要带我见识见识的。他又迟疑了下,时间稍长,垂头瞧了瞧自己的拖鞋:「去酒吧啊,好,等我上楼换条裤子……」
当时如何兴奋已经模糊了,只记得一种隐秘的满足感:我第一次上酒吧是他领去的;由此,我偷偷地、永久性地与他发生了联系,仿佛偷偷地、永久性地占有了一部分的他。
刚入夜,人不多,也不吵。驻唱还没开张,四下里像粗坯一般袒露着。男神熟稔地和小弟攀谈,我立在门边东张西望。他好笑又有点不耐烦的样子:「好奇宝宝。」一手端起桌上的蜡烛,低着头点烟。
我忽然发现他有双凤眼,眼尾的弧度恰在好处。这么说似乎太戏剧性,但如今可以确认这正是一个肇始:像明月出云,将大地上的景物从黑暗里一一浮现。他的美自此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细节化、越来越丰裕。
我说:「你啊出个门打火机也不带。」他抬眼朝我一看(大概我这嗔态做得唐突),没说什么又低下去了。我忽然就很高兴,得意洋洋,仿佛我们已经是能说这话的关系似的。
我估摸他对我起了男女之间的意思也在那一天,因为当我在桌子下面伸直了腿时,他上下掸了我两眼,问道:你有多高?
于是影影绰绰的暧昧升起来了;一次在他宿舍看电影,我对某个情节说了些什么,他大笑道:傻不傻啊,回手揉了揉我的头发。也有试探性的话茬,但我接过来,他却不追击,轻轻搁下了;倒把我撂在半空,好一阵难堪。或者兴头上调笑几句,又自己倦怠起来:「睡吧,半夜三更的,跟陌生男人聊什么聊。」
他不很热心,我也晓得。可惜我已经坠进烈酒似的激情里,失掉了距离上的分寸。他随口说想吃羊肉串,我立刻从实验室冲出去买好了送到他楼下。他格外客套地道谢,头颈朝前躬了躬;脸上有一点尴尬,掩着隐约的戒备,好像接受的不是礼物而是威胁。
我窘极了;他用彬彬有礼来表达疏远,并非为了敷衍虚饰、留些颜面,而是因为这样表达效果最好。那是一种明确的、尖锐的、毫不客气的客气。我几乎恼怒起来,索性破罐破摔,再三地贴上去搭讪;好比赌徒输红了眼,越输越赌,指望着一朝翻盘——直到全输光了。
他终于连着两三天没搭理我。我又羞惭又痛苦,觉得自己像锃亮的银餐盘里一坨滑稽的烂山芋。想放弃,又没彻底死个明白,来来回回地推敲、猜度;这自我驱迫的苦役在爱情的诸般不幸之中,是唯一一种惹人生厌的。
捱到周五,男神突然回了消息。先是闲扯了个把钟头,话题渐及私隐;愈滑愈深。最后他直截了当表示想和我上床。我说我还是处女。男神说他可以引领我。我说你先讲清是要一夜情还是炮友还是谈恋爱。男神说他现在不想恋爱。
我顺着话头陪他讲了几个荤段子,收起手机。然后惊讶地发觉自己竟很平静。我求得了结果,种种焦灼因此止息,同时感到荒诞和恍然:这谜底叫人失望,但严丝合缝、本该如此。
周一我看到男神在线。我隐了身。过了一会,他头像暗了。我就挂了上线,不料男神的消息立即闪了起来。
他说我以为你被我吓着了,就此消失了呢。我打着哈哈说怎么可能,我周末和朋友出门玩了,刚回来。他说倒大霉了,硬盘毁了,论文要挂。我说我认识一家很好的修复站,帮你找找电话。他说谢谢,看我这么倒霉,出来陪我吃个饭呗。
我忽然意识到我在他那里还是有一点分量的(虽然我的这一点价值,好比特意留长了要盖住秃顶而其实只是给头皮分了行的几绺毛,寒碜),于是隐隐生出了笃定,捎带着索然,坠在一片飘飘然里,像云端上坠了个秤砣。
过马路时男神拉了我的手,很自然,不扭捏也不油滑;我明知这是通往上床的一个步骤,仍有一列响颤由臂膀贯入全身。我们嘬着酒,初次言及父母家事,谈话沿着套路越发私密亲切,如同蜘蛛沿着它的网有条不紊地爬向网心。
他转过头来,直白地说:亲一下。我马上就顺从了,像小孩子顺从举着冰棒棍说「啊——」的医生那样。他的手握过酒杯,又凉又热,覆上我的腿,不紧不慢地摩挲;我讥嘲地想:你早就想这么干了吧。
这晚他还说了句古怪的话,「如果能这样持续两年,我们就结婚吧」。我说好啊。他说认真的哦,你答应了哦。他大概是认为我「还挺适合结婚的」。——好像比他讨厌我更叫人悲伤。
此后我们又有过几次亲密接触,每到最后那步我还是拒绝了。这些亲密也都谈不上幸福,是些造作的、虚有其表的亲密。他像是在进行程式化的表演,不怎么投入,或是演技太蹩脚,总之他始终抽离于他的角色;我则忐忑不定,一边又为自己凄凉。但我尽力表现得镇静老练——完全是无意识的,只出于动物式的本能,要遮盖着弱势。
男神待我似乎更淡了;我拿不准是不是因为我的拒绝令他不快。——后来搞清楚了,这就是他不快的方式:看起来绝不是故意要冷着你,只是意兴阑珊罢了。
有时从他宿舍出门,他半躺在床上看书,掀一掀眼皮:「那我就不送你了。」白天在食堂碰上,我还犹豫着该怎么招呼,他已经冲我客气地点了个头。他为人本就固有一种疏离感,这一来我跟油煎着似的。
但也还有好时候。他宿舍窄,地上摞了书,床和桌之间将将卡着把椅子。他卡在椅子里,我只能坐床。交谈起来,他半扭过头,是台灯光里的一个侧影。他言吐文质兼美,声音沉着又清越,鬓角裁得利落,瞳色浅而晶莹,唇线在接近嘴角的位置有个凹折,秀劲、性感;我就像老人注视球场上的少年那样感到又快乐又绝望。
偶尔坐他自行车后座,壮着胆环他的腰,他笑道你不热啊,我讪讪的,强要做出一脸泰然来,仿佛这事理所应当、惯熟寻常。有一回下暴雨,他买饭回来,满头淌着水,腾出手囫囵抹了把,问我:你要哪份?我取过毛巾替他擦头发,心里像汪着个池塘,泼来荡去却悄无声息。他在毛巾底下动了动:「没事,不用。」
这是一种奇特的情形——肉体的亲密程度远远领先于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它将我在幻想和不满足之间抛掷。我熬不住了,于是逐渐下了决心。其实也简单,只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他提上裤子就走,会后悔吗。答案是不会。仔细地想了几遍,是真的不会。
七月七日,桑拿天。我俩骑车去江边。坐在堤坝上,他买了两罐哈尔滨啤酒,抡瓶对饮。江面漆黑,浮着惨白的光点和折线,像个诡诞的低像素游戏。
码头的起重机一阵一阵轰鸣,隔水听着不很刺耳,是种绵绵延延、温文有礼的噪声。他兴致颇高,讲他家乡每到三月章鱼繁殖季,近海上就升起一片桃花潮。我说我有点事拜托你。他笑道那你怎么感谢我,以身相许?我说好啊,做我男朋友吧。
他一怔,说还是算了吧,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你太单纯了,我会害了你。
我捏着啤酒罐子摇摇头:我想过了。
他喉咙里一响,似是没成形的言语。目光错开了几瞬,又移回来看了看我:你以前这么对人说过吗。
我说没有,你是第一个。
他说那我很荣幸啊。但我怕你将来会后悔的。
我说如果不赌一把,我现在就会后悔。
这话一出,我自己激昂起来,还要往下讲,他吸了口气,抬手虚按了按,说:「闭嘴,闭嘴。」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的手顺势落在我肩上,就吻上来了。
我想我的初夜居然交给野战了,也算一项人生成就。不过那天终究没有做。最终破处是在七月二十六日早上。他问我有何感想。我翘着腿,说感想是没感想,真奇怪——并没有什么仪式感,我也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或是跨入新的人生阶段。
这么一件疯狂的事情,竟以普通得令人惊异的方式发生了。男神说怎么疯狂了。我说把初夜给一个不爱我的人啊。他说如果我动心了呢。我故作夸张地扑上去问真的假的。他闭上眼,收起笑容,刻意显出郑重来:「真的。」
当然,我其实还是不相信。后来,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还在继续过着;我相信了。
我对诸位的建议,请始终尝试说服自己,「左不过是涨经验值」。你的努力不是用来交换对方的爱,而是用来获取与对方共处的机会。你得到了体验——这就是报偿;无论结果如何都没啥亏的。
我干了,你随意。
一般人不会拒绝这个,因为有收益而无损失。所以这样其实赢面很大。但若总抱着要赢的念想,就与我干了你随意背道而驰了。
有人问赌输了会怎样。并不会怎样。这就像信徒敬奉神明。付出全部代价,只为了伏在他圣殿的台阶上片刻。你已经心满意足、感激涕零。
确实卑微,但迷上个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的美妙就在于对自我的消解。你终于撒开手,从执掌自我的责任与焦虑中获释,交出了自己:用以被席卷、被淹没、被烧成灰。
而这种关系里面,又只有自我是唯一重要的。神明的意思不重要。无论他是只想打炮,还是考虑过认真发展,都算不了数,后者打完炮也可能变成前者。所以检视你自己就够了:你愿意筚路蓝缕去朝拜神殿,即使永远不可能拥有神明吗?
爱情刚开始生发的时候大都包含想象,你爱上一个人,是因为他引发了你的某种遐想。没有人真的是神明,你所谓的神明只是自己的迷思罢了。然而,唯有用你的手触及神像,才是破除这迷思的唯一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