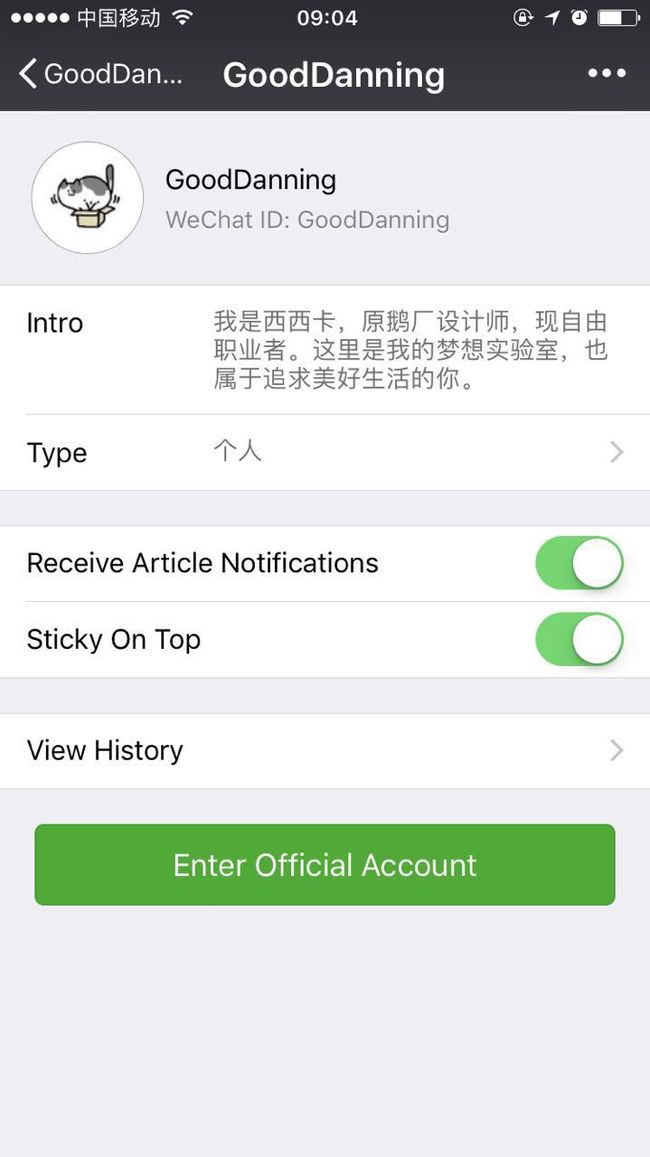“这是一个不说就很可能会随即消逝的故事。”这是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宝岛一村》宣传册上的一句话。
上周,这个故事重新在上海的「上剧院」呈现,我和朋友一起去了剧场。话剧演员3个半小时精彩的演绎,让我甚至怀疑自己曾经历过那个年代。
那是1949年,近200万人为了避难,从大陆撤退到台湾。政府为了安置他们,临时兴建了大量的房舍,也被称作「眷村」。这部戏是一幅巨大的卷轴,讲述了三个家庭来到眷村后近60年的变迁。
他们从心心念念想回去到再也回不去,从颠沛流离到安家落户。所有的无奈、无助、欣慰、爱恨纠葛,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一瓶醋、一个包子、一张唱片都能勾起他们对家乡浓浓的思念。然而他们却只能各自面向自己家乡的方向,抬头望一眼天上的星星。
老赵走了,没有等到开放探亲的那一天。儿子小毛代替父亲回到了故乡北平。
「北平的马路很陌生很陌生,我却觉得很熟悉很熟悉。」小毛感叹着。
见到自己素未谋面的奶奶,小毛噗通就跪下了。而奶奶没有说话,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这一巴掌是你替你父亲挨的。他跟我说出去玩玩,这一玩就是40年。」
这种对亲人的挂念和痛苦,冷如云也深有体会。她丈夫曾经是飞行员,夫妻俩曾经多么风光,住的房子都比普通人的好很多。然而有一天,李军官在一次任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据传是投靠了对岸,然后就杳无音信。被人背后指指点点的她不得已去当仆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50年后,她丈夫回来了。满头白发,步履蹒跚。
子康问她:「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她背过身抽泣:「都快过完了。」
当年子康离开家门的那天,看着他的背影,多么阳光的小伙子啊。谁知天黑了推门进来的,却是一个佝偻的老头。
「子康,你是要回来吃晚饭吗?」她轻轻地问,当作所有的一切只是假象。
除了离别的绝望,这里又有着太多的欢乐。
老赵的丈母娘钱奶奶是北平高级餐馆景福轩的老板娘,出生在天津的她最爱做天津包子。隔壁的台湾本地人周太太向她讨教。
可是这两个人一个只会说天津话,一个只会说闽南话。钱奶奶手舞足蹈,像个哑剧演员,努力地教着这个台湾媳妇。谁也没想到,这倒成为了周太太以后维持生计的绝活,「天津肉包子」也成了眷村独有的文化。
即使后来钱奶奶去世了,天津包子的香味依然飘荡在眷村的大街小巷。
对于第二代的孩子们而言,眷村带给他们的是美好。眷村有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朋友,他们喜欢的人。这个村子热闹了起来。
周胖偷看二毛洗澡,被大家追着打;大毛和大牛在防空洞偷偷谈恋爱,差点私奔;大车去台北参加「三朵花」比赛,全村人围在电视机旁加油,却惨淡收场;爸爸们在榕树下讨论政治,有个叔叔的奇怪方言从未被听懂过,但大家装作都懂...小小的村子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眷村俨然已经成为他们第二个故乡了。
我和朋友哭了笑,笑了哭,被每一个细节打动着。无论再不舍得,剧场还是有结束的那一刻。剧组给每个人都发了热腾腾的天津包子,真的觉得自己就是那里的村民,吃着吃着竟然想落泪,然后又联想到了许多事。
小时候,我曾经住在爸爸所在的部队大院。每天最大的事情,就是跟小朋友四处游逛。白天去菜园摘玉米,晚上在树上捉知了。听着各种不同的号角,看着爸爸和叔叔们的飒爽英姿。那时的我就想:我真的好想一直一直生活在这里啊。
可是我爸爸在部队的18年,却没有一天不在思念故乡,思念远方的家。爸妈结婚后异地恋持续了近十年,我们家有个箱子,装满了他们的信件。妈妈保护得很好,很少拿出来让我看。每次读他们的信,我就觉得好羡慕。信件抑或文字,对那时的人们而言,是一种寄托,一种滋养。不像我们现在,社交平台从未如此便利,文字却从未如此浮躁。这样想来,我也很久没有静下心来为家人写封信了。
然而每个硬币都有两面。从另一面来看,这个年代又是好的。网络的发达和交通的便利,让人们不必再经历那种一别就是半辈子的苦楚。
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我们的生命显得微不足道。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遇,决定着不同的命运。昨天跟我爸打电话,他对我说:「人啊,还是要顺应时代啊。」这句话我想了很久。
或许我们真的只是这个时代的一滴浪花?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哪怕只是浪花,我们也要活得精彩。
- END -
我是西西卡,希望和你成为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