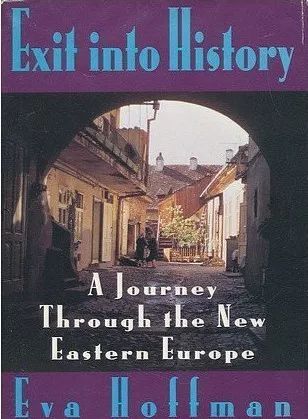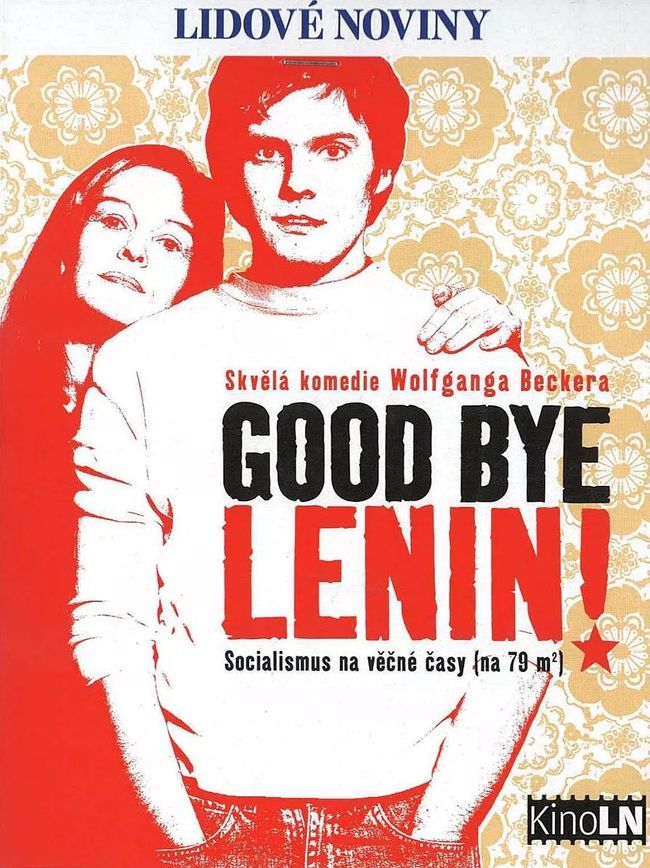反叛的东欧:伊娃·霍夫曼访谈 | M观察
伊娃·霍夫曼在自家客厅,望着东欧的方向。摄影:郝汉
三十年前,东欧各国在旦夕间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那一年也因此成为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时刻。与此同时,面对从前生活系统的全面瓦解与对过去价值体系的全盘否认,东欧的人们似乎也有些措手不及,只能让突然松绑的自由与尚未清算的历史裹挟着他们向着未知行进。
曾任纽约时报书评版主编的伊娃·霍夫曼在1990年与1991年返回了阔别数十年的故国波兰,也游历了包括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正在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东欧诸多国家。借助其记者身份,在与普通人交谈之外,也采访到了许多东欧知名作家、导演、前政党要员,其后整理写就的《回访历史》一书,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下了东欧彼时在旧秩序的废墟上试图重建新的精神秩序与民族认同的挣扎与努力,揭示了东欧剧变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日常生活等多个维度上的复杂性。原版于1993年的《回访历史》,在2018年由理想国出版,获得了许多中文读者的特别关注。
如今,东欧剧变已然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东欧诸国在各自前途未卜的道路上也刚刚走过了第三十个年头。那么,旧“东欧”在过去意味着什么?霍夫曼书中所希冀的新“东欧”诞生了吗?社会转型的复杂性究竟将“东欧”引向了何方?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东欧”对欧洲共同体从“拥抱”到“反叛”的态度转变?
解铃还须系铃人。理想国在格林威治时间2019年6月5日,前往了伊娃·霍夫曼在伦敦的家,亲自向她请教了这些问题。
《回访历史》,原版于1993年。
反叛的东欧 | M观察
——伊娃·霍夫曼访谈
采访、摄影:郝汉
1.
何谓“东欧”?
理想国:东欧剧变过去了三十年。铁幕下的“东欧”已成为历史。今天的年轻一代也很少有机会再度了解到那个时期的“东欧”。您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关于“东欧”的定义?什么是东欧?
霍夫曼:对“东欧”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便是“欧洲的东部”。当然,“东欧”这个概念不仅有着地理上的含义,也有着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内涵。传统上,“东欧”便一直被视为 “另一个欧洲”。二战后,丘吉尔的“铁幕演讲”于1948年至1989年间定义着“东欧”。总之,欧洲的这一部分一直被视为一个与西欧很不同的欧洲,一个较之很不文明和很不干净的欧洲。有一位旅行者说,你只要看到你身边的人都有着蓬乱、肮脏的头发,你就知道你身处“东欧”。
这些话有一点点道理在,由于东欧的这些小国在几个世纪以来实际上一直没有完全的主权,所以“东欧”的经济发展程度始终较低。独立主权长久以来的缺少可以拿波兰来举例。波兰在1989年东欧剧变以前,只经历过一段很短暂的拥有主权的时期。1795年开始,波兰就被瓜分了。波兰的统一局面崩溃有其内在的弱点,因为它当时其实比任何地方的任何国家都更“民主”。波兰那个时候有着经选举产生的君主,也有着所谓“自由”的高尚议会,但这些也让波兰陷入了混乱。当时周围的大国,包括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大公国和沙皇俄国利用了这种混乱,然后他们三个国家把波兰给瓜分了。波兰失去了它的独立性。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获得了独立主权,但随后又在1948年再次失去主权,开始被苏联统治,一直到1980年代才再度恢复了自主独立性。
霍夫曼在其伦敦家中进门处一个十分显眼的地方挂了一幅她前些年在北京游历时购置的紫禁城雪景图。
2.
东欧,作为欧洲的“他者”
理想国:萨义德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东方主义”,他认为,东方在西方的想象里总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您在《回访历史》一书中也有提到,您说人类似乎总需要一个想象的“他者”。东欧之于西欧便成为这么一个想象的“他者”,是“另一个欧洲”。那么,您怎么看此种“他者化”的想象,对“东欧”的想象是仅由1948年后政治意识形态的分裂导致的吗?或者,会否有一些根植于“东欧”历史文化里的因素为此种所谓欧洲内部的“东方主义”想象提供了素材?
霍夫曼:相比“中国”或“日本”总被西方想象、构建成一个遥远的“他者”,有人把“东欧”称为一个邻近的“他者”。在过去,很少有东欧人旅行,人们也很少去东欧旅行。所以,人们在铁幕落下以前根本不了解东欧。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过去在西方,人们会想象波兰为一个非常野蛮、原始的国家,一个黑暗、令人生畏的地方,满大街都是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云云。
理想国:据我了解,东欧的一部分比如匈牙利在历史上曾被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过,这段历史会否留下了一些文化遗产,成为“西欧”对“东欧”进行异域想象的素材?
霍夫曼:我目前没有仔细从这个维度思考过。不过我所知道的是,匈牙利总是希望它能够摆脱土耳其的统治。波兰也总为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战斗中做出的贡献而感到自豪。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想霸占东欧地区,所以他们对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非但没有自豪感,反而十分反感。
理想国:俄国曾经宣扬所谓“泛斯拉夫主义”作为团结策略,即东欧各个国家的人都为斯拉夫民族的后人,理应联起手来。那么,在冷战结束的东欧各国间,泛斯拉夫主义有成为过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作为团结手段吗?
霍夫曼:没有,东欧各国间根本不存在所谓“泛斯拉夫主义”。当年,我游历东欧以收集材料写《回访历史》时,我非常惊讶于所有这些东欧国家都将目光望向“西欧”,将“西欧”作为他们的一个参考范本,作为一个前进的方向。他们十分渴望成为“西欧”。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团结彼此。其实我认为这很糟糕,因为他们如果团结彼此的话,本来可以变得更强大一些。
以《窃听风暴》为成名作的导演在2018年的新电影《没有作者的作品》中的一幕,东德的艺术生正在对此作画。
理想国:与此同时,苏联的宣传机器也标签化“西欧”。那么,“西欧”在当时代表着什么?
霍夫曼:苏联官方对西欧的宣传,你想也知道它会是多么的荒唐,他们擅长用许多的假新闻去宣传。因此,东欧人实际上根本不相信那些宣传。这或许也是有一个如此荒谬的宣传机器的好处,没人会相信(笑)。在私下里,东欧人会认为“西欧”代表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有他们想要的一切。
理想国:你在《回访历史》一书中提到,东欧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惊喜和多样性,不能简单化归结为几个政治的面向。那么,当时对于“生活在东欧”的典型刻板印象是什么?
霍夫曼:人们会认为他们的生活相当黑暗、原始、野蛮,被共产主义信仰充斥,但实际上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三的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日常生活里,人们会认为他们只会互相称呼“同志”,而且事实上他们也会亲吻婴儿的手,和彼此热情地打招呼,说再见这些。
理想国:所以您试着通过讲述铁幕背后的普通人故事来打破所谓人们对于“生活在东欧”的迷思。但其中有一些故事的讲述者并不那么普通,有些是知识分子,有些甚至是党内的高级官员。你是否注意到这些精英在故事叙述上与普通人之间的显著差异?
霍夫曼:东欧剧变以后,各个国家在对历史进行重新诠释,在这一方面,普通人与知识分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比如,关于波兰大屠杀历史的辩论常常会变得十分尖锐。有些波兰历史学家想要把这些历史公之于众,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普通人更民族主义一些,他们仿佛不想知道太多关于这件事的信息。目前的波兰,关于这段历史的诠释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波兰政府的有意操控,他们想撇清波兰在大屠杀里的责任。
位于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西南六十公里外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约有110万犹太人在此被杀害。
3.
从“拥抱”欧洲到“反叛”欧洲
理想国:那如今“东欧”对“西欧”的浪漫想象依旧如初吗?毕竟他们成为所谓“西方世界”久矣。
霍夫曼:今天的情形非常复杂了。以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东欧的主要国家为例。当东欧剧变发生时,他们都非常欣喜。但与此同时,我也可以看到他们向“自由”过渡的艰难。自由地做出选择对于他们来说很难,人们突然开始必须自主选择自己的职业,决定送孩子进什么大学,决定要投票给哪一个政党。这一切突如其来的“选择”对他们来说很难。而且另一方面,东欧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也骤然被拉大了,有些人仍然像以前一样贫穷,但有些人却一夜暴富了。总之许多情形都十分令人沮丧。即使如此,那时的他们仍然想要强烈地成为欧盟的一员。
但东欧各国在最近对欧盟的一些原则的反抗得非常强烈,比如匈牙利正如你现在所知道的那样,出现了一个极右翼的保守政府。波兰的情形也非常相似,选举出了一个保守政府,即使不像匈牙利那样令人害怕,但也正在以一种令人担忧的方式限制宪法自由。我在波兰与之交谈的很多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都对此感到非常困惑。但我想我或许能够理解。
《波妮亚, 1863》(波妮亚为波兰国家化身),扬·马泰伊科绘于1864年, 内容反映了波兰在1863年1月的一场以失败告终的反对沙皇俄国的起义。画中被捕者等待被押送至西伯利亚,俄军军官和士兵监督铁匠将黑衣妇女(波妮亚)铐上手铐。
我对此的解释有着这么一个理论,因为波兰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处在“反叛”中的国家。波兰在十九世纪里曾三次反抗沙皇俄国,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有着最顽强地对于纳粹德国的抵抗,当时在波兰战场甚至成了最危险、残酷的战场。在波兰,有三百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了,但也有三百万非犹太人的波兰人战死了。总之,这一切都让“反叛”在波兰人心中根深蒂固。目前被选出来的这个右翼保守的新政府主要是由波兰的年轻人投出来的。这些波兰的年轻人一直在这种渲染波兰的“反叛”传统的环境中长大。所以,现在他们开始反抗欧盟的规则,反对那些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
在某种程度上,匈牙利目前的混乱状态也应该得到一些理解与同情。因为对他们来说,适应一个全新的所谓“欧洲人”生活是需要时间。例如,同性恋、同性婚姻、多元身份认同这些,但他们目前好像不得不快速地去适应这些。他们根本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去调整自己来适应、接纳这些东西。你知道哪怕“西欧”在接纳这些东西上,都花了不少时间。
4.
集团阴影下,始终被压抑的民族主义诉求
理想国:您此前提到了民族主义。目前,整个欧洲,包括东欧都正在经历民族主义的回潮。但在东欧这件事情或许有些不同。因为东欧曾经由苏联,由共产党控制。而所有的共产党都声称他们是世界主义者或国际主义者,东欧人想必听了许久那一套国际主义的说辞。因此,东欧国家当下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他们对欧盟的反抗,可否从他们从前在苏联治下被压抑了的民族主义诉求来理解?
霍夫曼:嗯,是的,这或许可以解释。实际上,在苏联时期,这些东欧国家变得非常均质化,因为苏联禁止讨论所有与民族认同相关的问题。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会被严厉地审查,可以说成为了一个禁忌。所以,他们目前很希望保有民族国家身份,甚至希望可以是一种纯粹的民族国家身份。你知道在西欧,所谓宣扬追求纯粹的民族国家诉求在政治正确的信条下已经不可能了。在西欧,除了一些非常保守的人之外,他们不想强调说我们是“某国人”,因为这话在政治上十分不正确。但在东欧,他们希望这样做,而且他们也做了。
比如,东欧各国就明确地表示不想接纳难民或移民,特别是那些来自伊斯兰国家的。他们认为移民太多,增加的速度太快了,移民又难以和谐地融于本地社会。那么,东欧认为他们不想要这些人。但这有些讽刺,因为“东欧”希望成为“西欧”,他们希望得到欧盟的所有好处,但却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且,也有许多东欧国家的人移民到了比如英国这些西欧国家,但东欧国家又不希望有移民去到他们那里,虽然目前东欧一些国家的官方口径说,他们希望他们的那些外出移民能够回来。总之,移民问题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保加利亚由于移民外流,失去了40%的人口。我认为这真是一个悲剧。我爱保加利亚,我去过那里旅行,认为那是一个极好的地方。但他们却失去了那么多人口。
电影《别了,列宁》,讲述了一个对共产主义虔诚的东德母亲在目睹儿子亚历克斯游行被捕后晕倒,母亲因8个月昏迷而错过了一整个东欧剧变。而母亲醒来后,医生嘱咐亚历克斯,他母亲要切忌任何刺激,亚历克斯决定在母亲康复之前要瞒住一切。
5.
对苏联的怀旧情绪
理想国:东欧人对于苏联时期的生活有怀旧情绪吗?
霍夫曼:不管你信不信,有些人真的很怀念苏联,这或许能说明,甭管好赖,人总能怀念任何往事。(笑)有一部名为《别了,列宁》的德国电影。那部电影就显示了人们对于苏联时期的怀旧之情。我认为怀旧情绪的持续时间倒没有太久,他们主要在怀念那个时代里被共享的集体性状态,比方说每个人都很穷,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被压抑着,这些成了一个共通经验。而且,在那个时候,人们互相都很能够支持彼此,在情感上也都很亲密。这也是他们怀旧的事情。我至今都记得在我小时候,我们一家与我的邻居一家一起坐在地上打开收音机,一起收听广播的场景。另外,人们在那个时候也积极地参与政治。他们有着仿佛看起来明晰的政治目标。他们似乎清楚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在反对些什么。他们认为他们都参与到政治生活里了。
在前去霍夫曼家中拜访的路上,经过了弗洛伊德晚年在伦敦的家。霍夫曼在《回访历史》的前言部分曾引用弗洛伊德对幸福的论述以解释自己写作此游记的目的。她如此写道,“弗洛伊德说所谓的幸福,就是童年希望的实现,那么有意义的知识,或许就是童年好奇获得了满足。”
6.
飘零的四海为家者
理想国:自您离开祖国波兰已有几十年了。您在美国度过了几乎半生,目前人又来到英国生活。波兰人,犹太人,纽约人,伦敦人,欧洲人,东欧人等身份,在您身上似乎都融汇在了一起。所以,我很好奇您会如何解读自己的身份?
霍夫曼:我希望有人能告诉我。(笑)你知道有一个词,叫作“飘零的四海为家者”。这本为一个俄语词汇,专门用来描述犹太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身份认同。我认为自己便是这么一个“飘零的四海为家者”。我待过的这些地方都组成了我内在的一些部分,美国当然成了我的一部分,因为我的知识分子生活在那里开始,美国承诺的所谓——美国是一个能够真正实现自己能力的地方,在我的人生经历可以得到验证。我没有显赫的背景,我可以说什么都不是。我的父母虽然说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但他们非常贫穷。然而,我却在美国得到向上流动的机会,我毕业后被纽约时报聘用了。我真的非常感激在美国所经历的一切。
然而,英国这里好像目前更适合我,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但我确实感到我是英国人了。我非常喜欢伦敦,我常常开玩笑说或许因为伦敦正好在曼哈顿和克拉科夫(波兰第二大城市,霍夫曼的童年生活在此度过)的中间点上。我目前也会自认为是伦敦人。比方说,这段时间我被英国脱欧乱局搞得心情很低落,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对英国这个地方生发出了一些的联结。英国有很多方面都吸引我。首先,英国人说的英语是如此优美。其次,英国人略带讽刺的幽默感。这一点是英国这个国家与波兰的共同点,或许因为英国和波兰也确实有着很长久的互相往来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非常多波兰人在英国定居。另外,英国人都非常文明、得体。不像纽约,那个地方的人太有侵略性。在英国,人们似乎知道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得体地去做。最后,则是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我很惊讶于这个全民医疗体系的存在,一开始我以为这会是一个非常冗杂、庞大的官僚机构,但来了才发现它居然很容易操作,几乎只需要我的地址而已。因此,相较于美国,英国有这个全民医疗体系造成了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因为在美国,如果你挣得不够多,便支付不起有质量的医疗,因此人们在那里总会对自己的医疗保障感到焦虑与担忧。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我在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机构(NHS)里经历到的英国人幽默感的故事。我在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注册了,然后我感冒了去看医生,我告诉他我浑身疼,很痛苦,非常不舒服。他说:“不要担心。一切只会变得愈来愈糟。”(笑)
访者介绍:郝汉,理想国译丛[Mirror] 海外作者访谈特派员,英国利兹大学Sociology在读,曾参与《锵锵三人行》节目的选题策划。
【 M 观察 】
【相关图书】
《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
伊娃·霍夫曼 著
点击书封购买
1989年前后,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人们曾经深恶痛绝,同时自己的生活又深植于其中的世界观解体,长期承袭的生活方式被迫重置。《回访历史》是伊娃霍夫曼在东欧游历的记录。她在1989年返回故乡,见证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正在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如何“创造他们的历史”。借由与当地各阶层民众的谈话,以及对所见所感的忠实记录,本书呈现了当时东欧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的转变。
作者介绍
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美籍波兰犹太裔作家。与双亲逃过纳粹大屠杀后移民加拿大,后于美国求学。曾于哥伦比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塔夫茨大学等校任教,并曾任《纽约时报》编辑、《纽约时报》书评版主编。著作《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由理想国出版。
转载:请联系后台
商业合作或投稿:[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