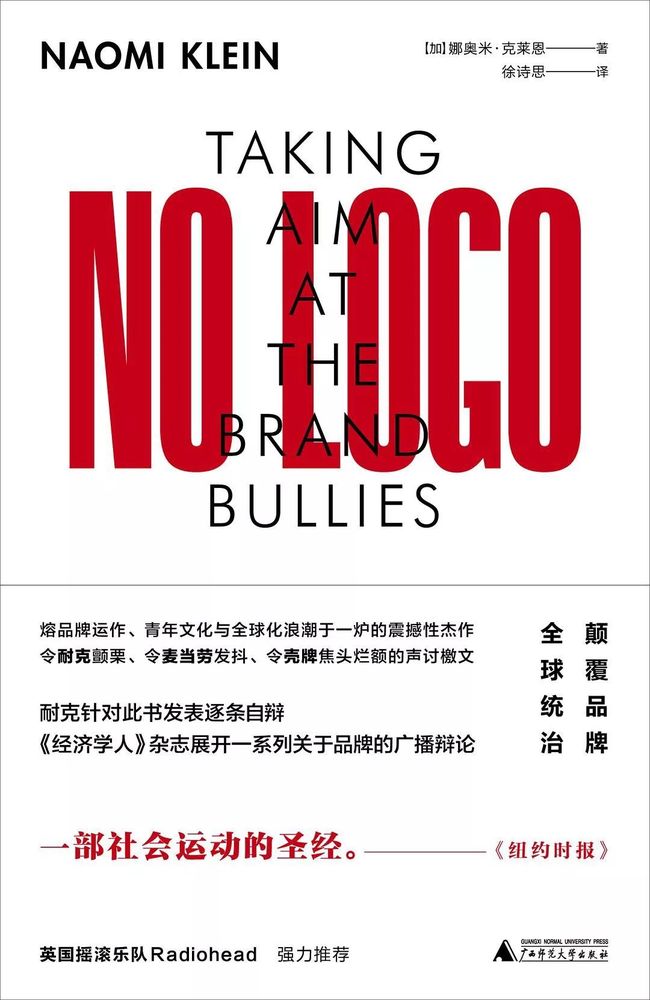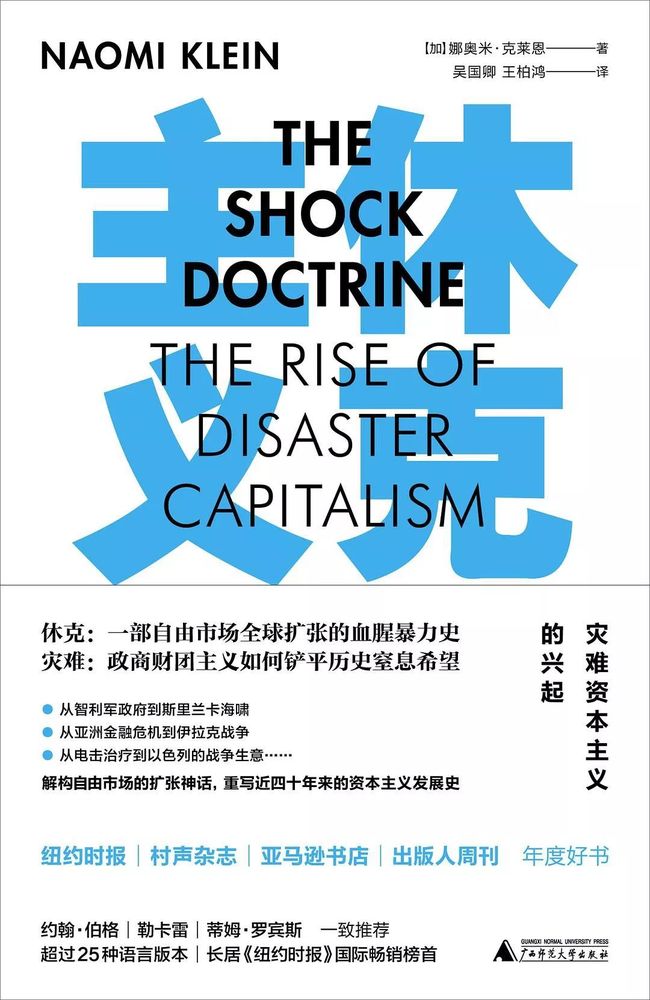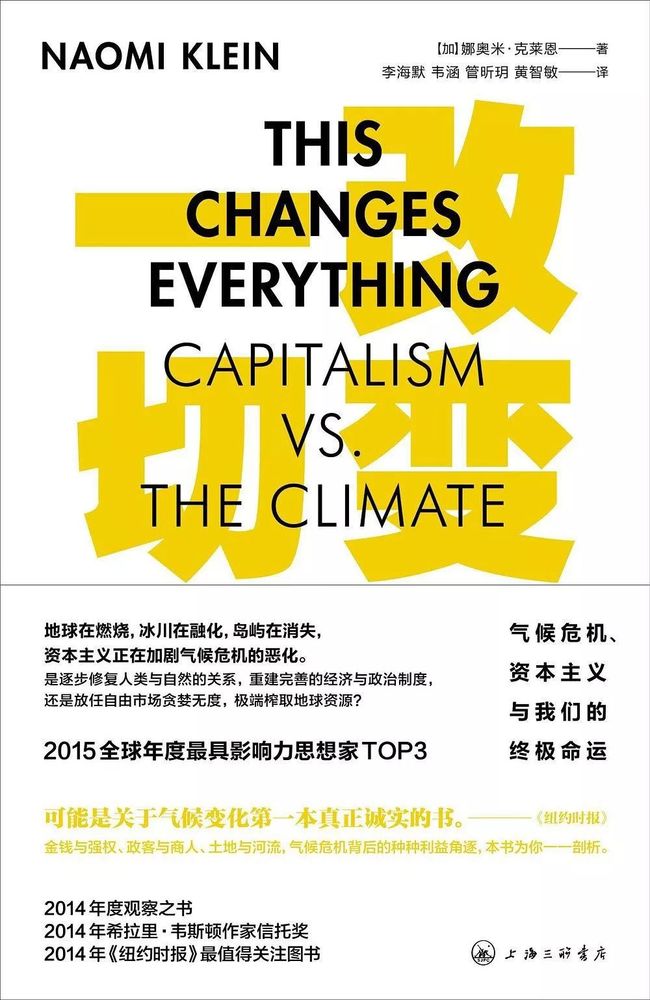交出你的灵魂,换取一份工作
最近,美国软件巨头甲骨文突然在中国宣布大规模裁员,“甲骨文被裁员工值不值得同情”成为夹在“996”和“669”热点之间,关于跨国企业中的中国员工“安于享受外企的高薪资、高福利、低压力的工作,最终活成了那只被温水里煮的青蛙”的鸡汤式批评,令职场人吐槽不断。
199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不景气时成年的那一代人几乎毫无例外不信任政客及企业,接纳了一套滋生不安感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体系:更贪婪、更强悍、更专心致志。Just Do It。成功只能靠自己。正如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不把职场视为灵魂的延伸。
跨国企业的裁员和撤离验证着自由市场清楚的信息:好工作对于生意无益,对于“经济”无益,应该不惜代价规避之。然而在这背后更沉重的真相是企业不再创造工作,只是在卷取利益,那我们将走向何种结局?这篇来自娜奥米·克莱恩的文章《培养不忠》,选摘自《NO LOGO》,正试图正视和传递其中的脉络与噪音。
1.
多变的职场最终啃蚀了我们的集体信念
1993年,当我从大学退学之际,有工作的朋友屈指可数。不论是年复一年没工作的暑假、百无聊赖决定继续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学经费削减的日子,抑或双亲失业的悲惨时节,我们一遍又一遍对彼此复述:“经济不景气嘛。”正如我们后来把从干旱到洪水的一切大小事都归罪于厄尔尼诺现象一样,不景气就是经济系统的坏天气,吞噬一切工作,一如密苏里的拖车屋停车场。
当工作消失时,我们了解这是经济艰难所致,似乎每一个人都被波及(尽管每个人遭受的冲击可能不同),从面临破产的公司总裁,到张牙舞爪的政客——每一个人,不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而我和我的中产阶级友人,当我们半调子地找工作时也不例外。从经济不景气到严酷的全球经济,这转变发生得如此突然,总觉得好像是我哪天生了病,便错失了一切——就像是十年级的代数课,我永远都在努力追赶别人。我所知道的就是,前一分钟我们还一起陷在经济不景气里,下一分钟,一批新企业领袖就有如凤凰一样浴火重生(西装崭新笔挺,信心满满),宣布新黄金时代的来临。但是,当工作重现的时候(假如真的重现的话),也已改头换面了。
对于出口加工区之外包工厂的员工而言,对于工业化国家里成群的临时雇员、兼职者、服务业员工而言,现代的雇主看起来就像厚脸皮的一夜情对象,在了无意义的露水姻缘之后,还敢奢求一夫一妻制的忠实,而且许多雇主甚至真得逞了好一段时日呢。许多人因为裁员及黯淡的经济远景而担惊受怕多年,确实已接受了没鱼虾也好这套说词。不过,日益剧增的证据显示,多变的职场最终啃蚀了我们的集体信念,不只是对个别的企业,还有涓滴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
暴涨的利润以及增长率,再加上大企业首席执行官支付自己的惊人薪水及红利,彻底改变了员工当初接受低薪及缩水福利的情境,让许多人觉得自己被耍了。这种态度的转变,再也没有比1997年大众对UPS罢工的同情还要明显的了。尽管美国人向来以不同情罢工劳工而闻名于世,UPS兼职员工的苦楚却打动了大家的心。民意调查显示,有55%的美国人支持UPS员工,只有27%站在投资方这一边。凯福(Keffo)是一份为临时雇员而编的辛辣在线杂志的编辑,他总结了大众的想法:
“日复一日,(人们)听闻、阅读经济宏景的报道,你无需具备火箭科学家的智慧就能了解,呃,假如UPS经营得那么棒,为什么他们不多付员工一点钱?为什么他们不将兼职雇员扶正为全职雇员?又为什么他们的脏手还紧紧扣住员工的退休基金不放?因此,在命运女神的摆弄下,所有‘正面的’经济新闻都站在递送员这边,齐声反对UPS。”
UPS了解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便同意将1万名兼职员工扶正为全职员工,时薪升为两倍,并允诺在五年内会将兼职员工的薪水提升35%。UPS副董事长奥尔登出面解释公司为什么让步,他说公司未曾料到,自己的员工会成为冲着新经济而来之怒火的象征。“假如早知道事情将从UPS员工身上扩及所有的美国兼职员工,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
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 Inc.,缩写为UPS)(NYSE:UPS),是世界最大的快递公司。2018年11月,UPS公司曾发布通知:将在11月7日之后停止接受夜间货运服务,因为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会有11000名工会工人罢工。
2.
“创造工作机会”曾是企业的保护色
抵御“破坏环境或侵害人权”谴责
企业对于裁员与重组不再隐瞒不过是最近三四年的事而已,不再躲在必然使用的借口背后,转而面无愧色地公开谈论自己对于雇用员工一事的反感,更极端的例子就是全盘撤出人力市场。过去,跨国企业吹嘘自己是“工作机会增长的引擎”,并借此争取形形色色的政府补助,如今,他们偏好自称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假如你刚好在找工作,这就另当别论了。企业确实使经济“增长”,但一如我们所见,他们采取的手段就是裁员、合并、移居海外——换言之,贬抑雇员,并减少雇员。而且,随着经济增长,直接为全球最大企业所雇用的人数比率确实在减少。握有超过33%全球生产性资产的跨国企业,却只占全球直接雇员的5%。虽然全球前100强企业的总资产在1990到1997年间增加了288%,在同样的狂飙时期中,这些企业的雇员增长率却不到9%。
最惊人的数字出现在1998年,尽管美国经济表现出色,尽管失业率降到史无前例的新低,美国各企业裁掉了67.7万个固定职位——比近十年来任何一年的裁员率都高。这批裁员有九分之一是合并的后遗症,还有许多裁员来自制造部门。一如美国的低失业率所显示,裁员的公司中有三分之二会创造新的工作,而被裁的员工也很快会找到其他的差事。但这项惊人的裁员数字显示的是,员工与企业雇主之间稳定、可靠的关系,和失业率抑或经济的相对健全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甚或完全无关。即便是经济最景气的时期,人们所体验到的仍是愈来愈少的安定感——事实上,经济荣景也许(至少有部分)正源自这种安定感的丧失。
创造工作机会,尤其是全职、薪水不错的稳定工作,曾是企业使命的一部分,如今,不论公司的利润高低,这项使命似乎已被许多大企业打入冷宫。劳工不再是健全营运的一部分,反而逐渐被企业界视为无可避免的负担,有如支付所得税,抑或是昂贵的麻烦事,就像不准将有毒废弃物倒进湖里。政客也许会说,创造工作机会是企业的首要任务,但是,每回宣布大批裁员,股市的反应总是上扬,而当员工看似要加薪时,股价总是下跌。不论我们是循着何种怪异的路径沦落至此,如今我们的自由市场送出了一项清楚的信息:好工作对于生意无益,对于“经济”无益,应该不惜代价规避之。这项等式在短期间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利润,固然无可否认,但将来很可能证明是产业领袖的失策。一旦公司抛弃了工作创造者的自我认同,就自陷于遭人抵制的位置,因为人们了解到,经济的平稳发展对自己并无明显的好处可言。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1997年的报告所言,“日益升高的不平等使全球化面临政治性反弹的严重威胁,可能来自北半球,也可能来自南半球......1920及1930年代赤裸裸、扰人地提醒着我们,对于市场及经济开放的信心,有多快可以被政治事件击垮”。
纪录片《大企业》
随着亚洲及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效应一发不可收拾,翌年一份针对“人类发展”的联合国报告说得更严重:联合国发展计划的主持人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注意到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表示“富人的财产多得惊人,发展的分配必须更加平均”。
最近你愈来愈常听到这种论调:反全球化风潮即将爆发的警语,使得企业及政治领袖在瑞士达沃斯的年度欢聚蒙上一层阴影。商业媒体充斥着不安的预测,比如《商业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即表示:“企业荷包鼓鼓的景象,竟与美国人持续停滞不前的生活水平共存,在政治上很难解释。”而这就是失业率达历史新低的美国。加拿大及欧盟各国的情况还更令人不安,前者的失业率是8.3%,后者的平均失业率是11.5%。
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的诺瓦公司,其首席执行官是特德·纽沃尔,他在全国议题企业会议上发表演说,表示有超过20%的加拿大人,其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之下,这可说是一枚“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确实,次要的产业培养出一批争先恐后、自称为道德先知的首席执行官:他们著书谈论新的“股东社会”(stockholder society),在午餐会报时公开谴责同行没良心,宣布这会儿该是企业领袖面对日益升高的经济不均问题的时候了。问题在于,他们无法就谁来打头阵取得共识。
担心穷人上街抗争的心理,可说与护城河的历史一样悠久,特别是财富分配不均的经济超繁荣时期。罗素(Bertrand Russell)写道,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上层阶级的梦魇就是劳动阶级会造反,好摆脱“恐怖的贫穷”;他们为此妄想症所苦,以致“彼得卢事件发生时,许多大型乡间别墅都备有大炮,以防暴民攻击。我那死于1869年的外祖父,当他最后缠绵病榻、神志不清之际,听到街上传来一声巨响,当下认为是革命爆发了, 可见至少在潜意识里,革命的或然性伴随着他度过长久的富裕生活”。
我有一位家人定居印度的朋友,说她住在旁遮普省的婶婶是那么害怕自家仆人会造反,因而把厨房的菜刀全锁了起来,仆人只好用磨尖的棒子切菜。同样的道理,愈来愈多的美国人搬进门禁森严的社区,只因郊区已不再能提供适当的保护,让人远离可知的都会危险。
尽管联合国持续表示贫富之间的鸿沟与日俱增,尽管西方中产阶级的消失备受注目,但我们身为地球公民所面临的最严重企业过失,也许并非工作以及收入水平的问题:理论上,这可以逆转。更糟糕的是,长期以来企业对于自然环境、食物供应、当地人民及文化所犯下的罪行。即便如此,对长期雇用员工的热忱不再,确实是引发反企业的抗争风气最重要的因素,这也是使得市场在面对广泛的“社会动荡”(social unrest,引述自《华尔街日报》)时,会如此脆弱的原因。
当企业还被视为财富分配的工具时(让工作及税收有效地从上方滴落到下方),他们至少让市民从事浮士德交易(Faustian bargain),用对企业利益的忠诚,换取可靠的薪水。过去,创造工作机会就像是一副盔甲,帮助企业抵御破坏环境或侵害人权的天谴。
再也没有比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工作vs.环境” 论战更能彰显这副盔甲的保护效果了。举例来说,当时正在发展中的运动壁垒分明,一边支持伐木工的权利,一边则想要保护老森林。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激进人士坐公交车从城里来抗议,而伐木工忠心耿耿地站在世世代代维系自家社区的跨国企业这一边。可如今,对于许多参与者而言,这种分野变得愈来愈模糊。冷酷执行的裁员、突然关厂、迁厂海外的持续威胁,剥夺了蓝领工人的权利,企业也因而失去了天然的盟友。
今日,很难找到心满意足的企业城,城中居民毫不觉得被当地企业出卖。而且,企业不再让社区派系分立,反而逐渐将劳工、环保、人权问题串成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没过多久,真相 就逐渐明朗:比如说,无止境地追求利润导致老森林惨遭砍伐,将工厂迁到印度尼西亚导致伐木城镇一蹶不振,两者的背后其实是同一套逻辑。英国的无政府主义环保人士约翰·乔丹(John Jordan)是这么说的:“跨国企业正在影响民主制度、工作、社区、 文化以及生物界。无意之间,他们帮助我们将所有的问题视为一套系统,让我们将每一个问题相互联结,不再单独看待。”
纪录片《大企业》
3.
新生入学第一事:开始存退休金
这股即将爆发的反弹,所牵涉的并非只是个人的不满而已。即便你刚好是有份好工作、从没被炒过鱿鱼的幸运儿,每一个人都听闻过类似的警告——就算不是针对自己,也和自己的孩 子、父母或朋友有关。我们生活在工作没保障的文化里,自立自强(self-sufficient)的信息人人耳熟能详。放眼北美洲,载货卡车朝墨西哥扬长而去;工人在工厂门口哭泣;废弃工业城里只见用木板钉死的窗户;人们睡在门口以及人行道上——以上种种就是这时代最强而有力的经济意象:烙印在集体意义里的隐喻,象征一个持续将利润摆在人类之上、毫无愧色的经济体。
最能明白感受这种信息的人,也许就是在1990年代初、经济不景气时成年的那一代吧。几乎毫无例外,当他们勾勒生活远景时,总有重重的声音告诉他们,不要抱持太高的期待,别把飞黄腾达的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假如他们想要在通用汽车、耐克或通用电器找差事,那声音就会告诉他,其实在企业界的任何地方都一样,信息都是:别指望别人。为免他们碰巧没注意到,高中的辅导老师举办如何开创“我公司”的研讨会、晚间新闻充斥着退休基金马上就要没了的消息、美国万全保险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这一类的公司鼓励所有人“做自己的靠山”,这一切都强化了这种信息。
放眼北美的大学校园,新生入学第一周的活动(校园生活首次呈现学生面前),如今是由共同基金的公司所赞助;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劝诱新进来的学生开始存自己的退休基金,而他们甚至连专业都还没决定呢。
这一切都是有影响的。根据人口统计营销学的圣经《扬克洛维奇报告》(The Yankelovich Report),相信必须自立自强的人,每代增加三分之一——从“成熟的一代”(Matures,生 于1909年到1945年)、“婴儿潮”(Boomers,生于1946年到1964年),再到“X世代”(不严谨且不太准确的定义,生于1965年迄今的所有人)。“超过三分之二的X世代同意:‘在这个世界上,拿得到的就要拿,因为没有人会给我任何东西。’同意这点的婴儿潮及成熟的一代就少多了——分别只有二分之一及三分之一。”
纽约的DMB&B广告公司研究全球的青少年,也发现相似的态度。“从满坑满谷标榜个人态度的对象可知,全球青少年最一致认同的就是:‘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决定权只在我。’”参与调查的美国青少年中,十个有九个认同完全自力更生的精神。
这种态度的转变促使共同基金产业大发利市。“为什么X世代那么注重存钱的需求呢?”《商业周刊》一位记者疑惑,“大多与自力更生有关。他们相信成功只能靠自己,不太相信退休时能仰赖社会福利金及传统的公司退休金过活。”事实上,假如你相信商业媒体的话,这种自力更生精神的唯一作用,就是引发一波惨烈的创业新浪潮,不靠任何人的孩子个个都要争第一。
毫无疑问,许多年轻人由于不信任政客及企业,因而接纳了这套滋生不安感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体系:他们会更贪婪、更强悍、更专心致志。他们会Just Do It。但是,那些无法拿到 MBA的人、那些不想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或理查德·布兰森的人该怎么办呢?企业一心想摆脱掉他们,为什么他们要为企业的经济愿景尽心尽力?放眼整个成年生活,企业轰炸他们的唯一信息就是“别指望我们”,对这种企业有何种忠诚的动机可言呢?
问题不单单是失业率而已。倘若你假设一份传统的薪水就能买到许多企业曾习以为常的忠诚度及保护(有时确实如此),那就大错特错了。从前那种为雇主终身服务的认同感,是临时的、兼职的、低薪的工作所激发不出来的。请在打烊前十五分钟去任何一家大卖场瞧瞧,你会发现崭新的劳资关系正在运作:所有的低薪店员排成一列,将手提包和背包打开,好做“提包检查”。零售业员工会告诉你,经理每天在他们身上找寻失窃的商品,已成了例行公事。
而且,根据佛罗里达大学的安全研究计划(Security Research Project)所述,这种疑心不是没道理的:研究显示,1998年全美零售业的货物失窃总数有42.7%是员工监守自盗,是史上最高的数据。星巴克的店员史蒂夫·埃默里喜欢引用某个同情的客人的话:“只要肯丢花生米,就可以抓到猴子。”当他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想起两个月前从印度尼西亚一群耐克员工口中听到的事。她们盘着腿在宿舍里坐成一圈,告诉我,在内心深处,她们希望自己的工厂烧得片甲不留。可以理解为何工厂工人的情绪会比西方世界麦当劳员工的不满极端得多——同理可证,在印度尼西亚的耐克工厂门前做“提包查检”的警卫,可是佩有左轮手枪的。
纪录片《大企业》
然而,正是在数百万临时员工的队伍里,最有可能寻觅到反企业运动的滋生地。由于大多数的临时雇员并不会在一个职位待得太久,久到让人记住其劳动的价值,绩效原则(merit principle,曾是神圣的资本主义守则)变得毫无意义可言。而情况可能令人极端泄气。“马上,这个城市里就没有我没做过事的地方了,”戈德写道,她是一名有 20 年秘书经验的临时雇员,“我在15家临时雇员经纪公司登记,就像是在拉斯维加斯玩吃角子老虎(Pocket Casino)一样。他们经常打电话给我,口气活像二手车销售员。‘我知道我很快就会帮你弄到完美的工作。’”
这句话出自《临时雇奴》(Temp Slave),那是一份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Madison)出版的小刊物,专门用来让为人员工者宣泄无止境的怨恨之情。在此,被标示为抛弃式的员工, 发泄着自己对企业的愤怒;企业把他们当成器材一样租借过来,然后再把用过的旧货送还给经纪公司。从前的临时雇员没有讨论这些事情的对象——工作的性质使他们彼此隔绝,这也使得 他们在临时的工作场合与领固定薪水的同事疏远。因此,无怪乎《临时雇奴》以及“全年无休临时雇员”这类型的网站上,沸腾着受压抑的敌意;这儿不但提供如何瘫痪雇主电脑系统的实用小秘诀,还可见到标题为“每个人都讨厌临时雇员,彼此彼此!”与“真无聊,临时雇员的职场生活无聊透顶”的文章。
一如临时雇员不适用绩效原则,像职业球员一般来来去去的首席执行官亦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童话中,收发室的小弟一步一步往上爬,成为公司的总裁,但临时的首席执行官是对这种传奇的迎头痛击。今日的经理人似乎只管互相交换高阶职位,有如天之骄子般生于与世隔绝的琼楼玉宇。在这种脉络中,从收发室步步高升的梦想愈来愈不可能实现——而且收发室可能已外包给皮特尼·鲍恩斯(Pitney Bowes)了,员工全是永久的临时雇员。
这就是微软的情况;此间临时雇员的怒火烧得比其他地方都炽热,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另外一点是,微软公开承认,临时雇员后备队的存在,是为了保障核心的永久员工不受自由市场蹂躏。每当哪一条产品线被腰斩,每当聪明的成本缩减新法门出现,受影响的总是临时雇员。假如你询问经纪公司,他们会说顾客并不在意自己被当成像过时的软件一样——毕竟,比尔·盖茨从来没有给他们任何承诺。“一旦人们晓得这只是临时的安排,当某天任务结束时,就不会有信任感破灭这回事。”Wasser Group的总裁Peg Cheirett 解释道,该公司是为微软提供临时雇员的经纪公司之一。
毫无疑问,盖茨设计的缩编法门使微软无须面对1980年代晚期IBM老板的处境;当IBM砍掉3.7万人时,指责公司背叛员工的哀号声震耳欲聋,以为自己坐拥铁饭碗的员工真的被吓到了。微软的临时雇员没有理由对比尔·盖茨怀抱任何期待,这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尽管微软园区的大门不会被抗议员工包围,却不能防止黑客从电脑系统内部入侵〔请回想1998年,黑客集团死牛崇拜(Cult of the Dead Cow)发表了为微软量身定做的黑客软件后洞(Back Orifice),从网络下载的次数高达30万次〕。
微软的永久临时雇员每天都做着在硅谷淘金的资本主义美梦,然而他们比其他人更了然于心,这场派对得有请帖才能进场。因此,尽管微软长期员工的企业向心力闻名于世,微软永久临时雇员的恨意也是举世无双。当记者询问他们对雇主作何感想时,其所提供的精彩答案如下:“他们看待你有如死水上的泡泡”;“这个制度里的人分成两种阶级,恐惧、自卑、嫌恶也从中而生”。
上图:微软总裁兼企业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脸上被丢派。 下图:生物烘焙大队(Biotic Baking Brigade)再次集结抗议。全球企业并购(global corporate takeover)的设计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得到了应得的惩罚。
3.
流失:双向的买卖
《适当的自私》(The Hungry Spirit)的作者汉迪评论这项转变:“显然,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精神契约已经变质了。现在聪明人讲的是维持‘适雇性’(employability)而非‘雇佣关系’(employment),这可以解释成,别指望我们,指望你自己,但假如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会助一臂之力的。”
但对于某些人而言(特别是年轻的员工),黑暗中仍可见到一线曙光。由于年轻人倾向于不把职场视为灵魂的延伸,从某方面来说,了解到自己永远不会碰到父母所遭遇的痛心背叛,反而让他们解脱。在这十年里踏入职场的人几乎都晓得,失业数字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而自求多福、飘忽不定的工作亦是如此。此外,假如找到工作像是纯属意外,失业就不让人那么害怕了。这种对失业的熟悉感,创造了工作者自成一格的流失——对一份稳定工作的完全依赖。我们可能会开始思索,该不该寄望终身不变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自己的存在感要随大企业的兴衰而起伏呢?
企业文化所造成的这种缓慢流失,影响的远非只是个人心理而已:技术工作者族群不自视为从一而终的企业人,他们可能会导致创造力的复兴,以及平民生活的再造——两种希望无穷的远景。有件事是确定的:他们已造成新形态的反企业政治活动。你可以从死咬微软不放的政治电脑黑客身上看到,即将在下一章出现的、专门攻击都市广告牌的“广告破坏者”(adbuster)游击队亦是如此。这点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恶作剧(譬如“打电话请病假”以及“从公司偷东西吧!因为公司正在偷你的东西!”之类的宣言)、在取名“企业美国有够烂”(Corporate America Sucks)之类的网站上,亦是历历可见。更别忘了国际性的反企业活动,比如麦当劳诽谤案所引发的反麦当劳运动, 以及针对亚洲工厂环境的反耐克风潮。
多伦多作家 Hal Niedzviecki 在《无聊的工作是放松良方》(Stupid Jobs Are Good to Relax with)一文中,将自己履历表上一连串“玩笑工作”所引发的疏离感,拿来和稳定升职却被迫提早退休的父亲的无所适从做比较。父亲上班的最后一天,哈尔帮他收拾办公桌,望着他把便条纸和其他办公室用品清出这家雇用他12年的公司。“虽然他工作了数十年,而我几乎没有上过班(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一共有五个学位),我们都走到了同样的结局。但他有上当的感觉,我没有。”
1960年代青少年文化的成员立誓要成为不被“出卖”的第一代:他们拒绝买票坐上那列标示着“终身受雇”的特快车。但是在成群年轻的兼职者、临时雇员以及短期契约员工的身上, 我们目睹了某种潜在力量更为强大的事物。我们看到的是第一波从不买别人账的员工——其中有些人是自己选择的,但大多数人是因为终身受雇的列车在过去十年来大多停在车站内。
这项转变的范围之广有目共睹。细察美国、加拿大、英国正值工作年龄的成人总数,拥有全职的固定工作、为他人而非为自己工作的人属于少数。临时雇员、兼职者、失业人士以及被就业市场完全淘汰的人(有些人是不想工作,但更多人是因为已放弃找工作的希望),如今占了正值工作年龄人口的一半以上。
换言之,大多数人都碰不上可让自己终身效忠的企业。对于年轻工作者而言,在失业、兼职以及临时工作之间持续打转, 使得他们与职场之间的关系更形薄弱。
纪录片《大企业》
【相关图书】
理想国 | 娜奥米·克莱恩作品三册
《NO LOGO》
点击图片购买
《NO LOGO》一书,让读者大众看到这些打造品牌的跨国企业背后,出现了什么样引人讨伐的勾当。本书主要探讨全球化的黑暗面、探讨跨国企业如何将品牌不断地深入消费者的私领域、探讨跨国企业如何剥削第三世界的人民以图自身利润。此书中剖析知名品牌如何征服世界,对此现象提出深刻反思,也分析反全球化的风潮将如何反扑。反对LOGO就是向NIKE这样的跨国大公司争取工资、争取工作、争取公共空间。
《休克主义》
点击图片购买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描绘了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一种新型灾难资本主义——私人财团与政治权力结盟,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旗帜,利用战争、政变,乃至自然灾害造成的休克状态,实行激进彻底的自由市场与私有化政策,其结果并未带来民主与繁荣,反而加剧社会断裂,置人民于悲惨处境。《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打破了“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神话,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扩展,远非自生自发的过程,而是依靠专制、暴力与灾难强行扩张。
《改变一切》
点击图片购买
关于为什么气候危机要求我们放弃 “自由市场”的核心意识形态,重构全球经济,乃至重塑我们的政治体系,这本书给出了睿智的解答。无论是我们自己主动做出改变,还是等待世界自己发生剧变,都意味着,现状已不再是一个选项。克莱恩指出,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纳税和医疗之外的又一个议题,更是一个警报,提醒我们修复已经多处败坏的经济体系。
转载:请联系后台
商业合作或投稿:[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