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欧美“威权民粹主义”的文化根源
对于西方社会的老人、白人和低学历者等群体而言,进步主义思潮颠覆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价值观念,破坏了他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等级和身份特权,由此导致的愤怒情绪驱使他们成为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的追随者。
作者| 黄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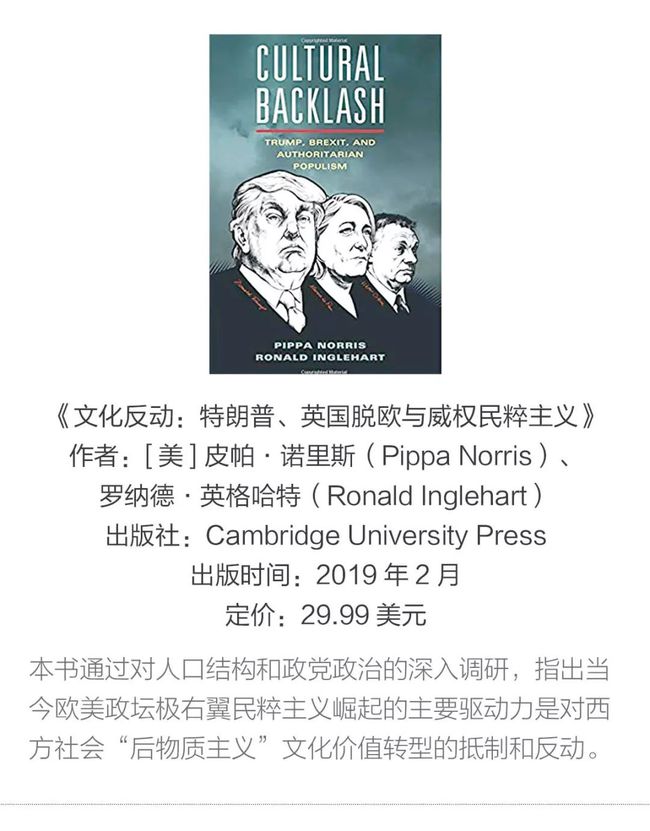
近年来,欧美极右翼民粹主义迅速崛起,甚嚣尘上。在美国,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在英国,2016年全民公投表决脱离欧洲联盟;在欧洲大陆,极右翼政党在许多国家议会中的席位都迅速增加,法国的勒庞(Marine Le Pen)、奥地利的霍弗尔(Norbert Hoffer)、荷兰的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等极右翼政客都成为人气爆棚的政治人物,对欧洲各国的自由民主制度造成了巨大冲击。
对于这种现象,一个广为接受的解释是,经济不平等是造成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
随着知识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兴起,制造业的衰退、全球化所造成的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工会的衰退和社会福利的收缩,大批底层民众入不敷出,缺乏安全感,对主流政治精英充满怨恨,极易接受鼓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欧洲联合与外来移民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的动员,认为外来的“他们”剥夺了“我们”的财富、工作机会和公共服务。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仅仅通过经济原因来解释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是不够的,这股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于当今西方社会的进步主义文化变革的反动。最近数十年来,西方社会经历了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普世主义、多元主义、环保主义、女权主义等左派进步主义思潮方兴未艾,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类似于绿党这样的左派政党。然而,对于西方社会的老人、白人和低学历者等群体而言,进步主义思潮颠覆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价值观念,破坏了他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等级和身份特权,由此导致的愤怒情绪驱使他们成为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的追随者。
上述两种解释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经济不平等所导致的不安全感,可以激发和强化对于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对进步主义文化变革的敌视。不过,到底哪个因素更为主要呢,是经济还是文化?美国政治学者诺里斯(Pippa Norris)和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文化反动:特朗普、英国脱欧与威权民粹主义》(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一书,通过对当今欧美人口结构和政党政治的深入调研,得出如下结论:文化因素是极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驱动力,传统政党基于经济理念的“左”“右”分野在今天业已被民粹主义和普世自由主义的文化分野所取代。
什么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反主流精英,相信普通人比主流精英更具备美德和智慧,对大公司、富豪阶层、职业政客、学院知识分子等当权群体充满了怀疑和怨恨。二是威权主义,追随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支持简单多数决定的直接民主(例如公投),反对注重权力制衡并且保护少数群体的代议民主。三是排外民族主义,主张“人民”是一个单一的群体,国家应当排斥来自其他国家和文化的移民,提倡单一文化而非多元文化,国家利益至上而非国际合作。
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的竞选策略就是挑动民粹主义,他成功地利用并煽动了种族仇恨、对多元文化的不宽容、孤立主义、对外来者的不信任、对女性的歧视、对穆斯林的憎恶、对政治强人的向往和对逝去荣光的怀旧情绪。当今欧洲各国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客与之类似。
曾经长期边缘化的民粹主义为何能够在当今欧美各国政坛强势崛起?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身为黑人的前总统奥巴马激起了很多白人的种族主义仇恨;英国公投脱欧则是由于很多支持脱欧的选民并不清楚这项决定将会如何损害自己的切身利益;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也都有相应的因果解释。两位作者指出,这类解释虽然每一个都很有说服力,但都只是基于某个特定国家的内政,无法说明民粹主义近年来为何能够在多个西方国家齐头并进,攻城略地,对此需要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提供宏观解释。
通过国际比较的数据研究,两位作者肯定了经济不平等是导致欧美各国民粹主义政治崛起的一项原因,但并非主要原因。在西欧国家,极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在失业人群、工人和低教育群体中占有较高比率,但是一个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得票率和该国的失业率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换言之,高失业率并不意味着极右翼政党的高得票率。在一些经济最平等、社会福利最完善、民众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例如瑞典和丹麦,民粹主义政党也是锋头甚健,这显然不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且,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的经济理念彼此差距颇大,德国共和党、英国独立党和瑞士人民党主张市场经济,而保加利亚的阿塔卡联盟和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则支持国家干预经济。
与经济解释不同,文化解释将民粹主义的兴起主要解释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是源自欧美国家的一部分充满怀旧情绪的选民对于20世纪后期兴起的西方文化价值转型的抵制和反动。
从19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后物质主义”文化价值转型,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西方社会对性的态度日益多元,特殊性取向(LGBT)人群的权利、同性婚姻、多变的性身份等等都得到社会认可;又比如对于移民、外国人和外来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态度趋向多元主义;再比如注重环保、提倡素食;等等。在政治领域,绿党等新型左派党派应运而起,在很多欧洲国家,主张生态平衡与和平主义的绿党都曾经和社会民主党联合组阁执政。
然而,这场文化价值转型也激起了那些固守传统价值观念的保守群体的恐惧和反对。
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一是年龄,人的价值观念主要形成于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经济衰退和世界大战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人从小在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下长大,因此对社会变革持有抗拒态度;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富裕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面对社会变革并不缺少安全感,因此心态开放,追求多样性。二是性别,知识经济的兴起极大地提升了女性的作用和地位。传统父权主义的大男人价值观,逐渐被追求两性平等和婚姻多样性的女性主义思潮所取代;与此同时,特殊性取向(LGBT)人群也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三是教育程度,受过高等教育者容易在文化价值转型中如鱼得水,受教育水平较低者则较难适应和接受。四是宗教,宗教越是局限在个体信仰的精神领域,对社会生活的干涉程度越少,文化价值的转型就越容易发生和落实。
最后一个因素是对移民和少数族群的宽容程度。这是导致当今欧美民粹主义兴起的关键因素。最近数十年来,前往欧洲和美国的移民一直不断增长,尤其是近年来,大量来自中东北非的穆斯林难民涌入欧洲,同时大批中美洲难民前往美国寻求庇护。这在欧洲和美国都激发了强烈的排外浪潮和种族歧视,要求通过强力政策限制和阻碍移民与难民。这不仅导致了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在多个欧洲国家的崛起,也造成了这些国家对欧洲联盟的离心倾向。这是因为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的边界管控相当宽松,欧洲联盟赋予并保障了欧洲联盟公民和永久居民享有统一的内部自由迁移权利,包括出入境权、居留权、就业权以及社会保障权利。英国脱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追求独立的移民政策,防范移民从其他欧盟国家无阻拦地进入英国。
在本书的主体部分,两位作者通过大量数据调查和分析,证实了上述五项文化因素确实是导致当今欧美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老年人、男人、低学历者、体制化宗教的参与者、多元化程度较低环境下的多数族群成员这五项指标,能够融贯一致地描述当今欧美民粹主义支持者群体的特征,而经济不平等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并不是一个融贯一致的指标。例如,小企业主和零售商这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群体比缺乏技术,从事体力劳动的低收入工人群体更支持民粹主义;又比如,以白人为主的农村居民,尽管生活相对宽裕,但是比生活困顿的、多元族群混居的大城市内城居民更支持民粹主义。
这并不是排斥经济因素对于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性,只是表明,经济因素本身并非决定性的主因,而是通过文化因素起作用。生计艰难所造成的不安全感和挫败感,会强化固守传统价值观念的保守心态,成为支持民粹主义的催化剂。
在对民粹主义做价值判断时,两位作者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他们认为,民粹主义的正面意义在于它有可能纠正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某些弊端。民粹主义运动可以传达草根民众的一些合理诉求,凸显被主流政客漠视的一些真问题,从而避免民主制度沦为由精英阶层主导的等级制度。
然而,民粹主义的危害性也是不容低估的。民粹主义总是和威权主义相结合,从而为政治强人、社会不宽容、非法治的治理打开了大门,损害自由民主制度赖以维系的权力分立、程序正义和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等原则。
在美国,特朗普对民主制度的破坏极其严重。他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支持,使得美国“三K党”、新纳粹等历史沉渣再度泛起,招摇过市;他对行政权力的滥用,包括指示白宫官员和内阁成员拒绝国会的传讯,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绕过国会向美墨边界派遣军队修墙等等,都严重侵犯了国会权力;他与基督教保守派的结盟,使得反堕胎团体变本加厉,多个由共和党控制的保守州相继出台严禁堕胎的法律,试图挑战最高法院在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中所做出的将女性堕胎权利视为宪法权利的判决。由于美国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极右翼政党——例如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执政的先例,故而对特朗普的威权民粹主义政治缺乏免疫力。
在欧洲,民粹主义运动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对政治体制的冲击还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2015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开放边境,让数以十万计的难民进入德国,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尤其是2015年和2016年跨年夜性侵事件的爆发,激发了排外民粹主义的兴起,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两年后的大选中一跃成为德国第三大党,改变了“二战”以后极右翼政党在议会中从来没有席位的边缘化地位。但是,德国民粹主义的兴起主要是由于移民的单一因素,因此对政治体制并未构成全面挑战。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德国的稳定是欧洲稳定的有力保障。
在今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抬头成为显着特征,例如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以23%左右的国内支持率领先于总统马克龙领导的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后者的国内支持率约为21%。但是,专注于加强欧盟的政党在欧洲议会占据了将近2/3的席位。换言之,欧洲的主流政治并未被民粹主义俘获。威权民粹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不同状况,是当前美欧裂痕急剧扩大的根本原因。
长期而言,欧美威权民粹主义的命运,取决于西方社会的“后物质主义”文化价值转型能否继续向前推进。曾几何时,舆论普遍认为,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会令“后物质主义”的文化价值转型所向披靡。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剧了信息碎片化,由此导致的“后真相时代”成为民粹主义崛起的温床;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则大大强化了威权领袖的控制力。更重要的是,如果人工智能意味着很多民众不再拥有稳定的工作,缺少一份体面职业所提供的安全感和尊严感,那么他们就无法拒绝威权民粹主义的诱惑。科技进步是否会逆转“后物质主义”的文化价值转型,是本世纪欧美乃至全球社会发展最关键的问题之一。
本文版权归第一财经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翻译。
![]()
黄湘
独立学者,资深媒体人,
现旅居美国,著有《美国裂变》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