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刘俏:更大危机在于未随经济发展培养起最稀缺的科学实证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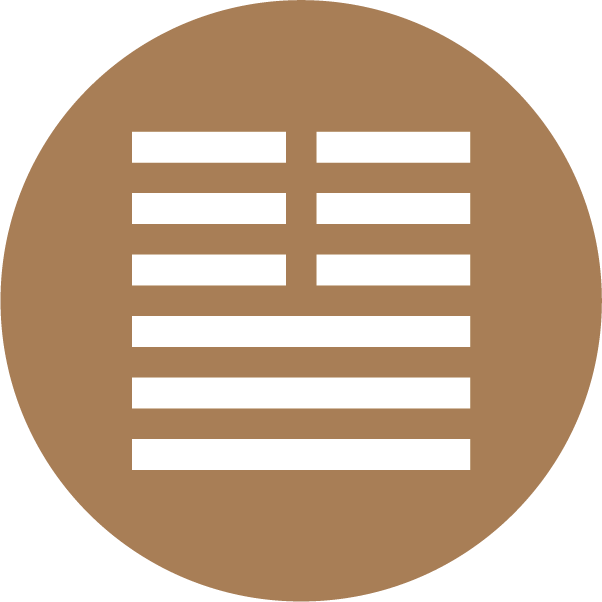 作别戊戌年,我们迎来了己亥年。
新年伊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
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巨变、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基础研究投入、资本收益率等六大方面出发,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时代挑战发表真知灼见,并提出了鞭辟入里的四大建议意见,值得仔细阅读与理解。
“我们更大的危机在于没有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培养起我们最稀缺的科学实证精神。缺乏对事物本质和内在逻辑的深刻理解,我们拱手让出思想自由,主动或是被动放弃对影响人类社会进化的第一性问题的思考,为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潮敞开大门,让一个又一个似是而非的思维泡沫引领自己,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答案”面前彻底迷失了对问题本质的认知,进而陷入更深的茫然。”——刘俏教授
原文首发于公众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洪泰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作别戊戌年,我们迎来了己亥年。
新年伊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
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巨变、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基础研究投入、资本收益率等六大方面出发,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时代挑战发表真知灼见,并提出了鞭辟入里的四大建议意见,值得仔细阅读与理解。
“我们更大的危机在于没有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培养起我们最稀缺的科学实证精神。缺乏对事物本质和内在逻辑的深刻理解,我们拱手让出思想自由,主动或是被动放弃对影响人类社会进化的第一性问题的思考,为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潮敞开大门,让一个又一个似是而非的思维泡沫引领自己,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答案”面前彻底迷失了对问题本质的认知,进而陷入更深的茫然。”——刘俏教授
原文首发于公众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洪泰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回顾刚刚逝去的戊戌年,焦虑以及无限焦虑之后的茫然无疑是两个关键词。这一年,世界风雨飘摇,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在世界范围内攻城略地;经历了近四十年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曾经的传统和荣光在“黑天鹅”和“灰犀牛”等阴影的映衬下开始出现黯淡的迹象;一生经历无数,成长于“悠长的夏天”,习惯了一定要赢的中国式的商业英雄们也纷纷落入去杠杆、质押股票爆仓和P2P暴雷等带来的满地狼藉,面对寒冬的来临一筹莫展;时代变迁下的普通人更是充满对未来的担忧,感慨他们曾经熟悉的世界逐渐退场,不可追回…...
焦虑背后是普遍的进退失据——人们或者从所谓的历史周期率里寻找各种能够慰藉自己的启示,期望新的一年峰回路转;或者固守在自己熟悉的逻辑体系里,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惊慌失措,在前行过程中出现的挫折面前自艾自怜,甚至选择放弃;或者蜂拥涌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5G技术、量子信息科学和消费升级等新鲜出炉的技术抑或概念……“没有什么比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更危险的”(德鲁克语)。
事实上,我们更大的危机在于没有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培养起我们最稀缺的科学实证精神。缺乏对事物本质和内在逻辑的深刻理解,我们拱手让出思想自由,主动或是被动放弃对影响人类社会进化的第一性问题的思考,为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潮敞开大门,让一个又一个似是而非的思维泡沫引领自己,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答案”面前彻底迷失了对问题本质的认知,进而陷入更深的茫然。
站在时间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帮助构建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那些成功因素正在式微,但是另一个全新的时代正迎面而来。我们当下急需回答的问题简单而且明确:我们在科学理性层面和精神层面是否已经做好了迎接新时代的波澜壮阔的准备?
这里,科学理性的最大价值在于让我们认识到隐身在林林总总复杂性背后的秩序和简单,建立起对那些穿透时间、具有普适性的基本规律的认知,让我们有能力去定义出那些亟待解决的第一性的重要问题;而精神层面的重要性体现在让我们展现出行动的决心和勇气,使我们能够在时代变幻的波诡云谲中沉淀下来,深刻洞察那些巨大挑战背后的机遇,用近乎于倔强的坚持直面问题并采取果断行动做出改变。
旧时风月虽然伤感,但是一个新时代的喷薄欲出不禁让人抱有期待。整理逝去时代在思想上留下的印记,塑造新的增长逻辑和发展路径,进而构建一个新的时代,过程注定蜿蜒崎岖。然而,从无尽的困难和挑战中崛起,是一个商业文明走向伟大的必经之途。
未来十数年,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经济社会面临众多亟待破题的重大挑战。
其一,全要素是构建新时代最重要的增长动能。我们现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大约是美国的43%,如果2035年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达到美国65%的水平,就需要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每年的增速比美国高1.95个百分点,对于刚刚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开始下降的中国,怎样才能在未来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其二,未来产业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我们国家2035年三大产业的GDP占比大概是3%的农业、32%的工业和65%的第三产业。如何从现在的产业结构过渡到十几年之后与高收入国家相似的产业结构?尤其是,这一过程中,如何实现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将现在占到整个就业人口27%的农业就业人口的绝大部分配置到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
其三,到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会达到37%,我们将面临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一方面是消费端的变化,对医疗、养老、财富管理、社会保障体系等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储蓄率的下降,这对我们未来保持高投资率构成巨大挑战;
其四,到2035年,保守预测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5%,从农村迁到城市的净人口数量将达到2.6亿, 这将对城市的空间布局、规划和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意味着什么?近3.7亿人生活在农村,对应着大致3-4%的农业GDP,如何在让他们从财产性收益和产业资本投入中同样获取收益,解决可能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其五,中国研发的GDP占比已超过2.1%,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我们规模巨大的研发大量投向研发的“发”,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只占研发规模的5.5%——没有对基础科学和底层技术的大量、长期投入,我们如何摆脱在关键技术上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形成产业供应链上的相对闭环?
其六,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含建筑)现阶段只是高收入国家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未来十几年我们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但是,如何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摆脱对以债务来驱动高投资率的增长模式的依赖将是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另一个挑战……
不论直接还是迂回,直面这些挑战,拥抱它们背后潜藏的机会将是时代漫长变迁的起点。如果说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及其带来的四十年的高速发展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和信心,那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从来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或是思维框架,它是一个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想探索和实践探索的伟大集成。中国发展道路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在于它以开放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发展中的第一性问题,并不断寻求以现实可行的方法去破解这些问题。
面对那些随时代变迁奔涌而至的巨大挑战, 我们唯有通过更为彻底的改革和开放,直面我们发展中的第一性问题。
这要求我们在未来以更彻底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更有效率的研发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实现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要求我们大力推进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要素等在内的要素市场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国家战略和自由市场更有效的结合;
要求我们重新梳理我们的人口政策和城镇化战略,大力保护企业家精神,大幅降低企业税负等等。
未来会更好吗?笃信“做时间的朋友”的巴菲特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阐释透过更长的时间维度捕捉历史趋势、判断事物价值的重要性:“整个二十世纪,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创伤和无数次代价昂贵的军事冲突;经历了大萧条,十几次规模不一的经济危机或是金融危机,一次石油危机,还有一次席卷全国的大流感和严重动摇人们对民主制度信心的水门事件的冲击。然而,道琼斯指数还是从世纪初的66点上升到了世纪末的11,497点。”透过更长的时间维度思考我们面临的机会和挑战,我们会发现眼前的苟且和满地鸡毛根本无法给奔涌而至的这个时代定性!我们选择张皇失措狼奔豕突,还是选择击节高歌策马扬鞭重新出发?关于未来的答案其实隐藏在现在。
桃花依旧笑春风,一个时代的逝去留下的并不仅仅是一曲悲歌。未来经年,以科学理性精神勇于面对发展中第一性的问题,以乐观和不放弃的精神捕捉那些“破裂世界里透过缝隙照进来的光”(莱昂纳德·科恩语),那么穿山越岭,我们或会迎接一个新的更伟大的时代的到来!你好,2019!
![]()
刘俏教授此前一直呼吁科学理性精神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去年,他曾在《时代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是我们在放弃自己》一文中表示,身处新时代的开端,我们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大家普遍感受到的焦虑和进退失据,而在于那一系列不断催生焦虑情绪的错误认知,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我们的思想力始终没有被培养起来这一事实。
我们并没有与经济高速增长去同步发展我们极为稀缺的科学精神。没有科学的理性精神,我们主动或是被动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脑子里固化出对“权威”和“大家”的崇拜与依附,将思想自由拱手让出,让一个又一个似是而非的思维泡沫引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进而不断加剧自己的焦虑感。
于是,面对迎面而来的各式冲击,我们雷厉风行寻找各种风口——制度风口、资源风口、商业模式风口、技术风口、甚至“无厘头”风口,把“短、平、快”的攫取利益视为当然,把建立关系和做交易的能力等同于经营管理和商业思想,把跑马圈地、占有各类资源并据此疯狂寻租看成中国式的商业规律;我们开口闭口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疗法、比特币、区块链和ICO,为能否得到那张技术”船票”而焦虑,却不知只有通过更为系统、注定辛苦的学习和独立思考才能深入理解这些技术的底层结构和支撑它们的基础设施,进而判断它们可能的商业应用场景。没有科学的理性精神,缺乏追问因果关系的想法,我们偏安于林林总总的各类思维泡沫之中,自以为是已经洞悉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找到了那些推动人类进化的源动力。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过去六十年,发展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证据告诉我们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科学规律。我们认识到反映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使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是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源于技术创新和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我们确知技术和模式创新确实影响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但这个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漫长、复杂得多。以生物技术、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主导的高科技不断改变全球产业格局的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还不到1%, 远低于1870年至1970年美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期间所取得的2%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获得了4%以上的TFP年均增长速度,很大程度解释了中国人均GDP的爆发式增长。但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高增长阶段的结束,TFP增长率在过去六年已经下降到年均2.3%的水平。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通过更多更有效的研发和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发与保护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重新塑造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占GDP百分之二的研发投入虽然绝对数量可观,但是研发的绩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大量的研发(Research & Development, 简称R&D)是发(development)而不是研(research);我们的创新也大量集中在满足用户体验和提升效率这两个层次,在以复杂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创新方面,我们严重匮乏。
缺乏科学的理性精神,我们急功近利、好奇心钝化,对建立起对人类世界、对本源和普遍性的深刻理解缺乏兴趣。我们不愿也无法专注于基础科学和底层支撑性技术的研究,通过资本实现技术上的“拿来主义。”我们躁动着,在各种各样质量不一的思维泡沫的指引下,寻找各种快速成“财”的商业逻辑与商业机会,却缺乏更大的格局去思考真正推动人类进化的力量。历史反复教育我们,人们愿意相信并乐于制造各类泡沫的原因在于只有在泡沫中他们才有机会短期攫取暴利。于是,在一个财富梦想主导一切的时代,在各式各样的思维脑洞里,在大风过后的满地狼藉中,我们感叹着埃隆·马斯克和SpaceX的奇迹,焦虑着自己的生活。这难道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时代调性吗?
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年,光绪帝颁发诏书,推行变法。未几,变法失败。变法者虽未竟事功,但留下了京师大学堂,国学之外,讲授科学,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科学精神启蒙和“赛先生”之滥觞。自此,“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蔡元培语), 致力于追求真理但宽容异见的科学精神,贯穿岁月山河于始终,敲击着我们的心灵。
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说到,“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在大分化的时代,指导性的理论和价值观分外重要,而形成超越的思想的最重要前提是科学精神。时代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是我们在放弃自己。一百二十年后,我们再度出发,诚意正心,拥抱我们从未真正拥有过的科学精神。
作者简介:
刘俏现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获得者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和中国经济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并多次由国际顶级金融与经济杂志出版;研究成果在2011年3月《经济学人》获国际巴斯夏新闻奖的《Bamboo Capitalism》一文中被大量引用。
刘教授拥有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应用数学学士学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2003年间,其曾任职于麦肯锡公司,期间负责麦肯锡在亚洲企业金融和战略策划方面的研究和知识领域,并为大型亚洲公司和跨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2010年底加入光华前,刘教授任教于香港大学,并获港大终身教职。他曾于2012年获北京大学中国工商银行优秀经济学者奖,2013年获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师服务奖等。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