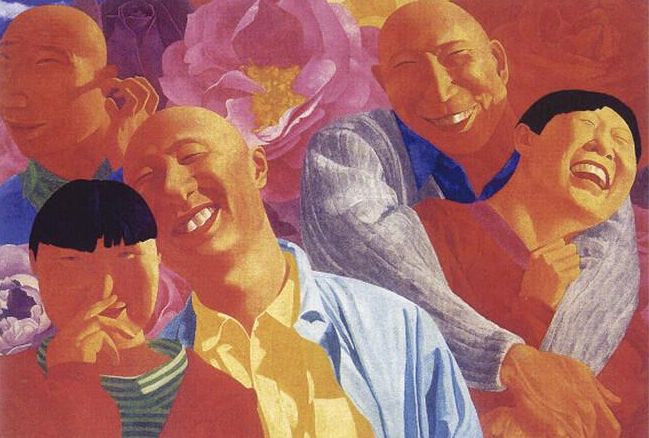大年三十
那个叫Cindy的二妮到家了
快下车的时候,她看了一眼朋友圈。
一位朋友转发了个段子:「过年了,怎么看不见Jony、Eric、Viven、Cindy发的美食、副驾、读书朋友圈了?是不是回到了老家,变成翠花,小丫,燕子,二妮,狗剩了。为啥不发朋友圈了?是不是老家没网了?」
她苦笑着灭了屏,想了想,又点亮手机,打开了飞行模式。
她有个说不上惊艳也说不上土气的普通名字,是父母给的。当有人这么称呼她的时候,她是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姑娘。
她还有个本来很洋气,后来被段子手叫烂了的英文名字,是入职的时候自己随便起的。当有人这么称呼她的时候,她是个28岁的漂亮白领。
她就是段子里总出现的那个Cindy,下车之后,所有人都会叫她二妮,或刘家二妮。
她知道,当有人这么称呼她的时候,她什么都不是,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加什么都不是。
刘家二妮不会干活,刘家二妮不会做衣裳,刘家二妮进城没挣到啥钱,刘家二妮不会伺候爷们,刘家二妮快三十了还没有对象。
但过年了,刘家二妮必须回到家里,带着热气腾腾的思乡之情,拎着沉甸甸的塑封烤鸭,换上厚厚的棉衣,绽开带着一点点眼泪的淳朴笑容,回到这片生她养她想念她的土地。
车停了,Cindy正式换好了名字,笑着对司机师傅喊了声过年好,便下了车,大步迈向那座老房。
谁说没有网,网速快的很。只是,我没什么好晒好分享的。
过年了,啊,又过年了。
大年初一
那个叫Cindy的二妮还是没能上桌吃饭
男人们围着饭桌喝着酒划着拳,女人们在厨房张罗着加菜收拾灶台,老人和孩子们坐在一边,等着男人们吃完饭。
孩子嗅着饭香哭着喊饿,老人一边从锅里夹了几块肉喂给孩子一边说:「大人吃饭孩子不能上桌」。
孩子咂摸着肉味似懂非懂的领悟了,坐到一边乖乖的看着桌上的男人们。
二妮靠在椅子上玩着手机。既不去看桌上喝酒吹牛的男人,也不去管那些听话的孩子们。
「老老实实的,二妮,别把外面那些臭毛病带回家里。」
去年二妮和爸爸说男人女人一起吃饭多好,爸爸瞪了她一眼,仿佛在亲戚面前丢尽了颜面地说道。
今年,二妮什么都不打算说了。
朋友圈开始有人晒团圆饭,有在家里吃大餐的,有在外面吃饭店的,还有在三亚的海边吃海鲜的。
二妮又想起朋友圈里面那个段子。好想去那位朋友的状态下回复一句:「不是没网,是没心情。」
可想来这么回复又是招惹来没什么意义的恶搞或安慰。算了。
「要么闭上眼睛,要么闭上嘴巴。」
二妮选择闭上嘴巴。
男人们吃完饭,坐到屋子的一边去抽烟侃大山,女人、老人和孩子们上桌吃剩下的残羹冷饭。
妈妈推了二妮一下,嗔怪地说:「这丫头,大过年的咋愁眉苦脸的呢,老看那破手机,快吃饭!一会儿凉了。」
「知道了妈。」二妮收起手机,挪向饭桌。
「早就凉了。」她心想。
大年初二
那个叫Cindy的二妮看亲戚打麻将
屋里被暖气和人们呼出来的烟熏得像北京的雾霾天,男人们围着桌打着麻将。
妈妈打了个小盹,醒来端茶倒水,放到麻将桌的桌角,爸爸没吱声,继续码着牌。
牌桌上一位亲戚的电话响了,一桌人开始起哄:「你看,准是媳妇催了,别接别接。」
男人假装爽朗的大笑,还是接起了电话。山寨手机的听筒发出一屋子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女人声音。
「你在哪?」
「打麻将呢!」
「什么时候回来?」
「你甭管了!挂了啊。」
男人们继续搓着麻将,一根接一根的烟把屋子弄的伸手不见五指。
二妮坐在床边,刷了一遍微博,又看了看朋友圈,打了个哈欠,看了看时间,快到午夜了。
那位男性亲戚的电话又响了,他刚听了一手好牌,随手挂掉了电话。
电话又响了三次,男人又按掉三次。不耐烦的表情爬上了牌桌上每个人的脸。
电话又响了,那位亲戚涨红了脸,抓起手机大喊:「催什么催!一会就回去了!」
妈妈本来又开始打盹,被这么一喊,又惊醒了过来。揉了揉眼睛轻声问:「用不用给你们添点水?」
牌桌上的爸爸很没面子的嘟囔一句:「你早该添了。」
妈妈默默起身,为桌上的每个人加满了水。
牌桌上一位叔叔看露出牙齿笑着朝躺在床上的二妮说:「二妮,你就得跟你娘多学学,多贤惠。别跟你那嫂子似的,啥都不会,就知道催男人回家,啊!」
另一个男人则假惺惺地对妈妈说:「嫂子,别管我们了,你去睡觉吧。」
妈妈没回答他们,二妮也没回答他们。
二妮只是假装看了看手表说:「呀,都快十二点了,我以为才十点呢。」
几个男人觉得有点尴尬,一桌牌被搅的稀里哗啦的响,干笑声和搅和麻将的声音,盖过了窗外的鞭炮声。
一轮牌打完,众人算算输赢约好明天的牌局就散了,爸爸客套着挨个送走了人,关起门冲二妮没好气的说:「你多余说那话。」
远处又有人放起了长长的挂鞭,噼里啪啦地摔打着浓浓的年味儿。城里的禁燃令管不到这里,就像那独守空房的嫂子的电话管不到这里一样。
大年初三
那个叫Cindy的二妮看望儿时的伙伴
二妮和小芳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还是小学到初中的同学。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也很少联系。这过年都回到老家,两个人还是要见见面。
老家没有shopping mall,也没有咖啡店。两个人就在小芳的闺房里,吹着茶杯上热腾腾的蒸汽叙旧聊天。
二妮看小芳总是眉头紧蹙,知道她有心事,便问她是不是家里闹不痛快了?
一问,问的得小芳眼泪汪汪的。
这些年,小芳的爸妈一直在城里摆摊做生意,省吃俭用好多年,一块钱一块钱地攒够了城里房子的首付。
房子是买给小芳的哥哥的。小芳不争,也不问,她知道那房子是给哥哥娶媳妇儿用的。
买房子的时候,所有的钱都填进去了,小芳的父母并没有想过给自己留钱养老。他们说,过得到一块就跟儿子过,万一跟儿子媳妇过不到一起,不啥就回老家住那套荒了几年的旧房子。
小芳的哥哥住进了房子,娶到了媳妇,也挣到了钱。
快过年的时候,哥哥给还没回家的小芳发微信,说这两年自己又赚了些钱,想换一套大房子,他和嫂子过去住,爸妈也可以过去住。这套小房子也值不了太多钱,就留给小芳住。
小芳被疼爱她的哥哥感动的涕泪满面,过年回来特地给哥哥和嫂子一人换了一台iphone。
可一进家门,就看见哥哥嫂子和爸妈坐在屋里,生着闷气。
小芳一问,才知道哥哥在城里找了这么个嫂子,怀孕之后娇气的很,过年回家,哥哥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让这位嫂子空着手跟着他进了家门。这情景被一路上的亲戚看了去,受尽了大伙儿的嘲笑,都说他找了个悍婆娘。这可丢尽了父母的老脸。
关起门来,爸爸对着哥哥嫂子就是一顿训。嫂子忙不迭的赔不是,哥哥倒是泰然自若,说城里都这样,照顾媳妇帮拎着东西没啥丢人的。
小芳听到这事,就知道这一年家里对男女的尊卑态度一点没变,心就凉了半截。
一家人闷闷不乐的吃了年夜饭,放下筷子,哥哥提出了要把房子留给小芳的事。父母一听果然是勃然大怒。母亲抹起了眼泪,父亲则是拍着桌子大喊不孝。
「你这叫什么话!你妹再过几年嫁出去,那就是泼出去的水了!」
小芳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默默地收拾碗筷,躲进自己的卧室。
后来小芳跟哥哥说房子自己不要了,免得爸妈生气。哥哥说你别理这些老规矩,听我的。
这反倒更要了小芳的命,本来是哥哥和父母的矛盾,一下子变成了自己和父母的矛盾。
「其实那房子真不值很多钱。」小芳哭着对二妮说。「我只是希望自己在选老公的时候,少被些东西绑架,多一点选择。」
二妮按着小芳的手,她理解。
她和小芳一样28岁,她和小芳一样单身。
她和小芳一样在大城市每天接触很多男孩子,她也和小芳一样总被人说眼光太高。
她们说,不是我眼光高,是到了这个岁数,我们怎么去挑选别人,别人就怎么去挑选我们。
她们说,就算童话里都是骗人的,起码婚姻应该基于爱情,而不是一套房子。
她们说,那些大城市的男孩子们在恋爱时都像极了电视剧里的角色,可到了结婚时,都会温顺地收起男人的血性,回到养儿防老的家族巢穴中,听父母那啪啦啪啦响个不停的小算盘,掂量孩子和房子与所谓爱情的此轻彼重。
她们说,暧昧的时候女人都是Rose,男人都是Jack。可熬过订婚礼包的争执、买房买车的博弈、嫁妆彩礼的纠纷,还能有多少人剩下来牵着她们的手,不变回翠花和二狗?
男尊女卑的规矩一代代压弯了女人的腰,从「女子无才便是德」一代代演变成「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看上去女人对不公的抗争愈演愈烈,而互相伤害的游戏却在一代一代养儿防老养女泼水的传承中从来没有停止,女人的腰也从没有真正的直起来。
她们深深的知道,所有城市里骄横地高喊着女权主义女孩子,都只不过是一只只炸起尖刺的刺猬,背负着来自家乡沉重无比的牌坊。
大年初四
那个叫Cindy的二妮去相亲
二妮一觉睡到了10点多,在妈妈的唠叨声中懒洋洋的爬起来。
她实在懒得去。
妈妈说,人家条件特别好,个子高,人也老实。
妈妈说,人家有手艺,家里关系硬,人家自己挣钱付的首付买了房。
妈妈说,今年你不上心,明年你就后悔。
妈妈说,人家亲戚都说了,差不多就行了,能挣钱人老实会过日子比啥不强。
二妮总不能说,只要是老家的男人,我就不想找。这话说出来太伤人,太骄傲,太不可理喻。
见面的时候,来的男人话很少,沉默的像是菜市场里捡便宜的小市民;妈妈更是比她还要紧张,低头不敢说话,就像是快要天黑的市场上吆喝着篮子里剩菜的小贩。饭桌上只有介绍人侃侃而谈,拼命地介绍着双方的优点,拼命地勾引着话题。
饭吃到三分饱,介绍人给妈妈使了一个傻子都看得懂的夸张眼神,两人便找了借口离桌而去,剩下二妮和那个腼腆的男孩子相对而坐。
二妮拿出手机假装给人回复消息,男人的额头上渗出汗珠,摸了摸兜,忽然眼睛一亮,像是摸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掏出一包东西,一脸终于找到个话题的表情兴奋地说:
「嗯,这是前两天我给我表姐求来的药,挺灵的。不知道你听说没听说过。这个叫......」
二妮没听说过药的名字,便问这药是做什么的。
「表姐42岁了,一胎生了个丫头,都七八年过去了,肚子再没个动静。表姐夫一家人对她越来越没个好脸色。表姐一直吃家里大夫给开的方子,不仅怀不上儿子,还落下了胃疼的毛病。这不我在城里工作,表姐就托付我找找高人,费了不少劲总算求来了这个方子。据说一年之内就能怀上......」
一股恶心的感觉涌上二妮的喉咙,她抢白到:「吃药怀孕这事真假先不说,生男生女是由Y染色体决定的这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那男人楞了一下,说:「是吗?这我倒真不知道。」
「高中时候就学了吧?」二妮又说到。
男人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嗨,学习不好,凑合混的......」
二妮不饶人地追问:「那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男人的头越来越低,说:「嗯就是瞎混呗,做做宣传什么的。对了,你是做什么的?」
二妮不知为何来了劲儿,昂着头连珠炮似的说:「我在一家外企,专门做智能硬件交互设计工作的,就是设计人和机器的互动过中之中一个叫做界面的层面的,算是融合了认知心理学、设计学、语言学等多门学科的复杂工种吧。这两年没打算回来发展,也没法回来发展。」
男人张大了嘴半天没做声。
妈妈回来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她轻轻叹了口气,说:「唉,这孩子,又把人家吓跑了。」
二妮耳朵红红的,低头没说话,刚才的劲儿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大年初五
那个叫二妮的Cindy决定回北京
上午送走了小芳,她说呆腻了,想提前回去玩两天。
二妮问她房子的事怎么办,她说,自己解决不了的事就随它去吧。两代人观念上的差异不是一次谈话或一场闹剧能解决的。
「只是希望等自己老了,不要再掉进这样循环的怪圈里去。」二妮感叹地说。
小芳对她说:「我最近看一本武志红的书,里面说到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就是一代一代的恶性循环,重男轻女,男人拼命逃离家庭在酒桌和牌桌上找存在,女人抓不住男人,只能拼命抓住儿子,而瞧不上迟早要嫁给别人的女儿。到了儿女这一代,男人要找一个像妈妈一样宠爱他的女人,女人则要找一个能给她家庭给不了的关爱的男人,然后双方继续对彼此失望,男人继续逃离家庭,女人继续抓儿子。这个循环像是一个咒语几千年来笼罩着中国人。」
「说的真好。能破吗?」
「除非有一个人,不惜背上不孝顺的名字,向上打破这个链条的一环,自愿成为一个被传统瞧不上的人。这个循环一旦破了,也就进行不下去了。我觉得我哥就是这样的人,他肯帮我嫂子拎着行李回老家,他肯把房子留给我。」
「你嫂子命好啊。」二妮叹了一口气。
小芳走之后,二妮也呆不住了。
家里还是每天有人来打麻将,电视里一遍一遍重播着春晚上那些煽情的歌舞小品。每当节目赤裸裸地演绎着回家的儿女和父母解开误会,热情地相拥后齐刷刷转过身来给观众拜年的时候,二妮总会尴尬的别过头去。
她为自己总憋在屋子里玩手机感到愧疚,却又会在和父母亲戚聊起她无法接受也无法改变的传统观念时感到无助和恐惧。
她知道忙碌了一年的Cindy应该放下城市里那些爸妈听不懂的世界观,老老实实的做好一个假期的二妮,生活的烦恼和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但她不想谈烦恼,不想谈工作,她只想谈谈,应该让奶奶和小孩们上桌吃饭,应该让打麻将的男人早点回家陪老婆,应该让回家的孩子们睡到自然醒,应该让男人们帮女人拿一点行李,应该让没做好抉择的女人自由的选择暂时单身。
她知道,不能说,说了,这个年就过不痛快,说了,她就是个进城呆了几年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死丫头。
过年,就应该是一家人其乐融融,女人和孩子们在厨房吃着剩菜,等着给打麻将的男人们倒上热水,看电视里一幕幕温情的解开误会含泪拥抱再转身拜年的小品,然后在天黑时关掉手机,不去看那些书籍文章旅行或新闻,任午夜牌桌上麻将呼啦啦的声音盖过窗外那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更盖过远方城市里那些孤独的心跳声。
「要么闭上眼睛,要么闭上嘴巴。」这是她的一位闺蜜告诉她的窍门。
每年都要陪爸妈过满一个春节的二妮,今年提出想早点回北京。
即使闺蜜和朋友们还没有回来,尽管街道还是空得连早点都买不到,尽管公司还没有上班,尽管那里还没有一个等她的男人。
在那里,她也许还是睡到上午10点,打开手机,刷刷微博,无所事事。
在那里,她叫Cindy。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