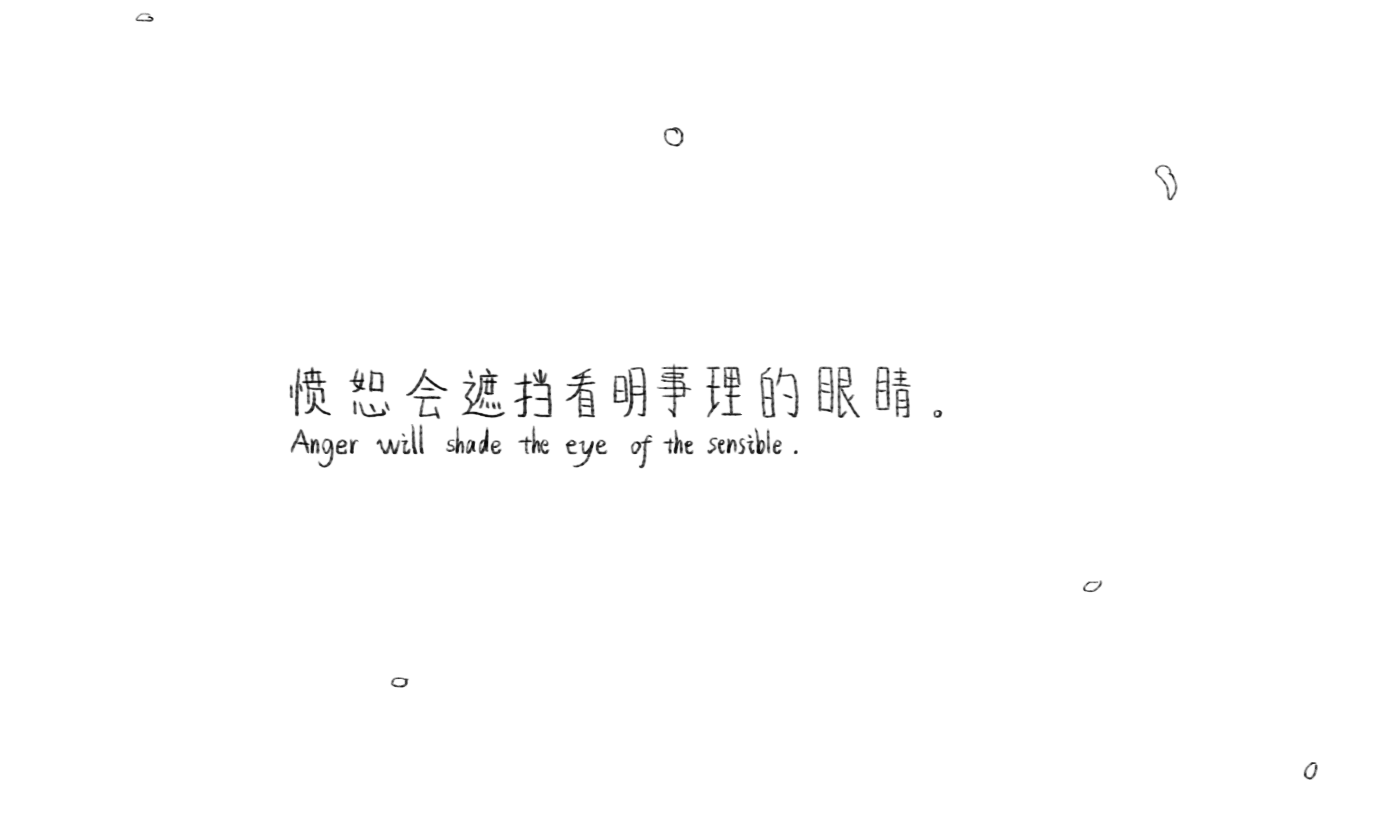民国十九年腊月初三的晚上,太原城柳巷德旺烤鸭子铺的老板孙三儿在自家院里的歪脖子榆树上,一根绳子结果了性命。
那天晌午开始,西北风夹着雪花呼啸而至,擦黑时候,风停了,雪却下得更大,数九寒天,家家都围着屋里的煤炉子熬冬,少有人走动,孙三是晚上趁着家里人都睡着了,自个儿悄悄起来穿了棉袄棉裤,脸上涂了猪油,出门在榆树上搭麻绳子打了结,上了吊。
第二天早上他儿子早起去买油条老豆腐,发现树上挂着一人,登时甩了个踉跄,一边爬起来一边喊媳妇喊妈,孙三儿老伴拉门看到这场景,咚一声倒了下去。儿子孙宝成和儿媳哭成了泪人,惊动了邻居乡亲,大家将老妈子抬进屋里,年长一点的就合力去弄树上冻得硬邦邦的孙三儿,那绳子早就和脖子根冻到了一起,扯不下来,就拿杀猪的刀子割了绳子,将孙三放下来。
众人七嘴八舌问他儿子儿媳是咋回事,没人说的清。有人叫孙宝成别哭了,快去西山请娘舅,雪又下了整整一天一夜。
尸体入了敛停了一宿,次日清晨,没脚深的大雪地里,人们帮着弄了棺材,雇了一班鼓手,吹吹打打将孙三儿抬上了东山。那老妈子服了郎中开的救心丸子,醒了过来,只是不进食,不睁眼,躺在炕上流泪,如此三日。
事过后,除了街坊邻居的议论,并没有引起任何的波澜,本来从古至今,草民们的去世,就如同蝼蚁之灭,兵荒马乱,自顾不暇,谁还会在乎他人生死。孙宝成见老娘醒了,就央媳妇招呼,他去了烤鸭铺,生意照做,片鸭子的那把刀从他爹手上到了他的手上,只是他根本就没学到他爹的那手段。他家的烤鸭子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爹片鸭肉的功夫实在是非寻常的存在,北京的烤鸭不过一百零八刀片完,他爹要片上两百六十刀,不多不少,正如一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字数。没过几天,街坊们的闲言碎语流到他的耳朵里,说这儿子媳妇对老人不好,偷了他老子搬来太原时带的细软,逼死了亲爹。孙宝成觉得很冤,但又不知道爹究竟为啥在大腊月里寻了短见。气不过,就胡乱喝酒,回家打媳妇骂孩子,老娘看不下去了,终于开了口,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孙三儿并非太原人,而是从天津卫搬来的,但也不是纯正的天津人,祖籍在哪没人晓得。孙三儿上吊时六十出头,三十年前,他在天津卫干的营生,可不是卖烤鸭,而是杀人。那营生不是做土匪强盗或屠夫刺客,而是为风雨飘摇的清廷处决死刑犯,他也不是一刀剁头的刽子手,而是施行千百年残害人体的刑法大典中最为人所恐怖的刑罚——凌迟,民间俗称千刀万剐。
在三十年前的清廷光绪帝手上,他是津门名噪一时凌迟刽子手。
那时他三十过头,已经有不少于二十个死刑犯经他的手施凌迟之刑,他的手段,绝非简化的“八刀斩”手段,在他眼里,那些手法根本就不入流,没有师承,纯属野路子,挣得是死人钱,而他却保持着传统的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凌迟大法,干的漂亮,声名显赫。每次割完最后一刀眼睑肉,人们便喝彩山呼,药铺子的伙计会从他手上用白瓷盘子接了那两块肉,装进紫檀木盒子里,飞也似的跑了去,后面跟着一串人去药店抢买,有更多人跟在后头看热闹,他们甚至守在药铺子门口,一定要等得有人买了去,再撵着买那东西的人一直到家。据说放在火炉子边上烘干了,与十几味中药配伍,弄成丸子,是治眼疾的神药,千金难买。
每次行刑前,都要按照行规祭天地鬼神祖师爷,每次行刑,更像是一个唱梆子戏的,年复一年吊嗓子压腿,直到有一天登台唱大戏,只能唱好不能唱坏,他的刀数要是没到点子上,差了哪怕一刀,饭碗子就毁了,所以得练,怎么个练法?自然是练鸡鸭鹅猪狗,但是畜生有个特点,活物都长毛,只有人才是浑身赤条条,怎么办,办法有的是,他有套秘术,那鸭子褪了毛照样还想跑,光溜溜的活鸭子被割到最后一刀才断气,刀法就差不到哪儿去了。所以每次行刑,都像是一个戏子登台,台下全是观众,只要是被判了凌迟的,早半年就要通知刽子手准备,消息一放出去,人们翘首以待,说书的早早就编了段子传唱,那些平时听戏读《玉蒲团》的也都放下手头的小爱好,走哪儿都在谈论那囚犯的故事,好不容易等到行刑日,人们倾巢而出,大街小巷,奔走相告,行刑时,小土台子要以柱子为中心,官兵合围,人们都想挤的近一点,里三层外三层,树上、屋顶上、墙头上全部爬满了人,附近的酒楼把临窗的位置卖出了比平时高三倍的价钱,依旧供不应求,雅士们端坐桌前淡然饮茶,临街观看,别有滋味。刽子手一出来,人们纷纷拍手叫好,如同欢送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军,犯人一出来,人群立刻发出海啸般的呼声,叫喊些啥,谁都弄不清,只听到一片“呜啊”声,这犯人承载了他们人生中最重要体验的所有幻想,终于来了,究竟是不是说书人嘴里那图谋刺杀朝廷大员的逆贼,还是奸了官员妻小的淫贼,或者是抢了钱还满门灭口的强盗,都不重要,管他是什么罪,主要是看他会在多少刀上死掉,砸了刀客的饭碗,还要听他嘴里骂的腔调,那些个话语,平时都不敢骂,死刑犯骂出来就等于自己骂出来,听着过瘾、痛快。还有更让人期待的是死刑犯骂上,越骂越难听,每一骂人们都哄堂大笑,直到刽子手开始割舌头,从骂变成了混杂不清的吼,再从吼变成嗓子眼的嘶叫,最后变成喷血沫子。这个过程连官兵都不看,人们能躲的也都躲开些,只有那好事的,围拢来,巴巴地看着,脖子后面流着冷汗,不停地咽着口水。
革命党闹起来之后,一些酷刑随着清廷迫不得已的变法给废除了,包括这凌迟大刑,孙三儿知道会有这一天,也做好了离开天津去别的地方做买卖的打算,但是清廷的大狱里,还有几个罪大恶极已经判了凌迟的犯人等候处决,刑罚已废,但犯人之罪过,不施以凌迟之刑又不足以平民愤,于是孙三儿接到了最后一个营生。
其时天津卫已经成了朝廷、革命党、各路豪杰以及洋人运筹业务之所在地,不甚太平,人们奔走往来,虽照例口口相传等待着这场极刑,但每个人心头都不似以往那般淡定从容,都听着各种传言,似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比起自身的安全来,别人的命毫不值钱,恰恰这次凌迟处死之人,却是曾图谋袭击在驻扎在天津小站手握重兵的朝廷大员袁世凯的主谋,虽然事件被压制下来,不见于报端,且这个人以枪杀雇主一家五口且凌辱雇主妻女尸体的罪名施以凌迟,但私下地人们都在传说这人被处决的真实罪责,自然,那惨死的一家五口,说不准是谁干的。
行刑的日子终于到来,人们怀着各种小不安,嚼着各种小舌根,照例来看热闹。孙三儿准备了两天两宿,这次行刑对于他而言,将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从今往后,就再也没有凌迟这个死法和他这样的刽子手了,也再也没有这样的行当了,他心情沉重,相较于惋惜丢了饭碗,他更怕做不好辱没了祖师爷的名声,行刑前夜,他端端地在屋里割死了两只鸭子,睡不着,半夜三更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心里慌的紧。
刑场上,青天白日,人群少了以往的狂躁,显得冷清而凝重,越是这样,孙三儿的底气就越不足,当他拿着薄如纸张的并刀,准备下手时,兀地看到那清瘦到皮包骨头的犯人嘴角泛起的冷笑,然后就听到犯人低声地说了一句,你割不死我的。声音很小,小到只有孙三儿一人听到,他咬咬牙,从胸部开始下刀子,人们屏住呼吸,想听到那标志性的骂声,可是,犯人没有任何声音发出来,孙三儿心里莫名慌张,但他屏住呼吸,又轻轻地挫了一刀下去,将那人皮提起来给众人看。几十刀下去了,犯人两眼开始流血出来没吭一声,突然他哇的叫了一声,嘴巴里掉出来一些血肉模糊的东西,不好,莫非他要咬舌自尽?孙三儿用刀把拨拉了一下地上的东西,发现是些鲜血淋漓的牙齿,原来这犯人咬碎了牙齿。他的不吭声不但挑战了孙三儿的技艺,更激怒了围观的群众,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刚硬之人,他们所期待的一切都没有出现,这个人的存在,侮辱了他们的耐心,斩断了他们的谈资,终止了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鲜血弥漫的经验,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有人在叫骂,骂孙三儿,也骂那犯人,骂声变成起哄,起哄变成了混乱,人们开始推搡,周围的士兵挡不住,终于,人们冲进了刑场,推开了孙三儿,把他踩在了脚下,扑上去撕扯那犯人,甚至有人直接去咬。等官兵维持好了秩序,人们悄悄用衣襟和鞋底擦了嘴巴和手上的人血,四下离去,孙三儿的刀不见了,衣服被扯破了,他跪在那里,仿佛遭受凌迟之刑的人是自己。
这场事件没有任何人记载,也没有任何报纸报道,只散见于一些评书段子里,而后来,说评书的人也稀少了,说的也都不是这些旧朝奇闻,自然,也就不知晓这事了。后三十年,孙三儿一直在太原的柳巷卖烤鸭,鸭肉被他片的如同蜡纸,追捧者甚众,人们都惊叹他那秘而不宣的手艺究竟是从哪儿学来的,连同他的儿子都不知道。他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他以往的事,知道他来太原前做的那档子营生的人,只有他老伴。
三十多年来他经常痛心窝子,吃什么药都不好使,老伴着急了三十多年,直到他计划上吊前的半个月,才跟老伴说了他的病根子,说了他之前的那些往事,老伴呕吐了半宿不敢入睡,孙老三告诉老伴,其时那场行刑后,作为一个刽子手的孙三儿已经死了,他隐姓埋名三十年,也足足想了三十年,他想那天要是行刑成功,他或许名垂青史,即便青史留不下名声,江湖野史里也应该有他的唱段,甚至,这门绝杀的手艺在他手上终了,也没算给千年的祖师爷丢脸。
更让他想不明白的,是那遭受极刑铁骨铮铮的死刑犯,是什么样的神明罩着他,非但没有哀嚎,没有怒骂,甚至连痛苦都未曾表现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如果没死,这样的人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他越想越忘不了那冷笑、那呢喃。还有一件折磨他三十年的事,他觉得自己至死都不会想明白,那天的那些看客们,究竟干了一件什么事?
就在上吊前三天,他围着火炉烤鸭子,果木在火力噼里啪啦燃烧炸裂的声音,似山呼海啸,似人声鼎沸,他忽地开了窍,他想到了那年围观的人,想到了以往他行刑时围观的人,其实,他不过是替那些人动刀子,他们每个人都有心来上一刀,可惜不得上手,他不是什么技艺高超的刽子手,他只是代庖的小丑,真正的凌迟之刑,不是一人所为,而是众人动手,没有了众人,凌迟就毫无意义,当他这个替众人施刑的刽子手无法达成众人的要求,他们一定会自己上手,法不责众,非但不责众人之肉体,亦不责众人之心。
孙三儿那晚翻来覆去睡不着,到二更时分,突然觉一口气松了下来,仿佛多年的顽疾痊愈般心情舒畅起来,他腾地从炕上立起来,点着了煤油灯,从箱子里翻了一把香,点上,在老伴诧异的注视下,跪在地上朝着东北方向咚咚地磕头,嘴里念叨着:“祖师爷呀,我可算没丢你的脸呐,咱们凌迟的这个手段,没有丢,没有绝,也不会断啊,往后哪朝哪代,只要有众人在围观跟人命有关的事,那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刽子手啊,一人一刀,刀刀都是血呐,那刀也不是刀,那是唾沫星子,是汉字块子,是说书的快板儿和唱曲的弦,是好奇的眼神,嘴里的嘀咕,心口头的欲望,是不能说的那种痛快啊……”
孙老三说着,闷声笑了起来,老伴惊恐地问他是不是中邪了?他脱了棉袄翻身上炕,吹了灯,跟老伴说,我给你说个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