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世界·公益阅读】伦理、正义以及其他——深圳基因剪辑婴儿事件的之前与之后

以“读”攻毒——科幻世界相伴,助力全民战“疫”
伦理、正义以及其他
——深圳基因剪辑婴儿事件的之前与之后
作者 / 索何夫
对于任何科幻作家而言,最为“科幻”的事,莫过于得知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以某种方式变成无可否认的现实。
2018年11月23日,“2018中国科幻大会”在深圳召开,而在三天后的11月26日,当笔者尚在海滨旅馆中参加笔会时,一条惊人的消息突然在网上传开:就在这一天,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他所参与修饰胚胎的两名经过基因剪辑的女婴“娜娜”和“露露”(巧的是,在笔者去年发表的描述未来基因混乱可怕景象的小说《直至沧海》中,女主角和女配角正好就叫娜娜和露露),已经在深圳的一家医院中诞生!按照此公的说法,这对女婴可以“天生免疫艾滋病”。而实验的详细数据,将会在次日于香港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公布。

不出意料,消息传出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各个主要互联网社区几乎都立即有了反应——最初的几篇相关新闻报道,无不是以一贯的报喜口吻报道此事,并宣布这是“重大科技突破”“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不少人随之开始欢呼雀跃,迫不及待地表达他们因为这一事件而被激起的自豪之情。
无独有偶,当时正在深圳参加笔会的圈内同仁中,恰巧也有包括本届银河奖最佳中篇小说奖得主谷第在内的几位生命科学专业人士。与网络上一边倒的狂喜气氛相反,在确认这并不是一条假新闻,也不是中国互联网见惯不怪的“标题党”文章或者营销号的夸大其词之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而且甚至不是一件应该发生的事。
此后的短短几十个小时内,事件的走向表明,专业人士们的猜测果然没错。
经过之后几天里各路科普人士的轮番轰炸,大多数认真关注此事的人显然都已经对这次“免疫艾滋病婴儿”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有了大致的了解。在网络上大轰大嗡的所谓“创造超人”,当然不过是无知者的无稽之谈。粗糙的基因剪辑的结果,不但无法确保这两名女婴能够免疫艾滋病,甚至还极有可能已经在她们的每一个细胞核内留下了终生无法摆脱的基因缺陷!而整个实验既没有什么技术突破可言(稍微像样点儿的实验室在几年前就完全可以这么干了,只不过没人愿意),也没有丝毫创新,更算不上成功,而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技术闹剧兼悲剧——对于这一点,真正的专业人士在听到新闻之后基本上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至少不是唯一的关键点。
毋庸置疑,这场轻率而无意义甚至充满了非法嫌疑的实验,是失败的。但失败本身并不值得谴责——自从实证主义原则被提出并采纳后,科研活动就一直是实验,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断试错的历史(相反,如果有谁能提前几年就在科研计划中详细给出取得成果的时间,甚至精确到月,那么他要么是个骗子,要么是个穿越者,要么就是个不得不撒谎的人)。严格来说,一次正儿八经的实验失败与成功同样有价值。如果这仅仅是一次“失败的实验”,那么,它并不会受到任何批评,甚至还值得尊重。但事实却是,几乎全球科学界都在第一时间怒发冲冠,开始向这次所谓的“科学实验”开火。
这是为什么?
从网民的草根舆论的反应来看,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至少并不真的知道。在怒斥这次实验的人中,有不少人是宗教信徒,出于其特定信仰而无法接受基因编辑。而另一些人则大幅度和之前的反转基因运动支持者重合:对他们而言,“基因剪辑”和“转基因”之间的差别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反正都和“基因”二字沾边),而只要和“基因”沾上了边,那么对其严加反对,就是应有之义。因此,正如空泛虚假的赞美并无意义一样,这样的反对不但无益,甚至有害——毕竟,就在几天之前,同一群人还以他们天才的想象力,将主要研究杂交水稻、根本不是基因工程专业人士的袁隆平,给列入了“转基因三丑”的名单之中。至于科学界和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焦点——伦理和程序正义——则鲜少被人提到。

有人说,在中国这个充满反转基因宣传的国度里,居然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例基因编辑人类,这实在是件很科幻的事情。但事实上,只要仔细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事实其实是相当符合逻辑的:无论贺建奎及其团队铤而走险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目前来看,是为了经济利益而非人类福祉的可能性更大),他们的行为都显然违背了程序正义和伦理,也是对科学精神的亵渎。而不幸的是,那些反对此事的人,同样也对程序正义、伦理与科学精神毫不在意——反转基因宣传的重点恰恰是“既然它可能有害,我们就要反对它”,而无视必要的转基因技术(比如番木瓜的栽培,如果没有转入抗病毒基因,绝大多数番木瓜早已因为木瓜环斑病毒而灭绝,我们根本别想吃到)在经过法定程序审核,并证明了其在科学技术上的合理性之后的实用价值。这种盲目的反对随时可能转化为盲目的支持,从这一角度而言,很多咒骂贺建奎的人正是催生这种行为的社会土壤。
何谓伦理?因为20世纪政治史和解构主义的共同影响,“伦理”这个词经常在人们的下意识中与“三纲五常”“君臣父子”这类“封建糟粕”,甚至“宗教”挂上钩。贺建奎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便有支持他的所谓“科学家”撰文声称,经过基因编辑的胚胎不允许发育超过十四天是因为“科学向宗教的妥协”——当然,反驳者随即澄清,决定何时停止胚胎发育的判断标准,事实上是胚胎的神经系统开始发育的时间。另一些机械唯物主义者则索性把贺建奎与布鲁诺等科学先驱并列,声称当前的伦理委员会就是中世纪的教廷,是在捍卫“封建伦理”和“神学”。这种言论纵然荒谬可笑,但也确实颇能说明问题。
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作为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伦理(以及道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和“封建落后”挂不上钩。相反,它是生产力基础和人类社会经济基础的映射,本身便具有极为重要的实用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近亲通婚——尤其是直系血亲通婚——的严格禁止。这么做的目的,并非过去的道学先生们所吹嘘的那些形而上的臆想,而是因为人类通过实践逐渐认识到,近亲通婚有更大机会产生畸形后代,不利于人类基因库的持续改良。同理,现在的伦理之所以不允许基因剪辑人类的诞生,并不是因为某些人胡言乱语的“西方人不敢僭越上帝”——且不说现代欧洲,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在几年前就超过了总人口的50%,而罗马教皇也早已无权干涉任意一所研究机构中任意一名科研人员的任何一个课题,就算是基因工程和遗传学本身,也是由西方人最早创立的——而是因为技术本身的不成熟,使得这么做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远远超出了可能的收益。毕竟,生命科学界早有共识:相较于可能的收益,让难以预料的基因缺陷流入人类基因库的风险要大得多。
当然,某些机械唯物主义者对此并不在乎,这些人的心态,在新闻刚流出时的欢呼雀跃,以及事件反转后中文网络上突然冒出的一大片“安乐死”“人道毁灭”呼声中显露无遗——在他们看来,就算是活生生的、独立自主的自然人,本质上也不过是可有可无的“零件”,与实验室里的植物种子或者小白鼠胚胎一样,出了问题大不了销毁了事。“为了发展,牺牲是必要的”这类言论是他们的口头禅。然而,正如马克思时代的哲学家就已经普遍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和唯一目的,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人类这一概念绝非一个虚无缥缈、大而无当的幻觉,而是实打实的、由一切自然人形成的共同体。换言之,对于个人的生命权和其他基本人权的漠视,是无法以“发展和进步”的名义加以开脱的,因为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最终目的的背反。归根结底,人类伦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实践中规范人的行为,而被许多人视为“陈规陋习”“条条框框”的程序正义,其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也正是为了确保我们的行为不至于在一系列的逻辑滑坡中,最终走向最初目的的反面。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对伦理的不屑一顾一样,许多持机械唯物主义和机械发展观的人,同样不喜欢程序正义——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够避免这些“浪费时间”的“走过场”,无疑“发展效率”会提高很多。当然,与某些历史玄学的兜售者所宣称的不同,这种危险的思维模式并非中国人独有,更不是中国人的某种“与生俱来的劣根性”(毕竟,“劣根性”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后发国家中——尤其是这些国家新生的市民阶级中——的心态。在20世纪,随着第三世界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认识,这些国家往往很容易产生急躁乃至激进的“弯道超车”和“一切为发展让路”的心态,期望能够尽快追平差距,其他的一切都被放在次要地位。而在科研活动中,科研的参与者们也往往会有意无意地附和甚至利用这样的心态。在本次事件中,众多网民、网络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因为“世界首次”这个字眼欢欣鼓舞,无视其余,乃至完全不在乎在新闻公布不久后便被披露出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伦理审查的形同虚设,整个实验低下的透明度,以及其他诸多明显与国际惯例和法律法规抵触的细节,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源自这样的心态。

不过,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尽管这次问题众多的实验本身显然是失败的,并且在事实上为人类这个物种的基因池中增添了一分消极的不确定因素,甚至还严重侵犯了两名刚刚出生的女婴的基本人权,但事实上,这次实验的负面效应,很可能还不止于此!
与直接的失败相比,实验本身可能造成的负面舆论影响,将是长远而恶劣的,甚至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数十年中持续发酵,成为生命科学发展前途中的巨大绊脚石!
也许有人会说:只要我们好好摆事实、讲道理,把整件事说个清楚,不就没问题了吗?
然而很不幸,整件事显然不会那么简单:在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大部分人都还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第三世界近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时代,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智人这个物种中的大多数成员,并不具备与现代生产力水平相对应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大多数人接收与处理信息的方式,仍然停留在前现代社会,而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和他们在农业社会的祖先别无二致。
在这种前提下,大多数科普宣传的实际成效,是值得怀疑的。在本次事件中出现的大量阴谋论,尤其是那些老生常谈式的反转基因言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别忘了,在过去,科普工作者和科学家们已经与反转基因运动来来回回“过招”了二十多年,但宣传成效却一直不彰——对于一个并不真的了解人类消化道工作方式,以及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过程,信奉萨满教式的“吃啥补啥”原则的人而言,无论再怎么告诉他“转基因食物不会导致你的基因被改变”,都是白费力气,因为对方并不具备理解这一事实所必需的知识基础。
更糟糕的是,这种情况并不完全基于单纯的学历水平——在投身于反转基因(在欧洲和美国,还有相似的反疫苗运动)的人群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者的身影。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单纯的知识储备其实意义不大,尤其是在信息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单纯的知识很容易就能搜索查阅到的情况下。相反,大多数人所欠缺的科学精神和逻辑能力,是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从未教给他们的,这类“现代原始人”的普遍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是科学的正常发展和良性运用的重大潜在障碍。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次事件归根结底不过是个人行为而已,而且贺建奎本人也已经宣称要“承担全部责任”,为什么要担心整个生命科学发展的前景受到影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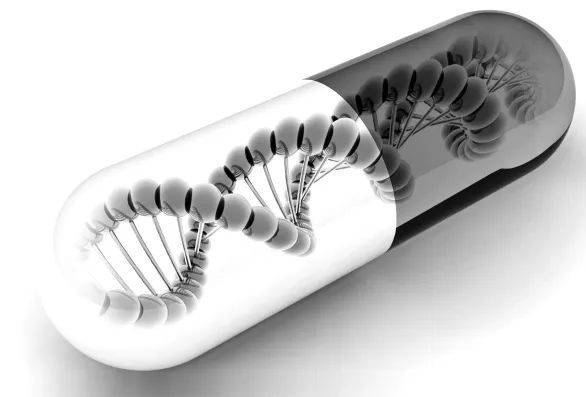
事实上,如果对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稍有了解,我们就不难明白,指望作为一个整体的公众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有多困难。当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说到底也仅仅是部分苏联技术人员和核电站官僚在安全方面疏忽大意,在一系列不幸的巧合之下酿成的悲剧,与整个核电与核能领域并没有多少关系。然而很不幸,以此为契机蔓延全球并持续了三十余年的反核运动,可不在乎这一点:在全世界谈“核”色变的人群,绝不会多花哪怕一秒钟时间,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具体责任属于谁搞清楚,他们不会也不愿将单独一座核电站与整个核电行业分开,甚至还普遍将核电与一切和“核”沾边的东西混为一谈。许多反核电人士坚信,核电站反应堆与核导弹的战斗部,根本是一回事,正如反转基因支持者们不断重复着“能毒得死虫,就能毒死人!”这句看似正确的陈词滥调,而从来不在乎何谓“脱离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一样。
除了之前已经分析过的“现代原始人”这一点之外,导致这种状况的还有另一个原因——传播学原理中的“选择性接收”。
作为一种心理防御手段,相当多的人对于自己不愿意听到的消息,都会下意识地采取这样的策略:充耳不闻,只捡愿意听的听。在信息的传播之中,这种状况又会进一步地表现为“削尖”与“磨平”:担任信息“二传手”“三传手”的人,会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认为关键的部分(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关键部分),而忽略那些被认为次要的部分。最终,在几轮传播之后,信息往往已经彻底走样,被传播者塑造成了他们想要的模样。所谓“转基因粮食吃了断子绝孙”和“碱性体质延年益寿、容易生男孩”的传言,事实上都来自这一传播模式。
可以想见,本次人类基因编辑事件本身,已经槽点无数、问题丛生,对于遍布全世界的千百万本就对生命科学充满疑虑,愿意以最大的恶意对其进行猜测的人而言,它无疑是一颗货真价实的信息核弹!纵然南方科技大学与全球生命科学从业者已经在第一时间公开发表声明,与贺建奎撇清关系,但任何略微熟悉传播学基本常识的人都不难估计出,这些事实几乎必然会在信息的反复传播中被遗忘、忽视,或者歪曲为“伪善”与“官样文章”。而它真实的一面,则会在兴致勃勃的阴谋论者与忧心忡忡的传播者手中,被塑造得更加张牙舞爪、面目狰狞,最终成为一个横亘在全世界生命科学界头顶的巨大魔影。
总之,我们目前必须承认一个不幸的事实:因为诸多原因,贺建奎事件事实上木已成舟,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然无可挽回,而且甚至可能会持续数代人之久。我们所能够做的,则只有分析它的成因,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止损——哪怕微不足道,但至少也比没有好些。
本文刊登于《科幻世界》2019年1月刊


【为满足广大幻迷战“疫”期间的阅读需求,科幻世界微信公众号(scifiworld)上线“公益阅读”板块,至2月底,推送大量免费的优质科幻小说资源,让科幻陪伴我们共度时间也共渡时艰,做精神上无忧无虑的“快乐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