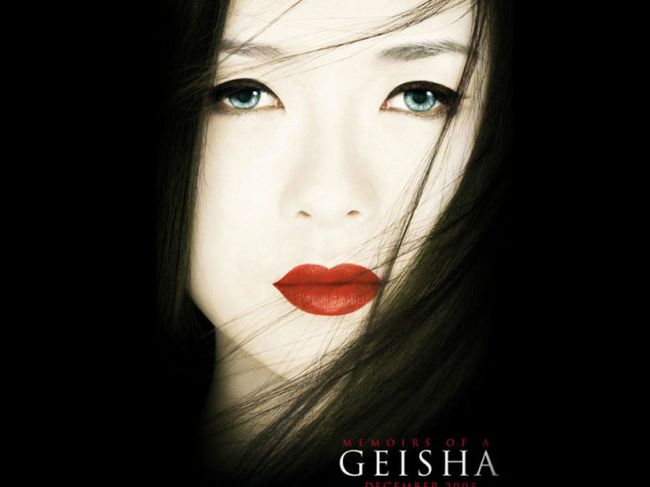金秋九月,到处一派丰收的景象。在南部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浓郁着丰收喜庆的色彩。今年特别风调雨顺,稻谷堆满了谷仓,池塘的鱼也悠闲地吐着泡泡,冒出头来,像是在等待着农民伸手来掂量掂量自己的重量。田野里随处可见那高高垒起的稻杆,像是一个个守护田地的守护者,又像一群群在田野里玩耍的小巨人。
而这个村子里大多数人姓张,故名张村。为了庆祝丰收及感激各路菩萨的保佑,张村的人便决定请城内有名的“青云戏班”来村里唱十天大戏。戏台设在张家祠堂。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异常高兴,黝黑的脸上都浮出了一丝微笑。
在庆祝丰收的同时,村东面的张家和王家的脸上更是多了一抹色彩。看着自己大肚子的婆娘,幻想着不久就有一个咿咿呀呀的孩子降临人世间,内心就特别喜悦。
说起这两户人家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待人都较温和,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妻子,一个温和,一个泼辣,温和的喜静,泼辣的好动。温和的叫刘云,泼辣的叫李香清,外号李辣椒。
戏台搭起来了,足足两米来高,铺上红红的地毯,台上红的、绿的脸,一会儿是煽情的《孟姜女哭长城》,一会儿是豪情万丈、保家护国的《岳母刺字》,一会儿又是悲情万丈、六月飞雪的《窦娥冤》。锣鼓喧天,车水马龙,好不热闹。那锣鼓的喧嚣声,观众的喝彩声在村子里回荡。
刘云和李香清坐在床上,一个在纳鞋底,一个在嗑瓜子,听着门外邻居三三五五成群结队地去看戏,听着他们绘声绘色的话语,李辣椒的心里像猫抓的一样,痒极了。浑身不自在。
她那烦躁的深情,她的丈夫王天给她递来一杯水,对她说道:“香清,你忍一忍,孩子都九个月了,快临盆了。就不要随便走。”“忍忍什么忍啊!怀孩子那么累,还不能让我出去放松一下,你是关牢人么?”李辣椒反驳道。说完迈起右脚就要走。看着李辣椒迈出门槛的身影,王天急忙道:“你别去看大戏,村长说祠堂不怎么干净!”“知道了,我去张婶她家走走,憋死了!”李辣椒回了他一句。像张婶他们家走去。
王天看着李辣椒往张婶他们家走去,便没有阻拦,只盼着她早点回来。
谁知李辣椒一瞧见自己丈夫走进了家门,便一溜烟地转变方向,挺着大肚子往祠堂的方向走去。
当李辣椒到了戏台时,却发现祠堂门前是人山人海,戏台上红红绿绿的面孔,咿咿呀呀地唱着什么,台下的板凳上黑压压地全坐满了人。李辣椒在最后,只看得清戏台上的人影,至于唱的是什么,听不清楚。
“这该怎么办呢?自己好不容易溜出来,只看到个身影可不行。”李辣椒心想。这是她尖锐的眼睛瞧见了中排的凳子上正坐着自己的一个远方亲戚,凳子的另一头还没有坐人,显然是为别人留的。李辣椒艰难地挤进人群,大声嚷着“让一下,让一让!”人群一阵骚动,都反过头来看李辣椒。
看到李辣椒那波澜起伏的肚子,村里的快嘴张便调侃道:“李香清,你怎么来了?哦!不会挺着大肚子来相亲吧?”李辣椒别了她一眼。“相亲,我相你祖宗八代的亲,最你这张臭嘴,活该守活寡。”李辣椒的话正中快嘴张的痛处,去年她的丈夫被房梁砸中,瘫痪在家。婆婆就一直怪她,说是她的嘴巴没有积德。快嘴张听了低下头来抹眼泪,慢慢地从人群中挤出自己单薄的身影。
几个熟悉的妇女看着快嘴张离开的身影,都叹了一口气。眼神中有点对李辣椒不满。李辣椒看着她们的眼神脸上慢慢红了起来,自己本不是有意的,但是是快嘴张每次抓着自己的名字来挖苦自己,不反驳不太吃亏了吗?这时的李辣椒已无心看大戏了,满脑子都是快嘴张那幽怨的眼。便挤出人群,朝家踱去。“不为自己积德,也要为孩子积德,李香清,你记住了没有?”李辣椒喃喃道。
由于看戏的缘故,走在路上的人特别少。走着走着,她忽的觉得后面有人在跟着她,她走一步,那个人也走一步。她敏锐的直觉告诉她,一定有个人在她的不远处。她想是不是快嘴张心怀恨意,跟着她想报复她呢?她赶紧快速地回头一看,却发现什么也没有。这时吹来一股凉飕飕的风,李辣椒打了一个寒战,加快回家的脚步。
回到家,李辣椒径直地躺在床上什么也没说,就连丈夫王天的问候也只是嗯了一声。不知怎的,她感觉自己的心口上有什么堵着似的,特别难受。王天也没察觉什么,以为李辣椒是累了。
当他走出门去时,隔壁的张龙笑着道:“王天,你们家是不是来了客人啊?你这么急匆匆的是不是去买菜啊?”王天一头雾水,不解地道:“没有啊!只有我媳妇,没有客人。你是不是看花眼了呀!”张龙摇摇头道:“不可能啊!我看到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左手拿着油纸伞,右手拿着绣花袋,紧随着香清进去的啊!”看着张龙认真的表情,王天摸摸张龙的头笑着道:“天啊!你不会是看大戏看多了吧!发烧了!”说完便摇头晃脑地去厨房给李辣椒做饭。
张龙也摇了摇头,“按理说不会错的啊!是来了个姑娘。”他嘟囔道。一边说一边在磨刀石上磨着菜刀,准备给妻子杀鸡补身体,产婆说刘云就这几天生产了,他得时刻准备着。
就在他磨刀的时候,他竟又看见了那个姑娘,她仍旧是穿着蓝色的青布衣裤,左手举着白色的油纸伞,右手提着红色的绣花袋。看上去不像是他们这个村子的人。那个女孩从李辣椒的家门口出来,鬼鬼祟祟地在门上画了一个月牙的记号,便匆匆离去。看到她鬼鬼祟祟的样子,张龙觉得很不对劲,很有可能是小偷。那绣花袋里很可能是她偷王天他们家的东西,王天家原本就不怎么宽裕,母亲刚过世,加上妻子又要生小孩,被她偷了他家可怎么活啊!可不能让他家雪上添霜。
俗话说:“捉奸要在床,捉贼要拿赃。”张龙便偷偷地跟在那个姑娘的后面,一眨眼就没有看见了她的踪影。正当张龙要离开时,只见她慢慢地从一个稻杆堆旁走出来,张龙看见她有点不对劲,是哪里呢?哦!他定睛一看,原来那姑娘右手的绣花袋不见了。“果然是小偷,在藏赃。我可不能让她得逞。”张龙想道。
等那姑娘走远,张龙便飞快地走到那堆稻杆旁,左看看右看看,却没有找到那个精美的绣花袋。会在哪呢?张龙便把手伸进稻杆堆里,在里面摸索。刚开始,什么都没有摸到,张龙不甘心,把头都埋进稻杆堆里,手伸得更长了。忽的他的手触碰到了一块柔软的东西,他欣喜若狂地一把抓出来,一看竟然是一个绣花袋,袋上还有精致的鸳鸯戏水图,一针一线都极为精细。
张龙没来得及欣赏袋上美丽的图案,迫不及待的打开绣花袋,忽的,银光四闪,无数大大小小、锋锐的绣花针呈现在他的眼前,张龙十分惊愕,看着这些绣花针,想起王天的回答,脑门会的冒出了冷汗。她不是小偷,莫不是老人口中常说的脏东西。张龙知道自己是遇到了鬼,看着那些锋锐的绣花针,他也明白了这只鬼的企图。她是让妇人难产的女鬼,是剥夺女人做母亲权利的恶魔。
张龙知道女鬼盯上的是王天的妻子,一想到那么憨厚、老实的王天会有丧妻之痛,他的心里就异常难受。他的脑海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毁掉那些绣花针,他颤抖的手拿出了火柴,“扑哧”一声,火柴划着了,整堆稻杆都燃烧了起来,火苗像一只凶猛的蛇迅速地把那精美的绣花袋吞食掉。看着那燃烧的大火,张龙真希望那恶魔可以随着绣花袋彻底消失。
慢慢地稻杆堆烧得只剩下一根中间的木棍,张龙也放心地转过身走了。在他转身的刹那,低下的双眸没有瞧见不远处稻杆堆后的女子满眼的怨恨。
当晚张龙和王天的妻子两人同时胎动,两个人都疼得呼天叫地,张龙和王天都在各自的房门前踱步,焦急不已。张龙本想告知王天关于绣花袋的事,但看着王天焦急的神情,便没有说出口。他只愿王天的妻子稳稳当当的,自己的妻子也平平安安的。
不久一声“哇”响,王天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产婆忙抱来报喜,王天抱着孩子高兴地向李辣椒奔去。看着这一幕,张龙也很高兴,他心底想那把火烧出了平安。
就在这时,妻子在房里惨叫,“呜呜”地疼得特别厉害。产婆忙出来问道:“主人家,你是保大还是保小啊?胎位不正,夫人难产啊!”
张龙一下子蒙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妻子会难产,他联想到了那带绣花针的姑娘,但那把大火已经烧了的啊!不可能的。于是他便道:“无论如何,保大人。”产婆进去了,那快速的身影带走了一阵凉风。
张龙瘫坐在地上,泪流不止。房内又断断续续地传来了呼叫声,一想起自己的妻子在曾经是爱巢的床上经受着非人的折磨,他的心像被针刺了的一般,很痛。
“刘云,刘云,你醒醒啊!”产婆传出了如杀猪般的嘶叫声。张龙知道情况不对劲,便推门而入,映入他眼中的是哭哭啼啼的产婆和浑身是血的妻子,还有那高耸的肚子。不,那肚子上还有一张狰狞的脸,她坐在刘云的肚子上,拿着那锋锐的冒着寒光的绣花针,胡乱地往她肚子上刺去。她那青布衣裤上沾满了血都变成了暗红色。刘云向木偶一样任她摆布,那成形的婴儿也已经被刺破,张大嘴,下身血肉模糊。张龙看着那狰狞的女子,她不断挥动着绣花针,还仰起脸对张龙笑。
张龙发疯似的冲过去,但却无法靠近她。张龙瘫坐在地,发疯似的抓着自己的头发,怒视着那张狰狞的脸问:“我家一直行善,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下场?”听到张龙的话语,那女鬼竟犹豫了一下,走下床来道:“世间万物皆有因果,人有人道,鬼有鬼道。我找的并不是你妻子,但你执意识破我,并烧毁我的绣花针,让我无法投胎转世。没办法,我只有另找一个替身。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
“好,即便是我自作自受,但你为何要害我的邻居李香清?她可是和你无冤无仇啊!”张龙问道。
“无冤无仇!”女鬼咬牙切齿道,那眼中闪烁的都是满满的凶光。
她用血红的双眼注视着张龙,挥袖一闪,便出现一个画面。那个画面里也是一个女孩在艰难生产,那肚子上也坐着一个有着狰狞面孔的女人,挥动着绣花针向女孩的肚子上刺去,张龙发现这个场景是那么熟悉,但那女孩死时着青布衣裤,那张腮边流泪的脸竟是眼前的女鬼。而那张狰狞的脸竟是李辣椒。
“你明白了么?一切皆有因果,前世她杀我,今生我来还。但你却不遵守人道与鬼道,让我只能错杀人。”女鬼悠悠的声音响起在空中。
张龙看着刘云那苍白,不愿闭眼的脸,他忽的像疯了一样,在冲刺着血腥味的房里跑着小圈,奶声奶气地道:“人道,鬼道……嘻嘻!”据说张村的人听到那“嘻嘻”声,都会毛骨悚然,因为那是刘云肚子里的小孩发出来的,“嘻嘻、嘻嘻”。你听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