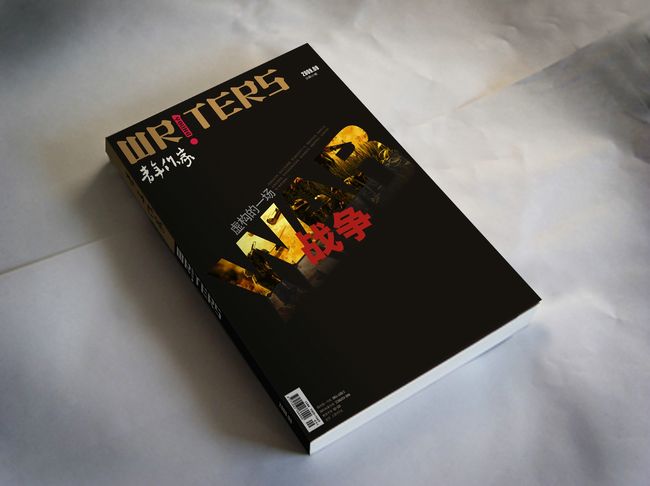我有个同学参加过七九年的战争,在越南他们都叫他钢盔。
他到达前线当天,有个狙击手被越南人干了,刚死的那家伙外号钢盔,向来独行独往,整个连队竟没人熟悉他事迹生平,但死去的战友总需要纪念,于是新来者被冠以钢盔这个绰号。此后一星期,我的同学为前一个钢盔写悼亡信,以便邮寄给他的家人,他很奇怪为什么由他执笔,他们回答说,因为你现在叫钢盔,没人比你更合适了。他在信中写道,你们的儿子是最优秀的战士,值得生死付托的同志,他用大段排比句式渲染情感,结果自己都被打动了,写信过程中泣不成声,他毫不做作的表白,愿做他们的儿子,等战争结束,代他们死去的儿子行孝。他想到在结尾处引用数据,但遇到了难题,因为不知前一个钢盔究竟消灭过多少越南人,他询问那些老兵,老兵们满含热泪地告诉他,钢盔是多好的人,从没杀过人,那些该遭天谴的越南佬。他随便填上几个数字,把信邮寄出去,完成对上一个钢盔的缅怀后,顿悟到现在自己才是钢盔。
钢盔等回信,一直到战争结束,也没丝毫回音。等信的一年,他多数时间都浪费在某个坑洞,坑洞编号为412,后来报纸把那些坑洞统称为猫耳洞,狭小潮湿的洞穴,给钢盔留下不少后遗症,双腿关节患有风湿,风湿病随着时间推移日益严重,十五年后,导致被单位调整下岗,战争还给他添加了脊柱劳损,耳硬化症等副产品,同时也治疗了原先的顽疾,譬如打呼噜,精力过旺,这些得失都是后话,对战争进程无关痛痒。真正影响到战争是皮肤病,皮肤病在前线非常普遍,几乎全部士兵都是患者,因此没人觉得是个问题,甚至可以当作不错的消遣。钢盔写完信后的第一周,裆下生出了几颗红点,手感象摸着乒乓球拍胶皮,醒来后阴部瘙痒,他还是处男,怕别人把挠痒动作误会成手淫,只能到岩石尖角蹭几下,不留心私处就被碰伤,钢盔疼得嗷嗷直叫。如果天气放晴,露天晒太阳是不错的选择,阳光是针缓和剂,能缓和过度抓挠的痛楚,钢盔知道该去何处,老兵给他介绍过阳台,战场总会有几处禁区,交战双方都竭力避免冒犯的地方,那些地方并无特别,成为禁区充满着随机性,开始只是偶然的战火盲点,然后双方都觉得有必要保留,这些属于君子协定,彼此心照不宣,就如同厚冰总要凿几个呼吸孔。
在前线的第二个月,他身心投入在等天空放晴,钢盔是内地人,没到越南战场前,无从想象热带雨季的可怕。他快腐烂了,钢盔快要死了,同伴经过身边,信手翻下眼皮,无论身处多远,其他人都要过问,这家伙怎么样?活着。他们失去兴趣。静卧让钢盔恢复几分元气,又开始挠血肉模糊的肉体,稍得闲暇便破口大骂,咒骂该死的雨林,该死的天气,该死的皮炎孢症,只有该死的越南佬始终没出现,越南佬潜伏周围,上星期花旦又被他们干了,钢盔藏身的坑洞较大,另外还有七个人,花旦、流氓、李小文、老九、小K、通讯兵阿訇,还有班长老光。花旦长得象娘们,凭这点他就该死,话是流氓说的,尸体也是他背回的,我们知道这事情的风险,放冷枪的人很可能没走,等着收拾处理尸体的人,越南佬最擅长这种伏击方式。那天晚上流氓痛哭流涕,像个娘们,其他人很安静,钢盔以前误会这俩人是死对头,战场上的厌恶与兴趣相投毫无逻辑,流氓相貌粗俗,乐于向人吹嘘过去的流氓史,假设他所说的一半属实,现在该去农场改造,而不该出现到这里。家里让我当兵,早知道受这活罪不如让公安抓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老子十八年后还是条好汉。挠皮癣时,流氓歪咧着嘴,从中发掘出莫大快感。花旦没染皮肤病,这成为流氓对他人身攻击的理由,流氓认为花旦在挑衅所有人,大家在坑洞解决大小便,用空罐头接了,晚上扔对面阵地上。他们高呼一声,让越南佬吃屎。任何举动都可套用为爱国主义,越南佬也朝这边空投屎罐,双方投掷互角,开辟出爱国运动的第二战场。花旦从不参加此类游戏,会藏身到别人无法观察的角落去排泄,甚至不惜跑出掩体。最早发现花旦失踪的人,只能是流氓,流氓刻薄的提醒在场所有同伴,花旦又藏起来了,他想发动所有人参与寻找,但别人兴趣索然,流氓恶狠狠说,他丫搞不好是代父从军的花木兰,找机会扒下裤衩瞅瞅,长没长壶嘴。以前花旦遇到过麻烦,半夜碰到巡逻队,差点造成走火事件,他被通报处分,通报回避了敏感字眼,罪名是擅离战斗岗位。花旦彻夜未归,第二天他们发现小河边躺着个人,半个脑袋被打飞了,多余的眼珠垂到卵石上,猴皮筋似的韧带连着剩下的另半边脸。
以为很快有人来接替,像自己填补以前那个钢盔的缺,钢盔期待花旦的替代者出现,这个愿望支撑他挨到旱季,身体状况每天都见好转,虽然皮炎还在折磨人,但钢盔逐渐适应。战场就是这样,替自己营造期望,有进展就活多了一天,钢盔后来发觉,他被卷入的是场生存游戏,身边的战友都是竞争者,他们相互较量,谁能活得更久。生存游戏的唯一要素是规则,自从花旦死后,老九被他人冷落,当时发现花旦的人,除了流氓,还有老九,他们俩组成个搜索小组,老九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外号因此得来,略过前面的修饰词,可能是所有人都很臭,谁也不想提醒了自己,坑洞就是鲍鱼之肆,钢盔后来亲口尝过鲍鱼,几十年后他发现这种贝类生物如此味道鲜美,就想起老九当年说的鲍鱼之肆,他非常想找老九求个解释,这么多年以后,钢盔已经忘记,当时他跟着其他人排斥老九。老九做了件非常丢人的事,流氓到河边背起花旦尸体,老九跑了,老九解释他想叫来其他同伴,以免流氓陷入埋伏,在总结报告上班长老光写道,临阵脱逃的行为,充分暴露出知识分子狭隘自私的软骨头天性,他本来还写着,老九骨子里对劳动人民歧视,交报告时,老光主动划去了这行。
每个新兵会得到应有的指点,最初他们听得匪夷所思,钢盔只记住几个禁区,班长老光说,记这些够了,别的没用。阳台的前身是山丘,我军或越南佬的炮火,一阵误射山头削平了,这里地势平坦阳光明媚,于是阳台上多出条隐形线,南部是越南国界,钢盔躺在靠北的领土上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太阳,对士兵而言,国界就在脚下,他们不会轻易逾越,前线必须恪守的准则是,没接到命令前,别激怒对手。当然总有人喜欢出格,他们漠视规则,对其他人而言是潜在威胁。李小文没有绰号,钢盔发觉到他的特殊,他胸怀壮志,想在战史中留下真实姓名,这些话由李小文亲口所说,李小文躺在钢盔左侧,钢盔右手捏着步枪,李小文说了很多话,有些话关乎私密,私秘到你不互换隐私就倍感羞耻。如果通讯兵阿訇不出现,这次交谈也许会让钢盔成为李小文的知己,阿訇带来上头的命令,他的长鼻子刚冒出阳台,所有人都紧张了,阿訇把电报递给班长老光,老光告诉大家,上头命令他们明天中午前攻占309,大家长吁口气,309阵地早被越南佬丢弃了,在前线这尽人皆知,那里有河流,各种野兽,冷血的蛇,可能还有很久前投掷的爱国粪弹,那里的河通向阳台。中国领土向下有一泓清泉,往前再有个积水潭,每个阵地附近必须有潭清水,越南女兵出浴时日光批离,老兵们口沫横飞,他们热衷于转述故事,仿佛千里迢迢前来越南,纯粹为了欣赏越南女兵的裸体,老兵们手搓皮屑,象正被刮下鳞片的活鱼,他们面容扭曲的干笑。钢盔注视水潭,想起几天前小K用手榴弹炸鱼,河在水潭下游,花旦死在河岸,小K拉了引线,把手榴弹丢进水里,河很浅,河床垫满卵石,卵石碎末如礼花绽放,小K因此遍体伤痕,他鲜血淋漓跑回坑洞,语气凝重的告诉大家,刚消灭掉整团编制的越南佬的鱼。
他们淌过小K炸过鱼的小河,通过抽签事先决定了战斗序列,老九位置最靠前,其他人兴高采烈背起装备,老九怀疑抽签做过手脚,他只对钢盔嘀咕,总会这样,等我出事后,肯定换成你拿到这张死签。钢盔被吓坏了,拍着老九胸膛给他鼓气,你不会出事,我们是战友。越南人会不会回来,钢盔右边挨着李小文,李小文严峻的扫视周围,他没兴趣再向钢盔提问。留意疯子李小文,他才不管你侧翼有人没有,要自己管好自己。流氓从身后捅了他一脚,钢盔还以为遭到越南人偷袭,那一脚踹得他屁眼剧疼,钢盔怀疑自己肛裂了。你看到老九在哪,我这看不到。声音从右边传来,看到有蓬茅草在哆嗦,李小文露出小半个头,象头愤怒的豪猪。跟我冲。李小文斗志激昂,呼唤钢盔跟上他,但钢盔被流氓制止住,别跟他乱跑,管好前方和右边,后面有我在,小兔崽子。流氓恫吓钢盔,再跑往脑勺上给你一枪托。争吵被老光及时阻止,他让流氓转身保护后面,命令钢盔保持原位。再出声,把你们俩都毙了。班长,李小文已经跑去前面了,我右面没有保护。老光恶声恶气回答钢盔,留给越南佬收拾他,你不准离开位置,妈的,有枪声,肯定有越南佬,全体趴下。前面越南佬似乎不多,他们只听到一个点射。阿訇给团部发电报,前往309途中遇敌优势兵力,请求炮火支援。这是老光在混乱中作出的最后布置,之后榴弹炮的呼啸把一切掩盖了。
阿訇半蹲在地,听班长老光口述战果,每句复述一次,老光点头后再发送出去,其他人负责警戒、打扫战场,钢盔和老九贴背而行,流氓和小K另组一队。等他们离开稍远,老九压着声音说,看老光的脖子,仰得跟打鸣似的,真拿自己当首长。老光站的地方是个弹着点,整个人被罩进硝烟中,象正被熏烤着的烟鸡。钢盔急切想了解李小文的安危,他移动得快,连带着老九步伐匆匆,老九不断提醒,别招麻烦,别招麻烦。老九突然停下,枪指着块岩壁说,这就是招惹麻烦的结果。一个面目全非的年轻人,直面老九的枪口,年画那样被贴上岩壁,四周深红浅红,非常喜庆。那个温暖而尘土飞扬的下午,只有背阳的岩壁显得阴森,他从明晃晃的阳光下跳到背阴处,李小文的肉体呈现青灰色,阳光撕扯比目鱼肌的咯吱声,雪白的骨头刺穿皮肤,一根手指掉到地上,当时流氓产生了错觉,怀疑是阳光杀死了李小文,而非该死的炮弹,他收藏了掉在地上的手指。他们先要处理遗骸,老光命令钢盔和老九去处理,想把李小文整个从岩壁剜下,并不是件容易事,李小文与山岳化为一体,就象古诗所唱颂的托体同山阿,好在钢盔带着匕首,他象个石匠趴在岩石上,手势却如同执行剐刑的郐子手,李小文被剜成了堆碎肉,要按着轮廓进行拼装,所有人参与进来,居高临下指点钢盔完成拼图。整个下午,他们成功复制出完整的李小文,地上只多出堆五脏六肺,他们很满足,李小文带着满腹理想而死,像葬身拍下的母苍蝇,留下一肚子的卵。
刚占领的309阵地,连充盈着污水毒蛇的坑洞都没有,流氓提醒班长老光,越南佬随时会接到反攻命令,老光仰面观天,忧愁的发现天色渐昏。老光通知阿訇请示上级,这期间老九偷问钢盔,听过李小文的理想没有,钢盔手拿匕首,想把李小文的肉屑从指甲缝里清除干净,老九告诉他,李小文对每个人都说理想,每个人都恨他。他们花几小时挖好散兵坑,在坟墓那样冷的散兵坑里守了个通宵,不敢篝火,冻成几根陈年麻花,太阳一出来就摧枯拉朽般的倒了,清晨,上头指令他们放弃309阵地,快速推进至412地区。听到这命令时,连阿訇跟着大家骂了声狗屁,所有人同时闭嘴,惊愕的望向他,阿訇眼皮跳了,表明阿訇非常紧张。他们回412,他们原先的坑洞,李小文是个大问题,他们用雨衣将李小文盛殓,李小文重新被裹成一团,外面用医疗绷带扎了几层,还是由流氓背着,路上他突然哭了,钢盔想起花旦死的那天。老光做出个聪明的决断,让阿訇给上头发了最新汇报,老光报告说他们伤亡严重,要求补充兵员,他把花旦和李小文的名字又上报一次,果然接到就地休整的通知。
补充进来了两个新兵,其中一个肤色白净,理所当然被叫成花旦,另外那个新兵姓闻,他们随口叫他小闻,后来意识与李小文谐音,他们颇感宿命。小闻很快察觉到隔阂,但不知事出何因,与多数中国人一样,他天性安分,又擅长投机取巧。入伍前两年,小闻被分配去养猪,他们告诉他,养得好一样立功,还没风险,但他运气不够,一窝吊肚子猪,不下崽也不出膘,立功无望的他不甘就此退伍,主动申请上前线,小闻有口好牙,钢盔喜欢看他傻乎乎的笑容。老光整天愁眉不展,新兵到位往往代表新任务将临,在前线熬了两年,他太了解潜规律,老光唾口浓痰,怒目园睁,看他们搞的破事,养猪的都派上前线。老光浓烈的家乡口音,带着很重的卷舌,似乎是最适合骂人的语言,一嘟噜舌头打卷的颤音喷薄而出,有开机关枪的通感,他的对手往往在连续抨击下,满脸紫青,半天憋出个把单词,只能算是单发,而且叽里咕噜的发音配合震怒时微翘的鼻翼,形成共鸣。
以前那些战役只算作儿戏,这次才是动真格的,他们将离开坑洞六天,穿过越南佬的前沿阵地,步行十几公里潜伏下来。然后呢,然后要做什么,他们谁也不知道,上头给他们一天时间准备,除了两个新兵,其余人双目朝天,瞪了整个通宵,第二天呵欠连天的出发了。他们满眼血丝,看上去斗志昂扬,两个新兵堕在最后,阳光依旧甩着媚眼,那是执行任务第一天的下午。他们经过309阵地,决定小憩片刻,他们各司其职,老光前往树林葱密的岔道,那些树无从分辨高矮,庞大的树冠,遮天蔽日,阳光都只能顺缝隙漏下,这是个搞伏击的好地方。不用任何人提醒,象尾椎上延伸的骨刺,老光观察敌情时,阿訇自觉会照顾他身后,可惜他手里只捧着无线电,真有越南佬也形同虚设,阿訇看到小K临河而立若有所思,兴许在凭吊往昔的丰功伟绩,在前线,小K仿佛是隐身人,除了炸过越南佬的鱼,从不做任何出格事,河水比上次见到时浑浊,小K无缘看清楚那些鱼,气泡冒出水面,鱼星或是沼气,他厌恶水里的腥臭,他对任何富含蛋白质的气味异常敏感,入伍前小K在菜市场上班,荤菜柜台的营业员,脂肪紧缺的年代,他从事的工作无疑会赢得市民普遍尊重,小K虚晃手臂,像又扔出几颗手榴弹,微泛玫瑰色的阳光碎片,悄无声息的随着河水流往下游,这让他心情舒解,接着又闻到腐败的真菌味,循着味道看到流氓和老九,流氓和老九分别靠着棵树,树阴苔癣阴恻的环绕,小K诧异这种环境下两个家伙竟能酣睡。钢盔终于找到那块岩壁,几天而已,痕迹已经渺然无存,好像李小文从未存在过,钢盔想到刚来的小闻,老光命令两个新兵去巡逻,这两个家伙嬉嬉哈哈晃着,笑声惊动流氓的好梦,流氓怒叱一声,两个新兵跑远了。
他们参与进小K发明的新游戏,兴趣盎然的忘了巡逻,更早是见到被雷伐倒的花梨树,花旦欢呼着跑过去,倒霉的树,刚被巨人扇过一巴掌,侧躺在地。花旦是根雕手艺人,家传数代,从未见这大品相的花梨树根,他情不自禁要谋篇布局,手指揣摩根瘤与凹孔,想到凹空里可以雕嵌像章,他只会雕像章,而他父亲以雕佛像出名,祖父也擅雕佛像,曾祖父更是清末微雕大家。小K双手捧着个东西,自河边过来,路过流氓身边时,流氓有气无力的睁开眼。小K一摊双手,拢出只出羽不久的雏鸟。越南佬的鸟。重音落在最后字节上,故意使人察觉到咬牙切齿。几个人围住树桩,钢盔率先到达,他询问关于根雕的常识,听懂花旦的答复后,钢盔自以为成了行家里手,便饶有兴趣参与争论。他们争论凹孔应该放什么,小K过来看一眼,信手将叽喳乱叫的雏鸟丢进里面。该放越南佬的鸟。他嘿嘿阴笑。他对雏鸟变型的大嘴非常不满。喂不饱的越南佬。他弯腰挖了点红泥,揉成个球塞进鸟喙,雏鸟被噎了,努力要把泥球咽下或者吐出,结果粘在食道口,哀号声声,如同三极管脱焊的矿石机。
他们在玩种名为活埋越南佬的傻游戏,每人手捏把土,依次填塞到凹孔里,小K,钢盔,小闻,花旦,严格按照次序,花旦完事后再轮到小K,最后谁把雏鸟囫囵埋了,三个输家要给获胜者凑包烟。因为忌惮别人渔利,他们每次只捻点土末,游戏进行到中途时,流氓被吸引过来,观望几分钟后他断然说道,这鸟迟早被你们搞死,其实雏鸟已经死了。花旦憋着尿,游戏的拖沓超出膀胱的饱和度,他匆忙跑出队列,一瘸一拐藏到树后,很快别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突然爆发出哄笑,为了助兴,小K乘其他人目光积聚到树桩的瞬间,端起半自动步枪向夭折的雏鸟补了颗子弹,他们以为越南人来袭,迅速趴到地上,小K发狂似的痴笑,贸然发现小闻有直直的站着,掀翻了半张脸皮,猩红牙龈,十几颗碎牙,零落满地的珐琅质。
确认小闻被误伤,至于弹片如何折射,种种穷枝末节,现在无关紧要,老光让阿訇立即向上头汇报,途中出现非战斗减员,申请返回驻地。行动第一天晚上,他们被迫留在309等上头命令,好在上次挖过了散兵坑,只需稍作加工,就有了藏身之处。这个晚上气氛沉闷,小K躺到小闻左侧,他紧闭眼睑,血腥融合潮湿空气,盘根错节,怎么努力他依然无法入眠,流氓的鼾声如潮水起伏,他羡慕那家伙。后半夜,钢盔爬进散兵坑,摇醒老九来换哨,老九穿着肥大的帆布雨披,被风撑起裂裂作声,象是有件滑翔膜衣,身躯被膨胀出数倍。我一直认为钢盔性格缄默,尤其越南归后,失语很长时间,钢盔给我详细描述当天的状况,喷薄的倾述欲令人刮目,他提到很多细节,譬如帆布雨披,雨披是行军的必备物资,铺着当防潮垫,晚上是被子,阵亡后充作裹尸布,李小文就是用雨披裹走的。但凡话题涉及到李小文,钢盔马上补充说明,声明李小文不是小闻,他的表述充满臆想,容易让人曲解。钢盔告诉我,那是整个战争的最后一役,双方都知道战争要结束了,所以急着打上一仗。见我不得其解,他调侃道,就象夫妻离婚,总要打闹一场,才裂得彻底,彼此间了无牵挂。
没接到新指令,任务还要继续,老光用水杯做成签筒,阿訇撕下纸,填上姓名,怒目圆视每个名字,揉成很紧的球团,再丢进签筒。老光是头领,还有通讯员阿訇,这两人必须到达目的地,伤员小闻要送回坑洞,那里留有急救用品,他需要紧急处理,一旦被感染有可能丢了命,他们要挑两个人出来护送小闻,结果小K和老九领到回签。未等到其他人走远,老九幸灾乐祸的笑,他说,你现在也被排挤了,凡是跟我在一起的家伙都没好下场。老九最后的话,缠绕了钢盔整整三天,在前线的几个月,让他变得多愁善感。三天后,他们到达指定地点,接到最新指令前,他们不能动弹,埋进齐腰深的草丛,跪着或是蹲着,山坳前方是越南人的村庄,快到晚饭时,到处冒起炊烟,淡青灰色,带点透明釉,整个山峦的阴影垂直下来,重量压到他们背上。
坑洞突然昏暗,但仍然是下午。小闻像个卧倒的油町,挥霍着体温。小K不停抱怨,现在光线暗弱又激怒了他,他勉强看清左手,苍白色闪光,指甲病态般耀眼,他的左手搭在担架边缘,担架晃动的频率让他忧心,担心小闻颠到地上,他只能用手托住颤抖的担架,很快半边身体就麻木了。小K要抽身而出,他问老九,找到奎宁药片没有。这是他第三次发问,老九半个脑袋探到洞外,侧脸向天。快下雨了吧?湿气很重,借助说话小K才能透气。老九走回担架旁,也向那看了眼,光线落差让他无法适应,所幸尚有悉琐之声。这家伙抖得厉害,可能染上了疟疾。语音刚落,外面砸了个雷,老九被吓得不轻,密集的雨点声又让他长吁口气。昏暗使得小K多愁善感,突然担心到老光那行人,小K问老九,不知那些人怎么样。老九不知怎么回答他,蚊子绕着老九身体乱撞,无论他怎么晃动,聒噪的飞虫毫无退意,他担心蚊子传播疟疾。一定要找到药片。老九停顿一下,他想说,我们迟早会被传染,结果强忍了回去。他们终于沉默了。
第一滴雨落到流氓头上,象机油灌进锈蚀的马达,唇齿间压抑的机械磨合声,他的同伴各行其事,流氓想引起他人注意,他攥紧李小文的一截断指,那是流氓的护身符。他们各有怪癖,花旦的征兆还不明显,时间问题,只要继续活着,会和其他人别无二致。已经是第五天,可能上头把他们遗忘了,常有的事,因为无线电静默规定,他们只有坐观其变。惟独花旦很活跃,几次爬到阿訇左近,询问最新指令,雨披擦过草叶边缘,比流氓永无休止的咒骂声,更触目惊心,花旦瞬间被所有人目光聚焦,只有流氓神态不忿,鼻翼张阖,鼓动出沉闷的吼声。由于疏忽大意,等到他们发觉,放牛的越南小孩近在咫尺,这孩子得过天花,凹凸起伏的脸皮,眼睛被压成细线,有双招风耳,他听到声音,好奇心让他丢下小水牛,一路摸索过来,他们藏身之处很隐蔽,不幸的是孩子被荆棘拌住脚,摔在地上,透过草茎缝隙,老光班驳的眼神落在他的脸上,他未及出声,老光手掌已经捂住越南小孩的嘴,挣扎中他被咬了一口,疼得嘴角直拧,阿訇整个身体扑上去,越南小孩不能动弹了,头部扭动频率也没先前剧烈,阿訇从后面勒住小孩脖子,他看老光一眼,见老光点了下头,便手臂向左一转。阿訇说行了,老光才缩手回来,问阿訇要点酒精棉,把伤口草草处理过。那条牛是个麻烦,会把越南佬招过来。钢盔点点前方,有响鼻声,听上去那畜生非常享受。小K在就好了,他对付这些玩意拿手。钢盔突然感慨了一句,他爬到老光这边,看眼咽气不久的小孩,干蜡般的黄脸让人恶心,钢盔别转过头,看到花旦刚匍匐前进到自己脚边,钢盔嗡声嗡气的评价道,越南小崽子真难看。猛然发现,自己正在模仿流氓的口音。整夜飘荡着越南佬的叫唤声,象是唱着招魂曲,越南佬不敢上山,但回声形同符咒,乘着夜色打围,令他们寒彻骨髓,他们聚求一处以谋温暖,丑陋的孩子被搬至近旁,直面尸骸他们默默无语。虽然不懂越南话,估计那些人在喊失踪孩子的姓名,象某个老电影明星的名字,流氓踹了尸体一脚,问他,你叫阮铃玉。越南孩子动都没动。
担架停止了颤动。那两个人埋首谈话,丝毫没注意到变化,老九谈到金鸡纳树,他告诉小K,奎宁原料就是金鸡纳树皮,几天独处下来,小K对老九刮目相看,他习惯做任何决定先咨询老九的意见。小K问老九现在该怎么办,小K的本意,要等所有人回来再处理小闻,他提醒了老九,老九转而问小K,担架好象不晃了。小K手搭回担架上,又举起了贴到脸上感受一下,等他再推搡小闻身体时,小闻哼了一声,声音细若游丝。老九与小K站到并排,摸过小闻额头后说,不能再等了,就算他们回来,一样是没药。他说的情况属实,老九说现在就要去邻近坑洞取药,这非常危险,要经过两处越南人阵地,老九等了小K很长时间,最后长叹一声。
他们汇报上级,行动已经暴露。三天后接到莫名其妙的回应,上头表彰他们阻击任务完成得出色,为主力部队赢得时间,同时通知他们,战役正式结束。那时他们自行撤回了原来的坑洞,正在讨论老九失踪事件。这家伙迟早是逃兵,只有阿訇在第一时间点头认同,老光巡视左右,那些家伙正忙着,只有小K闲着发楞,小K发楞有了几天,老光觉得有责任点醒他,他高叫小K的名字,凯跃进。由于是小K的本名,所有人茫然四顾着,老光尴尬的重叫一遍,被推了一下后,小K总算明白老光在等自己表态。到处都是越南佬,也许老九真出事了,再说熬到现在,这该死的战争总算要结束了。小K的话提醒了大家,他们悲哀的发现,无论何种结果,老九的失踪都是不折不扣的悲剧。
士兵们不会沉溺悲伤,战争已近尾声,以后的日子温煦明媚,他们镀着满身黄金,象群闲逛的旅游者,越南佬同样如此。幸福日子总会万事顺心,小闻突然病愈,虽然半张脸上血肉模糊很骇人,终究活了下来。钢盔迷上了根雕,间歇会跟随花旦到外面挖掘树根,现在这种状态,只要避开地雷,就不会生命之危。当然戒心依旧存在,钢盔没遇过越南佬,越南佬当然就在附近,树林会传达很多信息,一群鸟突然惊飞,树叶不正常的颤动,渐渐他对这些征兆变得麻木。他们不自觉在改变习惯,也许是为了适应离开战场后的生活,包括彼此间称呼,钢盔在那段时间内,温习了所有人的真实姓名,他们各自称呼对方本名,但叫得非常别扭,一周后又恢复到原先。这段时期最离奇的事情,是花旦带回来一个越南兵,他们俩肩扛着根奇形怪状的树干,一前一后喊着哨子,显得非常默契,这一幕让其他人瞠目结舌。花旦做得太过分了,但沉浸幸福中的他们保持了克制,其中很重要的因素,那家伙没携带武器,越南兵与花旦比划运刀走势,他说一口流利的国语。整个事件荒诞不经,那些人用方言咒骂越南佬是神经病,显然越南人不懂方言,甚至还抬头报以微笑。后来他们抽起了越南佬递上的烟,第一口烟雾从坑洞弥漫散开,越南佬开始自我介绍,他倾述欲极强,可能憋了太久,说起话有些结巴,他说自己是南越人,为增加可信度,报出吴庭艳的名字,可惜他们从未听说这个前南越总统。
流氓掐灭掉烟头,跑去外面吹口哨,原调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他拖缓了节奏,透出点抒情味。小K跟着也出来,眯着眼倚着块石头,不一会他们又看到钢盔,钢盔边走边摇头说,越南佬太能唠了。小K问,说到哪段了。还在西贡城,正和法国女人亲嘴。前面的那个法国老女人?不是,应该是老女人的女儿。钢盔也没搞清究竟该是哪个女人,他只是随意作出判断,但引起流氓的忿忿不平,流氓叱骂了声,这个越南流氓。那两个人与流氓对视一番,接着他们开怀大笑。他们揣测法国女人的长相,不能便宜越南佬,于是法国女人被勾勒成秃发、龅牙、独眼、驼背、瘸腿。每说一句,都引起一阵哄笑,最后小K给女人编排了满脸麻子,蜡黄的脸。流氓与钢盔同时刹住笑容,眼前清晰浮现出另一张脸。
钢盔平安离开了战场,他曾经以为自己是最幸运的人。他告诉我,花旦带进坑洞的越南佬名叫阮铃玉,和死去的电影明星重名。他说,就因为这名字,我们差点杀了他,那家伙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他习惯被当作钢盔,当有人叫他本名,他就会结巴,象坑洞里那个越南兵。钢盔真的去过前个钢盔的家乡,但没找到那家伙的父母,他忘记了前一个钢盔的真实姓名,这让他惆怅很久。退伍后一年,有封发自越南的信笺邮寄到他家,愕然发现竟是自己写给前一个钢盔的那封,他反复看过好几遍,依然被深深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