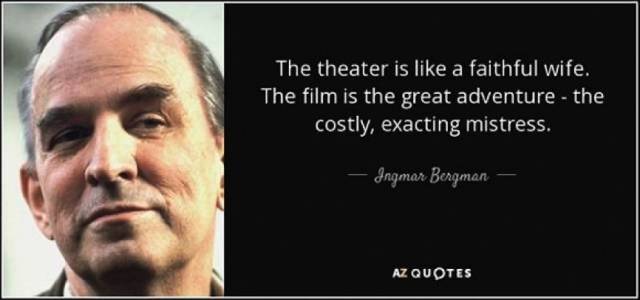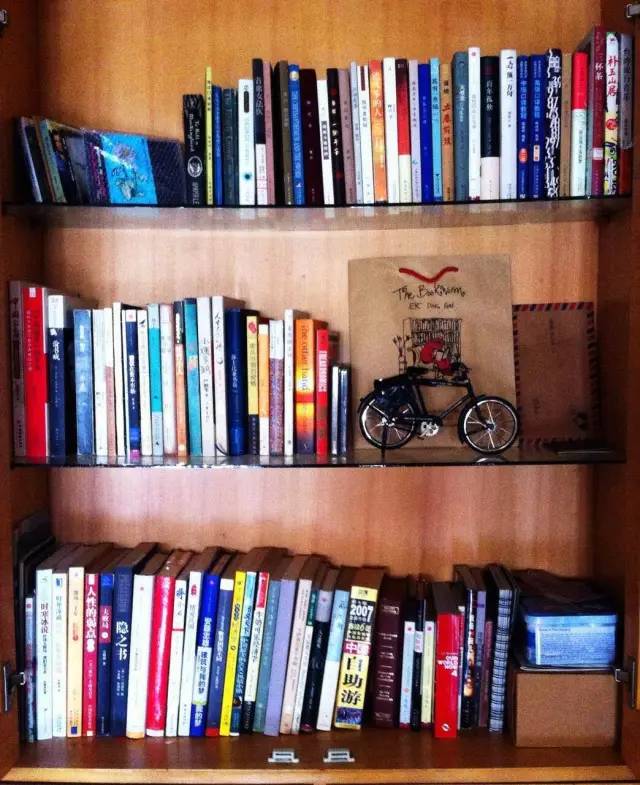▼
蓝贝工作照
编者按
北京的盛夏,干燥,炎热。楼下的狗伸着舌头堵着门口,缩在阴凉下,连踩它的尾巴也只是瞄我一眼,不叫了。我正午出门,听着Bruno Mars的《Lighters》打鸡血。经过小花园的时候,正巧是歌曲说唱的高潮,宣誓般的歌词越渐有力,鼓舞人心。抬头是被法国梧桐遮蔽的半个天空,阳光透过枝叶散落下来,耳机之外是撕扯拉长的蝉鸣。我站在那,恍惚法国梧桐变成了成排的香樟,耳机里的歌声掺杂了回忆的人声。那一刻的我,仿佛在夏日的歌声中融化了,这是多么美好的夏天!有关青春与梦想的夏天!我打开了朋友圈分享了这首歌,想起两年前的那个上海的夏天……
一分钟后,蓝贝发来消息:“Bruno Mars来过上海开个唱哦!我去听了,很棒。”
“是吗?不要刺激一个去不成上海的人啊!上海啊上海……”
“哦?你对上海有情怀吗?我可是对北京心神向往呢!”
“好啊!我们来换啊!”
“那,我们先交换故事吧!”
“比如,你的戏剧故事……”
蓝贝,是一个误入油气行业的高级工程师,有着工科生的严谨逻辑,又有文科生的感性温润。很多时候想用一个标签去理解他,却发现他是无法归档的人。中药铺每个抽屉都有一位药,可他却无法放入任何一个抽屉。他最欣赏的气质是沉静与自由,那种中国山水画里才有的气质,也许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吧。我很喜欢和他分享古典文学,讨论历史,那些过去的别人的故事。今天,他将分享他自己的故事《戏剧在彼岸,而我在这里》。
戏剧在彼岸,而我在这里
Sarah Boxer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称,伍迪•艾伦很遗憾自己的灵感只是喜剧方面的灵感,而不是戏剧方面的灵感。“与我现有的天分相比,我更愿意自己拥有尤金•奥尼尔或者田纳西•威廉姆斯那样的才华。我不是在抱怨。我很高兴我竟然有了某种才华。但我想做点了不起的事。”
广为人知的瑞典国宝级的伟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他几乎斩获过各大电影奖项,也被拉斯•冯•提尔、伍迪•艾伦、李安等知名导演奉为影坛巨匠。但对于伯格曼而言,他其实将一生之中大量精力投入了戏剧,这使他成为了欧洲当代戏剧舞台上“最激动人心、最具革新精神的导演之一”。他一生创作了50余部电影,却创作了120多出戏剧。 事实上,他的电影演员,很多就是他的剧组成员,他们是在拍戏的间隙,“插科打诨”地去拍了些电影,然后成了电影大师。当他谈到戏剧与电影的关系时,他这样说,“戏剧是忠贞的妻子,而电影只是刺激而骄奢的情人(The theater is like a faithful wife。 The film is the great adventure - the costly, exacting mistress)。”戏剧见证了他导演风格的转变与成熟,更是他一生的陪伴和慰藉。
我想,这也是我更偏爱戏剧的原因吧。
▼
蓝贝部分票根
电影演员导演深爱戏剧的例子还有很多,我想或许是与电影相比,戏剧对他们更具吸引力吧!似乎电影更是是一份工作,戏剧则更像心灵家园,他们不论在其他艺术上有了多大的成就,那块有限的舞台空间,始终安放着他们丰富而激荡的内心世界。
是啊! 戏剧是那么富有魅力,几乎所有进过剧场的观众都会被它所俘虏,当然就包括我。在我看来,戏剧与电影或其他艺术形式所不同的是,他更强调“人与人的相遇”,在剧场里,舞台上那种拳拳到肉的真实感, 演员的表演更富有张力,不会像电影一样隔着一层屏幕,白白消解了那份情绪,那份能量。
在简单的空间中,观众可以“时时捕捉到他们(演员)的面部特写”(伯格曼语)。有的导演甚至将舞台延伸到观众席当中,方便观众近距离体会演员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变化。伯格曼曾说主题、演员和观众是戏剧不可或缺的三要素,他曾通过高度凝练和集中的戏剧主题和形式,消除观众和演员的距离,尽力让演员激发观众的情感反应,这种探讨剧场与观众的关系,把观众作为戏剧的一部分的艺术手法,一直是我觉得戏剧最有魅力的地方, 在我看来,戏剧的成功就取决于双方交流的强度。这也是我不停走进剧场的原因。
我们热爱一件东西,通常是与我们的知识结构有关的。 我们因为懂得了一些知识, 就可以从一个很小的点走进去,然后从这个很小的点出发,越走越远,越走越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不论是做学问,还是其他的娱乐,都是如此。戏剧的舞台虽小,走进去却可以见到一个大天地。舞美、灯光、肢体、表演、剧本、音乐、道具、技术管理、各工种协调配合等等等等,都是一个个的大世界。所谓螺狮壳里都可以做道场,况乎这样一个集多种艺术形式于一身的戏剧艺术?
我不是戏剧科班出身,甚至都不算一个资深戏迷,但是也许正因为我不科班,我能有更加不一样的知识结构,我所看到的戏剧与其他科班出身的老师和朋友更加不同。至少像我这种理工出身的戏迷来说,戏剧理论肯定不是我所感兴趣的,学院里那种戏剧流派的争论于我也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就像最好的作家肯定不是中文系毕业的一样,一部好戏的诞生,在我看来,也绝不只是技法上的炉火纯青和无可挑剔。
在我这个外行看来,戏剧本身是一个充满遗憾的地方,每一次演出,都充满遗憾,正是有这些遗憾才令戏剧更有魅力。
这有点像看艺术品,我们会看到日本的一些工艺品和绘画特别好,简直好到无可挑剔。但是同样是具有东方审美的东西,你会觉得还是古代中国的东西好,它那种经过历史积淀下来的“不喧哗,自有声”的气场,是现代多么先进的技术和工艺都仿造不出来的。现在科技发达可以造出完美无瑕的东西,但是也正是因为他无暇,无错,这件东西才缺少点什么。
而艺术是需要错的,是需要有遗憾的,是需要对错交织,彼此碰撞,彼此映衬的,戏剧的不可剪辑性决定了它天生是有缺憾的,而这份缺憾让它无可取代。可是,貌似这一点并没有被普遍认识,包括很多学院派的老师们,他们好像也并没有担负起应该担当的责任,反而放弃掉精英的责任感,放弃了心法的东西,转而去追求一些技巧性的精益求精。而这是古代伶人们干的事儿,因为要帮着皇帝去教化子民,所有是非善恶美丑都那么分明而简单,把人性的复杂完全的舍弃掉,给予人物完全脸谱化的描述,这是一种退步,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这已经不是遗憾了,这是媚上,同时也是媚俗。
对于有追求的戏剧创作者来说,戏剧是否应该具有内涵?是否应该具有哲学性或哲学价值,是否不仅仅是消遣和娱乐?至少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仅仅停留在消遣和娱乐,仅仅是逗人一笑,惹人一哭,那么我想不出如何去评价一部戏其表达的深度、广度和张力。
▼
蓝贝支教时与孩子们
中国新时期的戏剧,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破除政治观念模式——三突出、高大全;80年代中期的破除艺术观念模式——写实定于一尊;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的先锋实验和科技技术;90年代中期以来的舞台多元化发展和舞台大制作。这些结果倒像是导致了时下圈内一些人归纳的、但绝非夸张的舞台现象——一流的舞美,二流的表演和导演,三流的剧本。大家仿佛越来越追求“术”,而忘了“道”。但是,我觉得,戏剧可以有多重叙事语言,舞美、灯光、表演、舞蹈、肢体、音乐、语言等等吧,但是所有的叙事语言,都应该为一个主题去做贡献,而不是一个看起来眼花缭乱的大杂烩。
冯小刚导演曾说,是现在的垃圾观众导致了垃圾电影(大意如此),我个人其实是深表赞同的。普通观众对戏剧的低要求,只求消遣娱乐,或者只是抱着社交功能进剧场,而资本势必要迎合这批主流观众,自然令创作人们放弃掉自己的理想(假设他们有的话),去造出一大堆不能称之为戏剧的玩意儿。
不是说戏剧非要戏以载道,无限拔高到什么程度,但是戏剧绝不应该只是消遣,只是令人哭哭笑笑,是不是也应该有些思想的启蒙作用?或者启发启迪也行。现在很多剧作者总喜欢拿无政治化说事儿,因为审查无处不在,所以他们很喜欢说我拍的东西就是为了逗观众开心的,我不想谈社会问题,不想谈政治,只想谈点风月,谈点家长里短,日常生活。这种创作方式,在当下的商业时代或许无可厚非,毕竟不能也没有必要要求所有的创作者都像伯格曼那样,动不动去讲一些生与死、灵与肉、精神与存在的问题。
但我想,家长里短,风俗人情,也有好多种拍法,不一定非要拍的那么媚俗,曾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反感有些戏在宣传里说,这戏惹得观众爆笑多少次云云。活活像个站街女,靠卖笑吸引观众,是把观众当做了嫖客。
在政治无处不在的情况下,是否不媚俗的戏,就真的没法拍了?我觉得还是一个用不用心,有没有自我要求的问题。
▼
蓝贝部分藏书
我记得明朝的张岱有两部著名的散文集《陶庵梦忆》和《西湖寻梦》,都是前朝的种种世相。从富贵人家的极奢荣华,到布衣百姓的平常热闹,街巷吃食,茶楼酒肆,说书唱戏,也有文人、士大夫的讲究生活,讲的也很好,很不俗。
史景迁在《前朝梦忆》中这样记述张岱的一生轨迹“在张岱眼里,生活多是光彩耀目,审美乃是人间至真。在精神的世界一如舞台生活,神明的无情操弄和人的螳臂当车之间并无明显的分别。我们所称的精神世界,只不过是人神各显本事,各尽本分的交会之处而已。张岱一生都在探寻这种片刻” 。我们的戏剧创作者,能否也学学张岱呢? 哪怕认为神明的无情操弄和人的螳臂当车之间并无明显的分别,是否也可以探寻一下“人神各显本事,各尽本分的交会之处”呢?
我想,不论何种艺术形式,最终的优劣好坏,还是要落实到从业者的文化内涵上来。不要仅仅学人家的风月,骨子里的内涵才是表面风月的原动力。就像世人只知道去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的书法,却没有好好读读序的内容,其实也是锦绣文章;世人只知道张岱是个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却不知他的“好”都不是普通的爱好,而是于每样都是行家,几乎精通晚明所有的艺术门类,同各种不同领域里的精英交流往来。而且,他不只是会这些“雕虫小技”,在明亡后,他辗转避居于山庙间,飘零岁月里仍然带着卷帙浩繁的明史诗稿,八十八岁那年,他完成了一部明史巨著《石匮书》,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学习前人的风流时,切不可只学个皮毛,一知半解,最后蹉跎青春,害人害己。
作为一个业余的戏迷,说了很多“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无意挑战任何人。事实上,对于戏剧在我生命中所占的比重,我从来不太确定,我爱它,却也从来没有痴迷于它。就像达芬奇,他爱画画,但是他不只是一个画家,他还是一个医生、一个军事工程师、一个剑术高手,一个各方面的天才。就像康有为,他是清末最好的书法家,但他却志不在此,他在国家鱼烂河决,苍生嗷嗷待哺的时候,他不想靠这些小道立于天地之间,只有他变法失败了,他才重新拿起了毛笔,去寻找毫素带给他的安慰;就像柳永,他也写过《煮海歌》这样同情盐业工人的诗,做过“为政有声”的父母官,并不只是一个只会写《雨霖铃》的风流浪子柳三变。
戏剧于我,也是类似的。我没有像很多情怀满满的朋友那样,离了就戏剧活不了。作为一个理工出身,目前主业也是与艺术完全不搭界的油气工程师,面对当下的戏剧现状,有时候,我只想走进最深邃的灵魂深处,做最浅薄的自己;偶尔与戏剧保持距离,其实也是在远离自己,但我不介意,因为那样才能看清自己。
毕竟,戏剧在彼岸,而我在这里。
你在戏中
我在戏外
我们共处一个空间
我不仅在看你
你也在看我呢
-THE END-
本期作者:蓝贝
空间戏剧责编: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