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泰精选 | 2020,我们需要“新安全”
洪泰精选:
一种新病毒在全球传播,挑战既有的传染病防控知识和国际协调机制, 暴露我们栖身其间的“安全”体系如此脆弱。
近四十年来,因科技跃进和资本激增而带来“安全”边界的扩张,彻底改变了供求双方。 尤其当科技创新逐渐打破地缘政治的平衡时,未来最有实力的敌人 不是某个发展速度过快、经济规模膨胀的国家,似乎应该 是以惊人速度与规模创造新知的科技本身 。
2020年,随着气温升高,新冠肺炎疫情或逐步缓解,而其激发有关“新安全”的思考必将持续发酵。
本文以全球化和“安全”角度切入对本次疫情国际传播的观察,其中涉及到的地缘政治、生产力分工、科技全球化等为我们在看待本次疫情全球影响上 提供了一种新的 视角和 更为深刻的层面,特此分享给大家。
全文4398字,大约需要6分钟。以下enjo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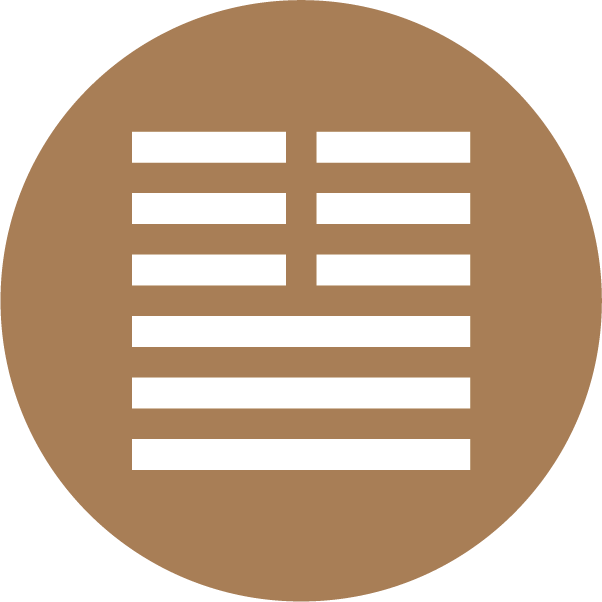 作者|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陈序
转载|公众号“FT中文网”(ID:ftcweixin)
作者|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陈序
转载|公众号“FT中文网”(ID:ftcweixin)
1
全球化完蛋了吗?
从此前2月刚举行的陈词滥调、被誉为“一塌糊涂”的慕尼黑会议来看,似乎是。美国和欧盟在关键问题上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各说各话,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拼命居中调和,然而还是没什么用。
但从越来越使人紧张的新冠肺炎疫情看,相反。种类政治人物站在对立的两边,一边认为疫情被对方低估,一边认为对方夸大了疫情。病毒学知识成为一种武器,杀伤力超过病毒本身。
一种新的病毒在全球传播,挑战既有的传染病防控知识和国际协调机制,暴露我们栖身其间的“安全”体系如此脆弱。
当世界关注东京奥运会是否停办的时候,我更遗憾地看到,从1972年的夏季奥运会到2020年的国际安全会议,在时隔近半个世纪之后,国际社会对所谓“安全”的理解,仍然受困于慕尼黑那场突然袭击的阴影,局限在经济全球化与冷战思维的对抗。(1972年在德国慕尼黑夏季奥运会上,5名巴勒斯坦“黑九月”分子突然袭击了奥运村,9名以色列运动员和2名以色列保安人员被刹。这桩流血惨案,被称为“慕尼黑事件”或“黑九月事件”。这届奥运会因此被迫停赛一天,这在奥运会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次流血事件引起了体育界人士的震惊,促使以后各届奥运会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
坐看疫情在地图上传播,所到之处经济冻结、市场下行,证明全球化由肌肤入腠理,不再局限于国家、组织和个人的外部行动,而正逐步改变它们的内部构成。疫情的爆发,让任何一国自身的公共服务——无论是资源还是公共支出都面临了压力。全球产业链却并未停摆,似乎给予全球化新的价值视角。
不过美国自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反全球化举措和战略,此前遭到了全世界的反击,但目前看起来,病毒似乎干成了美国总统想干而且干不成的事情。世界各国纷纷互相封锁,全球化风雨飘摇。仿佛叫嚣着“谁有口罩,谁就是救世主”。
显而易见,基于经济要素交换的外部贸易与分工在退潮蓄能,而源自社会身份认同的内部矛盾与斗争则汹涌而来。
传染性病毒像一艘隐形战舰,加入威胁全球化的阵营。既得利益者渐行渐远,失望情绪开始推动可能导致自毁的免疫机制,除非我们能够提出并着手解决如下问题。

2
什么是“新安全”?
我们并非为旧敌人所环伺,而是与新敌人共舞。耳闻目睹乔治凯南仍不断被垂垂老矣的职业政治家们公开引用,只能说明我们没有从他的先见之明中学到经验。(“冷战之父”乔治凯南是20世纪知名外交思想家,美国深受关注的战略家;他塑造了冷战时代,又不遗余力要打破美苏僵局。同时,他更是两届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
虽然“修昔底德陷阱”至少道出了在国家竞争力格局的变化中地缘政治的真相,但是,如同地壳板块受制于地幔对流的动力,当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根本动力——科技创新出来秀肌肉时,精心设计的地缘政治平衡危若累卵。
经历上世纪连续两次世界大战,大国关系、意识形态始终是地缘政治焦点。冷战的胜利使美国决策者冲昏了头脑,他们宣称地缘政治的一个基本概念已经过时。2008年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描述了一个“不以势力范围定义强国”的新世界。2010年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美国不承认势力范围。”2013年,前国务卿约翰克里正式宣告“门罗主义时代已经落幕”,为美国将西半球划归自身势力范围的将近两百年画上了句号。
这种说法有它正确的地方,因为地缘政治的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但至于变化究竟在哪里,它却弄错了。美国决策者们不再承认势力范围——也就是大国要求得到所在地区其他国家尊重或主导控制该地区的能力——不是因为这一概念已经过时。
相反,整个世界实质上都变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原本的多个势力范围被单一的势力范围取代,但强者照样能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弱者;世界其他国家被迫基本遵守美国制定的规则,否则它们将付出从严酷的制裁到明目张胆的政权更迭等各种沉重代价。势力范围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在美国霸权的压倒性事实面前塌陷并合而为一了。
然而今天美国霸权正在消退,华盛顿方面在其所谓的“大国竞争的新时代”面前警醒起来,因为中国和俄罗斯越来越多地利用实力来主张它们与美国相冲突的利益和价值观。但是美国决策者和分析人士仍然没有切实理解这个新时代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意味着什么。展望未来,美国的角色不仅会发生变化,而且其重要性会大大降低。尽管美国领导人还将继续宣示宏伟的雄心,但随着美国能使用的手段变少,最终取得的成效也会减弱。
单极世界已经结束,美国必须放弃幻想,不要以为其他国家还会屈就于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简单地接受自己被分配到的地位。美国将需要接受一个现实,即当今世界上存在多个势力范围,并非所有势力范围都属于美国。
现在,时过境迁,信息技术带动的科技革命替代前者,成为颠覆生产关系与政治生态的第一推动力。从而,不是国家竞争决定了科技进步,而是科技进步决定了国家竞争,改变着国家间的绝对优势。
因此,未来最有实力的敌人不是某个发展速度过快、经济规模膨胀的国家,而是以惊人速度与规模创造新知的科技本身。去年10月,美国众议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以研究如何保持五角大楼对其他大国的技术优势,并在此过程中讨论一些以前触碰不得的问题。

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网站)
美媒称,这个跨党派的国防未来工作组由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议员塞思·莫尔顿和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议员吉姆·班克斯领导,工作组任务期限为6个月,涉及范围广泛。预计它将重点审查长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并帮助五角大楼在技术上变得更具创新性。
这个新小组的任务是“评估美国国防资产和能力,评估国家安全创新基础的现状,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确保战胜竞争对手的长期战略优势”。为此,预计它将举行一系列听证会和闭门吹风会,并最终发布一份包含建议的报告,即便这些建议不受欢迎。政治生态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嵌合越发紧密。
同时,供应链的经济全球化正转化为数据网络的科技全球化。那颗结束了战争的原子弹不是坐在曼哈顿WeWork大厅里喝着免费咖啡的年轻人可以造出来。
但现在,不论颠覆一国政府还是改造人类进化树,研发者甚至不需要拥有一个车库。因为WeWork的失败,孙正义打了一场败仗,但他的眼光没错,科技全球化重塑市场与经济的愿景就像过去20年互联网与中国红利结合的风口。对中国商界来说,孙正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是马云创业早期最重要的投资者,软银目前仍是阿里巴巴的第一大股东。除此之外,软银中国还投资了分众传媒、字节跳动、滴滴、车好多集团、满帮集团等中国企业。
不过,这一次,“新安全”是左右科技全球化成败的双刃剑。
科技全球化将从个人到国家的各个组织层面动摇安全、考验信心,最迫切紧要者,莫过于加剧地缘政治矛盾,甚至战争威胁。具体表现为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相互影响,地缘政治较量与币缘政治较量相互呼应,战略施压与战术骚扰相互配合,军事威慑与意识形态渗透双管齐下,虚拟空间的真实较量与海洋空间和外层空间的争夺日益严峻,安全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日益突出。
过去,商品和服务的贸易保护主义屡次成为战争强化其“政治冲突终结者”的内在动力。现在,技术贸易保护主义会因对战争技术优势的需求而由一种政治手段变成政治目的。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数据,2018年非关税措施的总交易成本约为3250亿美元。大量的非关税措施逐渐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而技术性贸易壁垒(TBT)使用最多,占所有非关税措施的41%。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了超过30%的产品线和近70%的世界贸易,涉及对包装、标签等的要求以及所有合格评定措施。
作为“新安全”问题的出发点,科技全球化正在扩张法外之地,也在升级道德考验。保守主义和监管滞后,令科技创新不仅处在知识的边缘,也处在规制的边缘。无论基因编辑或是数字货币,对创新科技的巨大需求,包括来自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用科技解决痛点问题的供给引领、研发者的荣誉动机,绝非简单禁令所能压抑。
3
如何解决“新安全”问题?
思考“新安全”,需要重新厘定安全概念的边界。未经界定的“新安全”问题会加剧而不是优化资源消耗,增加而不是减少系统性危机发生。现代经济与生活方式的稳定性有赖对个人、组织与人类安全边界的共识与信心,边界移动则共识破裂,信心动摇,抑或引发过度保护,形成特定时间点上的资源黑洞。疫情如此,战争亦如此。
“新安全”需要新的规制手段,需要新的全球治理机制,需要国际间更多信息共享、数据交换,以及基于新技术标准的信用基础设施。解决“新安全”问题,尤其需要国家这一制度安排。相对于在过去20年之中纵横捭阖、睥睨天下的跨国私营企业,有效治理的国家愈显其在下一步科技全球化进程中的稀缺性,强大动员力、良好激励机制、信息公开透明,均能使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创新与治理进程的政府更具价值、领先一步。
国家将决定科技的发展形式,平衡科技对政治的影响,但无法阻挡科技进步的速度。自行其是的国别政策会加大全球科技竞争力差距,也会给各国国内市场带来对应的压力,而这一内部压力又会在传统体制中冲破罅隙,制造事故。
提出、解决“新安全”问题需要新型领导人。新问题不能用旧技术,每一个软件工程师都明白这一点,可大部分政府的精英领导层多数不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们更习惯于旧瓶装新酒。从过去两年马克扎克伯格出席的美国国会听证直播,到最近因防疫科技部署惰怠而饱受抨击的78岁日本IT大臣,新旧世界的鸡同鸭讲显示科技领导力的更迭才刚刚开始。
最后,“新安全”也将重构知识分子的专业分工、权力与责任。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是普通人,一样会陷入固步自封,一样需面对利益诱惑。信息不对称不仅在专业人士与普通人之间形成了悬崖,在不同专业知识的内部人之间也蕴酿着对抗。在缩小这两种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中,媒体将再次扮演重要角色。围绕科技竞争,需要更多坚持专业定位的媒体、具备专业素养的媒体人,这也是后发国家更难反超的劣势。
回顾100年前,身处“大萧条”时期,凯恩斯在展望未来经济可能性时曾定义的绝对需求和相对需求,是划分“安全”边界的一种简便方法,也是他认为人类可以在2030年之前解决最基本经济问题的信心所系。然而,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四十年来),因科技跃进和资本激增而带来“安全”边界的扩张,彻底改变了供求双方。今天所谓“新安全”,固然不再是我父辈祖辈所深信的,也绝无可能为未来世代继续坚守。2020年,随着气温升高,新冠肺炎疫情或逐步缓解,而其激发有关“新安全”的思考必将持续发酵,或能帮助我们将目光从拾人牙慧的短期记忆移向步步逼近的可见未来。
推荐
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