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人的自信,与这部长长的复“興”史分不开
在希腊神话中,伊阿宋寻找金羊毛时所乘的快船阿尔戈号,每一块木板都曾在旅途中被更替。但无论如何变化,它仍然被视为阿尔戈号本身,而不是一艘与过去挥手作别的新船。
著名建筑学家郑时龄认为,上海也是一艘同样的“阿尔戈号”。
如果历史足够漫长,一座城市的发展总会或快或慢、进程可大可小、节奏有高有低。在这一点上,上海经验尚浅,但胜在年轻。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的“興”就比中国任何城市都要更加剧烈。
快速的城市更新,让现代与历史在黄浦江两岸交相辉映。/图虫创意
郑教授对一位外国记者1886年时的判断记忆尤深:
“人们确信这座城市正在增长的重要性,它必将成为中国贸易的中心,任何推测都不足以说明,土地和资产的价值会达到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程度。”
此后,上海便如同冒险中的阿尔戈号一般,凭着一刻不停的城市更新,让前人的预言在难以想象的程度上,一一应验。
这种自我更新,能让一座城市从興起迈向興盛。
上海与阿尔戈号相似的还有另一面:剧烈的城市更新既让她难以捉摸,却也具备始终如一的高辨识度。
老城厢的新旧交织、中西交错、观念交锋,本已很难用单一的形容词定性,但人们还是从瞬息万变的画卷中,刨出了足以概括上海的定义:魔都。
海派腔调的興起:从激荡到和解
说起魔都,很有必要做一个严肃的小科普:魔都并不是日漫《中华小当家》的发明。
不过,此等透着迷之中二气息的“雅号”,确实也出自日本人的脑洞。
1924年,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出版了一本叫《魔都》的书,第一次将上海称为魔都。在村松看来,上海华洋辖区的相互冲突和渗透,在当时营造了种种特殊现象,这让上海有了与其他城市绝不相同的“魔性”。
时光倒流79年,上海在1843年正式开埠。
当年那个把守长江出海口的小县城,彼时还没有左右命运的能力,只能接受清政府无能的事实,被率先拉进现代化的大潮中。
面对突如其来的使命、淘金逐梦的奋斗、华洋争夺的社会激荡与交错,上海容下了一切的不同,从种种“魔性”中寻找着海派文化的“腔司”。
在上海话中,腔司是来自英语单词chance的舶来词。如果有什么东西够得上一个“腔司浓”的标签,那可真是腔调、派头和品味都十足了。
在激荡的岁月,淘金逐梦的浮华是腔司浓的。
犹太人马勒失踪前留下的马勒别墅,在租界内本已是让人心驰神往的存在。城堡的腔司却不在五千平方的土豪做派,讲的是跑马场淘金冒险的成功范式。
马勒别墅的设计像一座梦幻城堡,据传灵感来自马勒小女儿的梦。/图虫创意
在平和的年代,得体周到的转身是腔司浓的。
同一处延安西路1262号,哥伦比亚俱乐部是外来者的社交私域,上海生物制造研究所是新中国工业的烙印,上生新所则转身成为公共空间,与当下的市民生活共生。
上生新所经历了从体育馆、车间到休闲空间的转变。
上海的興替确实很迅速,文化却不见得会成为历史尘埃。
所有曾经的激荡与交错,都可能在开放和包容的城市更新中觅得落脚处,成为海派新腔调的一部分。
魔都生活的興旺:从局部到共融
1851年开始,巴黎也曾经历过一番剧烈的城市更新。当时,在塞纳区长官奥斯曼男爵的主持下,大批“无用”的古老建筑被拆除,让位于巴黎市中心的修路需求。
1916年,美国记者盖姆韦尔也曾对上海的城市更新,表达过相似的担忧:
“上海整座城市都处在急速不断的变化中,日复一日,旧建筑正在消失,取代它们的是现代的建筑。人们担心许多古老的地标很快就会不复存在。”
但是,田子坊这样的老街区,如今也可借助艺术转身。
老腔调的興与衰,终归还是取决于能否与当下握手言和。毕竟,老厂房会告别历史使命,旧观念可能会让位给科学发展。
而永远留在“当下”的,只有属于普通市民的生活。
去年,上生新所的改造者万科,曾公布过一个“中興路一號”的社区规划。静安北的中興路原属老闸北区,也是孕育上海早期繁荣的苏河湾的一部分,离外滩不过两公里。
作为上海多年来出让的少数内环内地块之一,它在市中心的价值不言自明。
但是,苏河湾正由“百年工商传奇”向“城市文化新地标”转变,“中興路一號”也顺应上海的城市更新趋势,做了一个“超级底盘”设计。
在这个设计中,“中興路一號”的部分地面区域,将以公共空间的形式“还”给城市。
 “超级底盘”设计,为社区和邻里带去更多公共空间和设施。
“超级底盘”设计,为社区和邻里带去更多公共空间和设施。
说到底,开发者读懂的,就是上海对市民公共生活空间的重视。
此前,在“中興路一號”附近的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修复工作上,万科同样考量了魔都对空间开放的城市更新需求。
如无意外,这个位于天通庵路190号的百年老址,将成为静安男女们下一个自由拍照的文艺打卡圣地。
放在100年前,静安也曾有过被西方人管治的时期。洋人修建了马路、下水道、跑马场,管理上确实比华界要更现代化。
但这种表面興旺的市民生活,并不属于在同一界内生活的华人。
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就曾撰文提到,黄埔公园在当时明确规定,只有外国人能够入园游玩。
无可否认,当时的社会有当时特殊的历史因素。但即便到了今天,人们也依然需要为种族、性别、地域、贫富等问题而奋斗,文明的实现从来不容易。
与高楼林立的华美相比,上海今天能够对市井生活足够的重视,恰恰体现了这座城市在价值观上更文明和现代化的复興,也是魔都今天一切复興的答案。
 沪上明珠的振興:从繁华到卓越
沪上明珠的振興:从繁华到卓越
一战期间,上海在远东地区就已经颇受瞩目。当时还没有北上广深的说法,上海被拿来对标的往往是伦敦、巴黎和纽约这另外三大魔都。
这个崛起的速度,活脱脱就是一场停不下来的快速逆袭史。
从小渔村到大都会,从通商口岸到东方巴黎,从被迫开埠到改革开放,上海的来路看似既深且长,其实上升曲线也才爬了不到两个世纪。
 不到两个世纪,上海就实现了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興起。
不到两个世纪,上海就实现了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興起。
在当下,上海无论在任何维度上的复興,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有条不紊。
没错,快速的城市更新确实造就了繁华的大上海,但也正因为城市化早早实现,魔都的下一个挑战,已经变成从繁华迈向卓越的振興。
两年前,上海酝酿五年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落地,首次提出要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的2035年目标,对标曾经的对手伦敦和纽约。
在卓越面前,GDP显然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考量。
对于上海来说,这将是一次更精准的城市更新,既慢不下来也无法只顾埋头向前冲。创新、人文、生态三个事关生活興旺的分目标,将在未来被2500万主考官亲身考验。
 上海为“卓越”定下创新、人文、生态三个目标,上海人既是建设者也是主考官。
上海为“卓越”定下创新、人文、生态三个目标,上海人既是建设者也是主考官。
这样的考题,上海也并非第一次遇到。
90年代初,上海就曾为数十万家庭解决过人均不到4平方米的居住矛盾。
最终,那场持续到世纪末的“365万平方米危棚简屋改造”,完成了1200余万平方米的房屋改造,直接受益居民48万户。
在全世界,很多城市都存在旧区与新城之间的割裂,这种“局部興旺”的生活恍如隔世,一百多年的魔都曾经遇到过,当下的上海并没有让昨日重现。
而这,还只是上海从繁华走向卓越的开始。
五年前,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正式揭牌,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片区、张江高科技片区三大片区正式纳入上海自贸试验区。
一方面,三大片区借助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改革试验田肩负了先试先行、敢试敢闯的使命,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步伐率先积累下一步的经验。
成为改革先行者,从来不是想象中那般容易。
但,这就是上海迈向卓越的必经之路。当她的市民能够得到公平的保障,当她欢迎一切公共空间的来客,当她用安居乐业、舒适安稳、物质丰盈构筑起万家興旺的生活,离卓越也就不远了。
 郑时龄:上海为什么要进行城市更新|市政厅
上海的城市更新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国科学院院刊
张鸣:上海租界里的三六九等|腾讯大家
城市更新的历史演进与未来发展——以上海市为例|房地产导刊
郑时龄:上海为什么要进行城市更新|市政厅
上海的城市更新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国科学院院刊
张鸣:上海租界里的三六九等|腾讯大家
城市更新的历史演进与未来发展——以上海市为例|房地产导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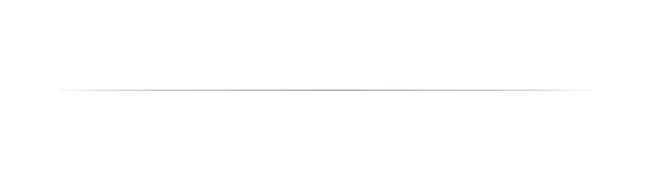
作者 | Slowly 欢迎分享到朋友圈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广告合作请联系微信号:xzk96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