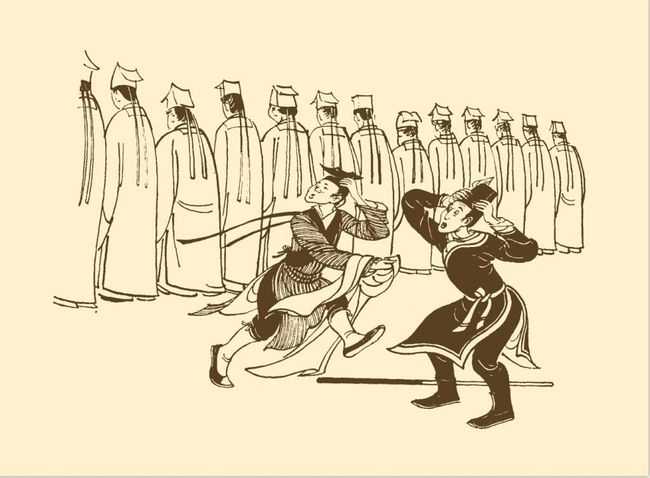- 情绪觉察日记第37天
露露_e800
今天是家庭关系规划师的第二阶最后一天,慧萍老师帮我做了个案,帮我处理了埋在心底好多年的一份恐惧,并给了我深深的力量!这几天出来学习,爸妈过来婆家帮我带小孩,妈妈出于爱帮我收拾东西,并跟我先生和婆婆产生矛盾,妈妈觉得他们没有照顾好我…。今晚回家见到妈妈,我很欣赏她并赞扬她,妈妈说今晚要跟我睡我说好,当我们俩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握着妈妈的手对她说:妈妈这几天辛苦你了,你看你多利害把我们的家收拾得
- 关于沟通这件事,项目经理不需要每次都面对面进行
流程大师兄
很多项目经理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项目中由于事情太多,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召开会议,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有效地管理项目中的利益相关者?当然,不建议电子邮件也不需要开会的话,建议可以采取下面几种方式来形成有效的沟通,这几种方式可以帮助你努力的通过各种办法来保持和各方面的联系。项目经理首先要问自己几个问题,项目中哪些利益相关者是必须要进行沟通的?可以列出项目中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清单,同时也整理出项目中哪些
- 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间关系与区别
ℒℴѵℯ心·动ꦿ໊ོ꫞
人工智能学习深度学习python
一、机器学习概述定义机器学习(MachineLearning,ML)是一种通过数据驱动的方法,利用统计学和计算算法来训练模型,使计算机能够从数据中学习并自动进行预测或决策。机器学习通过分析大量数据样本,识别其中的模式和规律,从而对新的数据进行判断。其核心在于通过训练过程,让模型不断优化和提升其预测准确性。主要类型1.监督学习(SupervisedLearning)监督学习是指在训练数据集中包含输入
- 随笔 | 仙一般的灵气
海思沧海
仙岛今天,我看了你全部,似乎已经进入你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梦幻,还是你仙一般的灵气吸引了我也许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追求,这样才能够符合人生的梦想,生活才能够充满着阳光与快乐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的感叹,是在感叹自己的人生,还是感叹自己一直没有孜孜不倦的追求只感觉虚度了光阴,每天活在自己的梦中,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是在逃避自己,还是在逃避周围的一切有时候我嘲笑自己,嘲笑自己如此的虚无,
- 一百九十四章. 自相矛盾
巨木擎天
唉!就这么一夜,林子感觉就像过了很多天似的,先是回了阳间家里,遇到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儿。特别是小伙伴们,第二次与自己见面时,僵硬的表情和恐怖的气氛,让自己如坐针毡,打从心眼里难受!还有东子,他现在还好吗?有没有被人欺负?护城河里的小鱼小虾们,还都在吗?水不会真的干枯了吧?那对相亲相爱漂亮的太平鸟儿,还好吧!春天了,到了做窝、下蛋、喂养小鸟宝宝的时候了,希望它们都能够平安啊!虽然没有看见家人,也
- UI学习——cell的复用和自定义cell
Magnetic_h
ui学习
目录cell的复用手动(非注册)自动(注册)自定义cellcell的复用在iOS开发中,单元格复用是一种提高表格(UITableView)和集合视图(UICollectionView)滚动性能的技术。当一个UITableViewCell或UICollectionViewCell首次需要显示时,如果没有可复用的单元格,则视图会创建一个新的单元格。一旦这个单元格滚动出屏幕,它就不会被销毁。相反,它被添
- element实现动态路由+面包屑
软件技术NINI
vue案例vue.js前端
el-breadcrumb是ElementUI组件库中的一个面包屑导航组件,它用于显示当前页面的路径,帮助用户快速理解和导航到应用的各个部分。在Vue.js项目中,如果你已经安装了ElementUI,就可以很方便地使用el-breadcrumb组件。以下是一个基本的使用示例:安装ElementUI(如果你还没有安装的话):你可以通过npm或yarn来安装ElementUI。bash复制代码npmi
- 10月|愿你的青春不负梦想-读书笔记-01
Tracy的小书斋
本书的作者是俞敏洪,大家都很熟悉他了吧。俞敏洪老师是我行业的领头羊吧,也是我事业上的偶像。本日摘录他书中第一章中的金句:『一个人如果什么目标都没有,就会浑浑噩噩,感觉生命中缺少能量。能给我们能量的,是对未来的期待。第一件事,我始终为了进步而努力。与其追寻全世界的骏马,不如种植丰美的草原,到时骏马自然会来。第二件事,我始终有阶段性的目标。什么东西能给我能量?答案是对未来的期待。』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便
- 地推话术,如何应对地推过程中家长的拒绝
校师学
相信校长们在做地推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市场专员反馈家长不接单,咨询师反馈难以邀约这些家长上门,校区地推疲软,招生难。为什么?仅从地推层面分析,一方面因为家长受到的信息轰炸越来越多,对信息越来越“免疫”;而另一方面地推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营销话术没有提高,无法应对家长的拒绝,对有意向的家长也不知如何跟进,眼睁睁看着家长走远;对于家长的疑问,更不知道如何有技巧地回答,机会白白流失。由于回答没技巧和专业
- C语言如何定义宏函数?
小九格物
c语言
在C语言中,宏函数是通过预处理器定义的,它在编译之前替换代码中的宏调用。宏函数可以模拟函数的行为,但它们不是真正的函数,因为它们在编译时不会进行类型检查,也不会分配存储空间。宏函数的定义通常使用#define指令,后面跟着宏的名称和参数列表,以及宏展开后的代码。宏函数的定义方式:1.基本宏函数:这是最简单的宏函数形式,它直接定义一个表达式。#defineSQUARE(x)((x)*(x))2.带参
- 小丽成长记(四十三)
玲玲54321
小丽发现,即使她好不容易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下一秒总会有不确定的伤脑筋的事出现,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人生就没有停下的时候,小问题不断出现。不过她今天看的书,她接受了人生就是不确定的,厉害的人就是不断创造确定性,在Ta的领域比别人多的确定性就能让自己脱颖而出,显示价值从而获得的比别人多的利益。正是这样的原因,因为从前修炼自己太少,使得她现在在人生道路上打怪起来困难重重,她似乎永远摆脱不了那种无力感,有种习
- c++ 的iostream 和 c++的stdio的区别和联系
黄卷青灯77
c++算法开发语言iostreamstdio
在C++中,iostream和C语言的stdio.h都是用于处理输入输出的库,但它们在设计、用法和功能上有许多不同。以下是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区别1.编程风格iostream(C++风格):C++标准库中的输入输出流类库,支持面向对象的输入输出操作。典型用法是cin(输入)和cout(输出),使用>操作符来处理数据。更加类型安全,支持用户自定义类型的输入输出。#includeintmain(){in
- Long类型前后端数据不一致
igotyback
前端
响应给前端的数据浏览器控制台中response中看到的Long类型的数据是正常的到前端数据不一致前后端数据类型不匹配是一个常见问题,尤其是当后端使用Java的Long类型(64位)与前端JavaScript的Number类型(最大安全整数为2^53-1,即16位)进行数据交互时,很容易出现精度丢失的问题。这是因为JavaScript中的Number类型无法安全地表示超过16位的整数。为了解决这个问
- mysql禁用远程登录
igotyback
mysql
去mysql库中的user表里,将host都改成localhost之后刷新权限FLUSHPRIVILEGES;
- 绘本讲师训练营【24期】8/21阅读原创《独生小孩》
1784e22615e0
24016-孟娟《独生小孩》图片发自App今天我想分享一个蛮特别的绘本,讲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也是属于这个群体,80后的独生小孩。这是一本中国绘本,作者郭婧,也是一个80厚。全书一百多页,均为铅笔绘制,虽然为黑白色调,但并不显得沉闷。全书没有文字,犹如“默片”,但并不影响读者对该作品的理解,反而显得神秘,梦幻,給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作者在前蝴蝶页这样写到:“我更希望父母和孩子一起分享这本书,使他
- 30天风格练习-DAY2
黄希夷
Day2(重义)在一个周日/一周的最后一天,我来到位于市中心/市区繁华地带的一家购物中心/商场,中心内人很多/熙熙攘攘。我注意到/看见一个独行/孤身一人的年轻女孩/,留着一头引人注目/长过腰际的头发,上身穿一件暗红色/比正红色更深的衣服/穿在身体上的东西。走下扶梯的时候,她摔倒了/跌向地面,在她正要站起来/让身体离开地面的时候,过长/超过一般人长度的头发被支撑身体/躯干的手掌压/按在下面,她赶紧用
- 店群合一模式下的社区团购新发展——结合链动 2+1 模式、AI 智能名片与 S2B2C 商城小程序源码
说私域
人工智能小程序
摘要:本文探讨了店群合一的社区团购平台在当今商业环境中的重要性和优势。通过分析店群合一模式如何将互联网社群与线下终端紧密结合,阐述了链动2+1模式、AI智能名片和S2B2C商城小程序源码在这一模式中的应用价值。这些创新元素的结合为社区团购带来了新的机遇,提升了用户信任感、拓展了营销渠道,并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完美融合。一、引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社区团购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在满足消费者日常需
- 向内而求
陈陈_19b4
10月27日,阴。阅读书目:《次第花开》。作者:希阿荣博堪布,是当今藏传佛家宁玛派最伟大的上师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仁波切颇具影响力的弟子之一。多年以来,赴海内外各地弘扬佛法,以正式授课、现场开示、发表文章等多种方法指导佛学弟子修行佛法。代表作《寂静之道》、《生命这出戏》、《透过佛法看世界》自出版以来一直是佛教类书籍中的畅销书。图片发自App金句:1.佛陀说,一切痛苦的根源在于我们长期以来对自身及外
- 消息中间件有哪些常见类型
xmh-sxh-1314
java
消息中间件根据其设计理念和用途,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常见类型:点对点消息队列(Point-to-PointMessagingQueues):在这种模型中,消息被发送到特定的队列中,消费者从队列中取出并处理消息。队列中的消息只能被一个消费者消费,消费后即被删除。常见的实现包括IBM的MQSeries、RabbitMQ的部分使用场景等。适用于任务分发、负载均衡等场景。发布/订阅消息模型(Pub/Sub
- 三大师传
beca酱
巴尔扎克的作品被誉为“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学大师维克多·雨果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是:“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一个原本寂寂无名的小人物,从地中海的某个海岛上,只身一人来到巴黎,没有朋友,也没有名望。作为一个一文不名的外乡人,凭着赤手空拳赢得了巴黎,征服了整个法兰西,并且赢得了世界。这个人就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
- 水平垂直居中的几种方法(总结)
LJ小番茄
CSS_玄学语言htmljavascript前端csscss3
1.使用flexbox的justify-content和align-items.parent{display:flex;justify-content:center;/*水平居中*/align-items:center;/*垂直居中*/height:100vh;/*需要指定高度*/}2.使用grid的place-items:center.parent{display:grid;place-item
- 我的烦恼
余建梅
我的烦恼。女儿问我:“你给学生布置什么作文题目?”“《我的烦恼》。”“他们都这么大了,你觉得他们还有烦恼吗?”“有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烦恼。”“我不相信,大人是没有烦恼的,如果说一定有的话,你的烦恼和我写作业有关,而且是小烦恼。不像我,天天被你说,有这样的妈妈,烦恼是没完没了。”女儿愤愤不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烦恼,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烦恼多的数不完。想干好工作带好孩子,想孝顺父母又想经营好自
- 活给自己看,笑容才灿烂
听着了么
白岩松说“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心情是自己的。若只是活在别人的眼里、嘴里,便掌握不了让自己开心的主动权。人活着,不是为了活给别人看的,唯有做最真实的自己,活给自己看,笑容才灿烂。诚然,世事纷繁复杂,人人都有一张嘴,管也管不了。永远有人欣赏你,也永远有人批评你,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开心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人生苦短,有太多
- 每日一题——第八十二题
互联网打工人no1
C语言程序设计每日一练c语言
题目:将一个控制台输入的字符串中的所有元音字母复制到另一字符串中#include#include#include#include#defineMAX_INPUT1024boolisVowel(charp);intmain(){charinput[MAX_INPUT];charoutput[MAX_INPUT];printf("请输入一串字符串:\n");fgets(input,sizeof(inp
- WPF中的ComboBox控件几种数据绑定的方式
互联网打工人no1
wpfc#
一、用字典给ItemsSource赋值(此绑定用的地方很多,建议熟练掌握)在XMAL中:在CS文件中privatevoidBindData(){DictionarydicItem=newDictionary();dicItem.add(1,"北京");dicItem.add(2,"上海");dicItem.add(3,"广州");cmb_list.ItemsSource=dicItem;cmb_l
- 情殇——(5)压抑的小木匠放纵了自己。
石疯聊情感故事
木讷的小木匠,其实只是不苟言笑。其实内心深处也是挣扎着,由于性格内敛,不喜形于色,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木讷。其实小木匠情商智商都不低。他为人扎实,非常的务实。他的爱是既深沉又宽容。可是是一个男人,都会对妻子出轨的事儿,不会忘怀!只是压抑在心底,为了某种考量或许是真爱。小木匠对于丽影和别人私奔又重回家庭,表面上并没有,天翻地覆,暴风骤雨,其内心深处也是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再一次酒后,他和一个离家多年
- 2019-12-22-22:30
涓涓1016
今天是冬至,写下我的日更,是因为这两天的学习真的是能量的满满,让我看到了自己,未来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让我看到了这两年这几年的过程中我所接受那些痛苦的来源。一切的根源和痛苦都来自于人生,家庭,而你的原生家庭,你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你这个灵魂在那一刻选择他们作为你的爸爸和妈妈来的,所以你得接受他,你得接纳他,他就是因为他的存在而给你的学习和成长带来这些痛苦,那其实是你必然要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你去接纳的
- 直抒《紫罗兰永恒花园外传》
雷姆的黑色童话
没看过《紫罗兰永恒花园》的我莫名的看完了《紫罗兰永恒花园外传》,又莫名的被故事中的姐妹之情狠狠地感动了的一把。感动何在:困苦中相依为命的姐妹二人被迫分离,用一个人的自由换取另一个人的幸福。之后,虽相隔不知几许依旧心心念念彼此牵挂。这种深深的姐妹情谊就是令我为之动容的所在。贝拉和泰勒分别影片开始,海天之间一个孩童凭栏眺望,手中拿着折旧的信纸。镜头一转,挑灯伏案的薇尔莉特正在打字机前奋笔疾书。这些片段
- Google earth studio 简介
陟彼高冈yu
旅游
GoogleEarthStudio是一个基于Web的动画工具,专为创作使用GoogleEarth数据的动画和视频而设计。它利用了GoogleEarth强大的三维地图和卫星影像数据库,使用户能够轻松地创建逼真的地球动画、航拍视频和动态地图可视化。网址为https://www.google.com/earth/studio/。GoogleEarthStudio是一个基于Web的动画工具,专为创作使用G
- 今天我破防了
sin信仰
今天本来是大年初一,新年的第一天,应该是高高兴兴的一天,但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具体原因很简单,原本计划年后去县城找了一份会计的工作,被公公婆婆否定了,我心里立马就不舒服了,但是当时刚好肚子疼,我去了厕所,等我上完厕所,公公由于喝了酒还在那里和婆婆唠叨个没完。然后我就在心情极度压抑的情况下把午饭吃完的碗筷和锅给刷了。边刷碗筷和锅,边在那里难受,感觉自己在这个家里真的是过的憋屈死了,公婆不让我去上班
- java数字签名三种方式
知了ing
javajdk
以下3钟数字签名都是基于jdk7的
1,RSA
String password="test";
// 1.初始化密钥
KeyPairGenerator keyPairGenerator = KeyPairGenerator.getInstance("RSA");
keyPairGenerator.initialize(51
- Hibernate学习笔记
caoyong
Hibernate
1>、Hibernate是数据访问层框架,是一个ORM(Object Relation Mapping)框架,作者为:Gavin King
2>、搭建Hibernate的开发环境
a>、添加jar包:
aa>、hibernatte开发包中/lib/required/所
- 设计模式之装饰器模式Decorator(结构型)
漂泊一剑客
Decorator
1. 概述
若你从事过面向对象开发,实现给一个类或对象增加行为,使用继承机制,这是所有面向对象语言的一个基本特性。如果已经存在的一个类缺少某些方法,或者须要给方法添加更多的功能(魅力),你也许会仅仅继承这个类来产生一个新类—这建立在额外的代码上。
- 读取磁盘文件txt,并输入String
一炮送你回车库
String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IOException {
String fileContent = readFileContent("d:/aaa.txt");
System.out.println(fileContent);
- js三级联动下拉框
3213213333332132
三级联动
//三级联动
省/直辖市<select id="province"></select>
市/省直辖<select id="city"></select>
县/区 <select id="area"></select>
- erlang之parse_transform编译选项的应用
616050468
parse_transform游戏服务器属性同步abstract_code
最近使用erlang重构了游戏服务器的所有代码,之前看过C++/lua写的服务器引擎代码,引擎实现了玩家属性自动同步给前端和增量更新玩家数据到数据库的功能,这也是现在很多游戏服务器的优化方向,在引擎层面去解决数据同步和数据持久化,数据发生变化了业务层不需要关心怎么去同步给前端。由于游戏过程中玩家每个业务中玩家数据更改的量其实是很少
- JAVA JSON的解析
darkranger
java
// {
// “Total”:“条数”,
// Code: 1,
//
// “PaymentItems”:[
// {
// “PaymentItemID”:”支款单ID”,
// “PaymentCode”:”支款单编号”,
// “PaymentTime”:”支款日期”,
// ”ContractNo”:”合同号”,
//
- POJ-1273-Drainage Ditches
aijuans
ACM_POJ
POJ-1273-Drainage Ditches
http://poj.org/problem?id=1273
基本的最大流,按LRJ的白书写的
#include<iostream>
#include<cstring>
#include<queue>
using namespace std;
#define INF 0x7fffffff
int ma
- 工作流Activiti5表的命名及含义
atongyeye
工作流Activiti
activiti5 - http://activiti.org/designer/update在线插件安装
activiti5一共23张表
Activiti的表都以ACT_开头。 第二部分是表示表的用途的两个字母标识。 用途也和服务的API对应。
ACT_RE_*: 'RE'表示repository。 这个前缀的表包含了流程定义和流程静态资源 (图片,规则,等等)。
A
- android的广播机制和广播的简单使用
百合不是茶
android广播机制广播的注册
Android广播机制简介 在Android中,有一些操作完成以后,会发送广播,比如说发出一条短信,或打出一个电话,如果某个程序接收了这个广播,就会做相应的处理。这个广播跟我们传统意义中的电台广播有些相似之处。之所以叫做广播,就是因为它只负责“说”而不管你“听不听”,也就是不管你接收方如何处理。另外,广播可以被不只一个应用程序所接收,当然也可能不被任何应
- Spring事务传播行为详解
bijian1013
javaspring事务传播行为
在service类前加上@Transactional,声明这个service所有方法需要事务管理。每一个业务方法开始时都会打开一个事务。
Spring默认情况下会对运行期例外(RunTimeException)进行事务回滚。这
- eidtplus operate
征客丶
eidtplus
开启列模式: Alt+C 鼠标选择 OR Alt+鼠标左键拖动
列模式替换或复制内容(多行):
右键-->格式-->填充所选内容-->选择相应操作
OR
Ctrl+Shift+V(复制多行数据,必须行数一致)
-------------------------------------------------------
- 【Kafka一】Kafka入门
bit1129
kafka
这篇文章来自Spark集成Kafka(http://bit1129.iteye.com/blog/2174765),这里把它单独取出来,作为Kafka的入门吧
下载Kafka
http://mirror.bit.edu.cn/apache/kafka/0.8.1.1/kafka_2.10-0.8.1.1.tgz
2.10表示Scala的版本,而0.8.1.1表示Kafka
- Spring 事务实现机制
BlueSkator
spring代理事务
Spring是以代理的方式实现对事务的管理。我们在Action中所使用的Service对象,其实是代理对象的实例,并不是我们所写的Service对象实例。既然是两个不同的对象,那为什么我们在Action中可以象使用Service对象一样的使用代理对象呢?为了说明问题,假设有个Service类叫AService,它的Spring事务代理类为AProxyService,AService实现了一个接口
- bootstrap源码学习与示例:bootstrap-dropdown(转帖)
BreakingBad
bootstrapdropdown
bootstrap-dropdown组件是个烂东西,我读后的整体感觉。
一个下拉开菜单的设计:
<ul class="nav pull-right">
<li id="fat-menu" class="dropdown">
- 读《研磨设计模式》-代码笔记-中介者模式-Mediator
bylijinnan
java设计模式
声明: 本文只为方便我个人查阅和理解,详细的分析以及源代码请移步 原作者的博客http://chjavach.iteye.com/
/*
* 中介者模式(Mediator):用一个中介对象来封装一系列的对象交互。
* 中介者使各对象不需要显式地相互引用,从而使其耦合松散,而且可以独立地改变它们之间的交互。
*
* 在我看来,Mediator模式是把多个对象(
- 常用代码记录
chenjunt3
UIExcelJ#
1、单据设置某行或某字段不能修改
//i是行号,"cash"是字段名称
getBillCardPanelWrapper().getBillCardPanel().getBillModel().setCellEditable(i, "cash", false);
//取得单据表体所有项用以上语句做循环就能设置整行了
getBillC
- 搜索引擎与工作流引擎
comsci
算法工作搜索引擎网络应用
最近在公司做和搜索有关的工作,(只是简单的应用开源工具集成到自己的产品中)工作流系统的进一步设计暂时放在一边了,偶然看到谷歌的研究员吴军写的数学之美系列中的搜索引擎与图论这篇文章中的介绍,我发现这样一个关系(仅仅是猜想)
-----搜索引擎和流程引擎的基础--都是图论,至少像在我在JWFD中引擎算法中用到的是自定义的广度优先
- oracle Health Monitor
daizj
oracleHealth Monitor
About Health Monitor
Beginning with Release 11g, Oracle Database includes a framework called Health Monitor for running diagnostic checks on the database.
About Health Monitor Checks
Health M
- JSON字符串转换为对象
dieslrae
javajson
作为前言,首先是要吐槽一下公司的脑残编译部署方式,web和core分开部署本来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丫居然不把json的包作为基础包而作为web的包,导致了core端不能使用,而且我们的core是可以当web来用的(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所以在core中处理json串就是个问题.没办法,跟编译那帮人也扯不清楚,只有自己写json的解析了.
- C语言学习八结构体,综合应用,学生管理系统
dcj3sjt126com
C语言
实现功能的代码: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malloc.h>
struct Student
{
int age;
float score;
char name[100];
};
int main(void)
{
int len;
struct Student * pArr;
int i,
- vagrant学习笔记
dcj3sjt126com
vagrant
想了解多主机是如何定义和使用的, 所以又学习了一遍vagrant
1. vagrant virtualbox 下载安装
https://www.vagrantup.com/downloads.html
https://www.virtualbox.org/wiki/Downloads
查看安装在命令行输入vagrant
2.
- 14.性能优化-优化-软件配置优化
frank1234
软件配置性能优化
1.Tomcat线程池
修改tomcat的server.xml文件:
<Connector port="8080" protocol="HTTP/1.1" connectionTimeout="20000" redirectPort="8443" maxThreads="1200" m
- 一个不错的shell 脚本教程 入门级
HarborChung
linuxshell
一个不错的shell 脚本教程 入门级
建立一个脚本 Linux中有好多中不同的shell,但是通常我们使用bash (bourne again shell) 进行shell编程,因为bash是免费的并且很容易使用。所以在本文中笔者所提供的脚本都是使用bash(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脚本同样可以在 bash的大姐,bourne shell中运行)。 如同其他语言一样
- Spring4新特性——核心容器的其他改进
jinnianshilongnian
spring动态代理spring4依赖注入
Spring4新特性——泛型限定式依赖注入
Spring4新特性——核心容器的其他改进
Spring4新特性——Web开发的增强
Spring4新特性——集成Bean Validation 1.1(JSR-349)到SpringMVC
Spring4新特性——Groovy Bean定义DSL
Spring4新特性——更好的Java泛型操作API
Spring4新
- Linux设置tomcat开机启动
liuxingguome
tomcatlinux开机自启动
执行命令sudo gedit /etc/init.d/tomcat6
然后把以下英文部分复制过去。(注意第一句#!/bin/sh如果不写,就不是一个shell文件。然后将对应的jdk和tomcat换成你自己的目录就行了。
#!/bin/bash
#
# /etc/rc.d/init.d/tomcat
# init script for tomcat precesses
- 第13章 Ajax进阶(下)
onestopweb
Ajax
index.html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
<html xmlns="http://www.w3.org/
- Troubleshooting Crystal Reports off BW
blueoxygen
BO
http://wiki.sdn.sap.com/wiki/display/BOBJ/Troubleshooting+Crystal+Reports+off+BW#TroubleshootingCrystalReportsoffBW-TracingBOE
Quite useful, especially this part:
SAP BW connectivity
For t
- Java开发熟手该当心的11个错误
tomcat_oracle
javajvm多线程单元测试
#1、不在属性文件或XML文件中外化配置属性。比如,没有把批处理使用的线程数设置成可在属性文件中配置。你的批处理程序无论在DEV环境中,还是UAT(用户验收
测试)环境中,都可以顺畅无阻地运行,但是一旦部署在PROD 上,把它作为多线程程序处理更大的数据集时,就会抛出IOException,原因可能是JDBC驱动版本不同,也可能是#2中讨论的问题。如果线程数目 可以在属性文件中配置,那么使它成为
- 正则表达式大全
yang852220741
html编程正则表达式
今天向大家分享正则表达式大全,它可以大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正则表达式也可以被当作是一门语言,当你学习一门新的编程语言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小的子语言。初看时觉得它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很多时候,你不得不阅读一些教程,或文章来理解这些简单的描述模式。
一、校验数字的表达式
数字:^[0-9]*$
n位的数字:^\d{n}$
至少n位的数字:^\d{n,}$
m-n位的数字:^\d{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