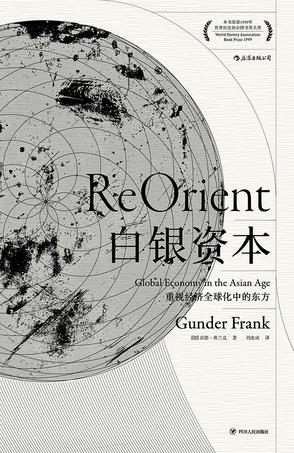随着全球化概念的日益深化,史学界愈发认识到那些以欧洲史为中心、将各地历史简单罗列在一起的历史著作的局限性。全球史作为历史学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一种反应,迅速崛起,并已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在以往的史学著作中,作者们往往从西方本身剖析其崛起与发展,认为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解放了西方人的思想、增强了他们的理性,再加上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方世界带来了大量资本与贸易通道,从而将欧洲推到了世界中心的位置。
然而,本书作者贡德·弗兰克作为全球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却指出,西方的兴起更多的应该归于外界因素:一方面是美洲白银为其买到了一个“亚洲经济列车上的三等厢座位”;另一方面则是白银大量的涌入,导致亚洲经济开始由盛转衰。
其实,本书的书名就足够耐人寻味,你可以将其理解为重新审视东方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亦可以将其看做一种呼吁,希望更多人能在思考全球化时将东方置于中心位置。
亚洲吸引力
对中国读者而言,《白银资本》中所阐述的观点足够振奋。
作者弗兰克在本书开篇就驳斥了“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的理论,提出了“亚洲吸引力”的概念。他指出,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而是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并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之上。
为了证明15-18世纪之间,欧洲在远东的贸易中并不能占主导地位, 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四章中,弗兰克分别考察了近代早期世界几个地区的跨区域贸易活动,比较了世界各地的技术水准、人口增长、商品化、金融体制。数据显示,在这个时期,欧洲人从未拥有或控制超过10%的海上贸易,在南中国海就更少了,在北中国海则根本无权置喙,这与欧洲广大的历史神话恰恰相反。
弗兰克在一系列数据分析后指出:欧洲十字军东征之前,这个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及其动力推动着欧洲人寻求通向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亚洲的途径,这才有了1492年哥伦布航海及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绕非洲航行。
事实上,在新航路开辟之前,东亚以及印度地区就已存在相当繁荣的贸易,而在西方人通过新航路进入亚洲、插手亚洲贸易之后,他们并没有成为新的贸易主导者,而是继续遵从着之前的贸易秩序。
被“捧杀”的中国经济
虽然欧洲人大航海的初衷,仅仅是为了打通与亚洲进行贸易的通道,但它确实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分水岭。
从表面上来看,新航路开辟后,中国经济的确进入了极为繁荣的时代。
哥伦布虽然没有到达印度,但他发现了至关重要的贵金属。有数据显示,从1493年到1800年,世界上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来自拉丁美洲。而这些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欧洲正是用这些钱,买到了一张亚洲经济快车的三等座票。
接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谓欣欣向荣: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因为欧洲人对中国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丝绸、陶瓷和茶叶等的渴望,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然而,有意思的事,随着大量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经济却逐渐衰弱,并最终在19世纪,被欧洲“攫取”了亚洲火车头的位置。
明明赚的盆满钵满,却最终落得“家破人亡”,这是为什么呢?弗兰克把这种现象称为“高度平衡的陷阱”,翻译成当下的流行语就是“捧杀”。
原因就是:充足的资金、良好的社会制度带来了人口的爆发性增长,形成了劳动相对机器极其廉价的局面。在欧洲,情况却完全相反——人少,工资高,再加上可以获得资本,所以对节约人力的技术进行投资既合理又可行。就这样,中国丧失了机器大工业替代传统手工业的最初机会。
亚洲衰弱与欧洲崛起
传统观念里,欧洲是凭借自身力量使自身“现代化”的,继而又慷慨地将这种“现代化”送给了亚洲及其他地区。
然而,弗兰克却认为这只是东西方经济地位互换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亚洲人变得衰弱了,标志性事件就是鸦片贸易使得清朝白银大量外流。《白银资本》第六章——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地)胜出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事实上,直到18世纪,欧洲的制造业依然毫无竞争力。除了白银之外,欧洲人依然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提供给亚洲人。然而,欧洲人在美洲、非洲及亚洲不断汲取和能量的同时,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却在逐渐衰败,最终的结果正如罗兹·墨菲绘制的曲线图所显示——两条曲线在1815年前后交叉,欧洲经济彻底超越了亚洲经济。
弗兰克这部重新定义早期经济思考框架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1998年出版,1999年即获得了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本书在中国的盛行是偶然也是必然。在“立足欧洲,分析世界经济”盛行的大环境中,一部由西方人撰写的把中国称作“中央之国”的著作,其全球化视野本身,就足够让我们热血沸腾。与此同时,本书所展示的开阔宏大的全球视野和整体主义的学书观,也为我们今后解读世界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心态与思路。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