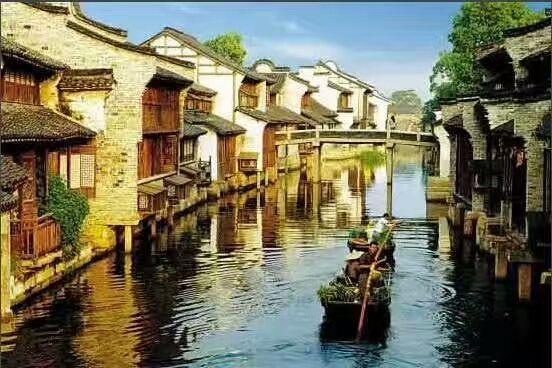1.
在我的记忆里,暮色里的水源山是奇异的。
在村外的山头捋完丛毛,我和爱姑总会在那个小山头,稍站一会,不急着回转。
我差一点忘了说了,在水源山,松树不叫松树,叫丛树。当丛树的叶子老了,老得不能再挂在树枝上,就会落到地上来。它是山村里最好收拾的柴火,山里每个未成年的女孩子,放学回来,都要到山上去捋丛毛。
我和爱姑站在山坡上。天光慢慢暗下去,平日熟悉的村庄,村庄里的房子,鸡和狗呀,还有村庄里的人群渐渐遥远起来,慢慢地看不清楚了。山脚下的房子像是陌生人的房子,村庄像是陌生人的村庄。爱姑的家,在村子东头的祠堂边上,祠堂里长着一棵高大茂盛的柏树,即使是再好的晴天,在我和爱姑喜欢站的这个地方,也只能隐隐看到柏树下爱姑家的屋顶。而每到这个时候,当天光渐渐暗下来了的时候,爱姑的家,是连屋顶也看不到了。
屋顶都快看不到了。但很奇怪,爱姑却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走吧,瘪姑都到家了。瘪姑是她的小弟弟,一个长的有些瘪头瘪脑的小男孩,连说话也瘪声瘪气——这也叫人感到奇怪,在水源山这个地方,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大伙都喜欢在名字后面加一个“姑”字地叫唤。是我记错了吗?大伙在男孩子后面加上的那个“姑”字,可能是水牯牛的那个“牯”。因为这方圆好几里的大小村落,都喜欢把我们水源山叫做“水牛山”的。很奇怪吧?在大伙儿看来,水源山的男人好像都不会讲道理,个个像田里的水牯牛一样地憨、一样地犟。
我和爱姑担着满满一担丛毛打回转。看起来遥远的村庄,越发显得远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迎面碰到割猪草回来的人,大都被我们吓了一跳:我和爱姑两个人,远远地看,就像两团圆乎乎的大黑影,无缘无故,从山坡上骨碌骨碌滚下来。
丛毛是刚从树上掉下来的,很新鲜,要是在太阳底下,会散发出金灿灿的光泽。但这个时候,它们和我们一样,灰蒙蒙什么也看不清,只有一阵阵浓郁的丛树气味,被暮色包裹着,笨头笨脑地盖过来。这气味香得让人脑袋发晕,尤其是经过那一片黑黝黝的茶树林的时候,我和爱姑都熏得有些迷迷糊糊,睁不开眼。
这片茶树林,即使是大白天,我和爱姑也不敢走到里面去。住在我家屋后的美禄哥,我在一个大清早,看到他用一个簸箕装着他没满月的孩子出了门,那个没满月的孩子,一动不动地躺在一个崭新的簸箕里。美禄哥把她带进这片茶树林,就再也没有把她带回来。听说,村子里那些来不及长大的孩子,大多数在这里。
我的脚步不由加快了些,眼前的路看不到尽头。这条小道是这样安静,爱姑急促的喘气声,好像就在我的耳朵根底下,而我自己的呢?在我的记忆了,仿佛消失不见了。
终于到了村后的路口,爱姑还没等我看清楚,往东头一拐弯,一下就走远了。我要经过六婆家,还没到她家伙房,就听到六婆拖长的声音:
“亚姑——”
每次我都很奇怪,屋里的六婆怎么会知道从屋前走过的人是我呢?
我听话地放下肩上那担柴火,走了进去。
六婆正愁眉苦脸地坐在灶膛门口,眯着眼睛:“进灰了,帮我吹吹。”
就着灶火的一点微光,我凑近她的脸,努力地嘟起小嘴,用劲地一口一口吹着。
六婆的眼睛,老得没有睫毛了,被烟火一熏,泪水就关不住。我踮起脚尖站在她面前,灶火因为许久没加柴火,一点红色的微光渐渐弱下去,六婆煨的烤红薯的甜香,在伙房里低低地浮着。
从六婆家出来,记忆里,我还要独自一个人走很长一段路。我家那栋白色的老房子,不在东头,也不在西头,而是在这个村庄的最前头。
还没走到我家门口那方水塘边,在水塘的水和水草的腥气里,我听见母亲在唤我的名字。
天,完完全全黑下来了。
2.
记忆里,水源山的夜晚总有笛声,是运宏哥的笛声。
那清越的笛声乘着慢慢升腾起来的夜雾浮过来,现在想来,真的像是电影里的场景,如在梦中。应该还有月亮吧,大而白、圆,低垂在树梢……也许是我的想像,因为那时的我,多半被母亲赶着上床睡觉了。
但运宏哥的笛声,隔了几十年的光阴,依稀还在耳边。
乡村的夜,记忆中是扁平的,这样一幅夹在天地间薄薄的剪影,因为笛声而变得饱满生动。
油灯下踩缝纫的母亲,听着笛声,常会停下手中的活计,微叹一口气。
我有点奇怪,这笛声多好听,为什么叹气呢?
我出生的那个村落,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水源山,真的是依山傍水。一丛竹林、一座桔园、一片茶山,把小小的村落一分为二,我家房子在老屋场,二伯母家在新屋场,而大伯父家,却在那丛竹林后面,桔园前面,茶山下面。
到茶山捋柴火,会经过大伯父家。经常跑进去,向大伯母讨水喝。远宏哥不在家,他高中毕业,留在公社中学当了一名民办老师,不是礼拜天,难得看到他。
那天口馋,和爱姑、秀姑几个,爬上大伯父家的阁楼,去摘几个长在伸进楼道口枝桠上的桔子。看见运宏哥的房门虚掩着,带着一份孩童对成年男子的好奇,我们推门进去。
房里很整洁,我们上窜下跳,很有几分大闹天空的欣喜,运华哥的竹笛,也被我们抢着乱吹一通,一不小心,就把笛膜弄破了,忙做鸟兽散。
以为闯了很大的祸,过几天碰见远宏哥,我心里老大不自在,又奇怪他怎么提都没提一下。
没过多久,就听说他恋爱了,是个比他小不了几岁的女学生,但差不多已经毕业。
因为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姑娘,运宏哥扛着铺盖从学校回到家,应该是这么一回事吧。我那时太小,只隐隐约约听大人说起过。
他的恋爱没有成功,那个女学生很快由家里人作主,嫁了人。
山村那么小,我却很少看到运宏哥。
只是那笛声,某个月凉如水的夜晚,还是会从那个竹林深处的人家传过来。
过了差不多一年,有人来做媒。女方是祖母家远房亲戚。
那姑娘第一次来访,大伯母特意邀请手艺好的母亲去帮厨。我很好奇相亲的事情,对来相亲的姑娘,更加好奇,便一蹦一跳地跟了过去,躲在门后偷偷地看。是个很好看的姑娘,有一头又黑又粗的浓发,坐在凳子上,跟坐在另一头的运宏哥挺般配。
姑娘走时,家里人要运宏哥送送,运宏哥好像很乐意地去了。过一天回家,没想到那姑娘为送他,也跟着来了。没法,运宏哥只好又转头出门,送姑娘回家。
家里人一边拿这事取笑,一边又觉得很高兴。
但一直到年底,我还是没盼上家里为运宏哥办亲事,我预想的那份热闹,一直没有来……
是运宏哥的缘故吧,他一直含含糊糊。那边姑娘终于灰了心,没多久,另外找了人家。
那年春节,在城里工作的父亲买了成箱成捆的烟花回来。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饭,村里大大小小的年轻人,都挤到我家的院落里来,和我们一起放烟花,但不见运宏哥来。
听母亲说,运宏哥生病了,心病,躺在家里。
我是第一次看到乡村的夜空绽放如此绚丽的花朵,虽然稍纵即逝,但小小的心已经被巨大的喜悦涨得满满的。至于什么是“心病”?运宏哥怎么会得这种病?我虽然有些好奇,但一扭头,就忘了打听。
夜空下那一张张被烟花映红的笑脸,还有我家围墙角落那棵被照亮,灿烂若花开的石榴树,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大人们现在不大提起,那一夜的繁华,如那夜的烟花,只寂寥地盛开在我记忆里最深处。
过完年,在临武工作的父亲,就把我和母亲接了去。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
等我再一次回到水源山,已经是十多年后。
大伯父和大伯母都在,运华哥成家了,生了好几个孩子,一屋子满满的人,就是没看到运宏哥,听说他在镇上搞修理,一直没有成家,性格和行为都有些古怪,不爱搭理人。
伯母一直在叹气,一提起运宏哥就叹气,我看了看屋前的竹林,也不由叹气。
我知道,记忆里那个吹笛子的年轻人,再也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