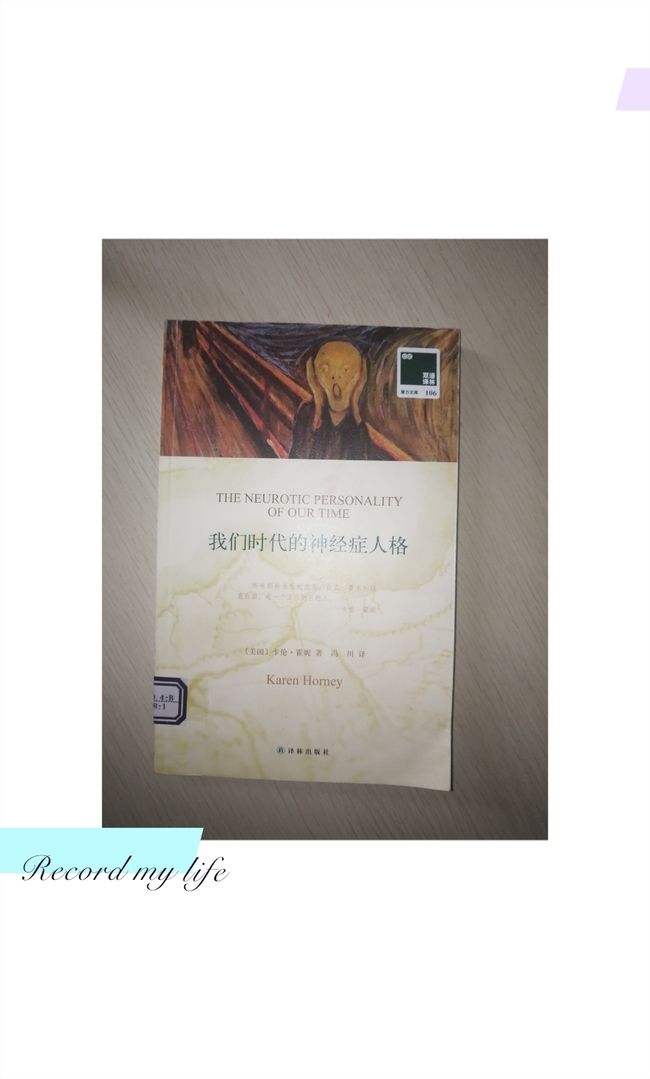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985-1952),医学博士,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义代表人物,继承并发展了弗洛伊德学说。霍妮是社会心理学家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主张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
百度了一下关于神经症的定义:神经官能症又称神经症或精神神经症。是一组精神障碍的总称,包括神经衰弱、强迫症、焦虚症、恐怖症、躯体形式障碍等等,患者深感痛苦且妨碍心理功能或社会功能,但没有任何可证实的器质性病理。
这本书的书名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我们时代表明神经症人格也必然或多或少和我们每个人相关。霍妮打破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弗洛伊德试图把神经症都与性欲结合起来,企图用生物的本能来阐释种种症状。霍妮则从另一个宏观的社会角度来阐述神经症,即文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或者更深层次的阐述文化之困境而导致神经症。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相对而言也是我们文化的副产品。
正常与不正常如何界定,它们的边界在哪里,即所说边缘化、异化、非社会化。这样的理解都得在一个宏观的文化环境下才能加以阐释,因为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被称为不正常的人到了另外的文化环境之下就是正常的,凭借了文化来界定大部分正常与不正常。
霍妮这里所谓的神经症病人,是指那些行为、情感、思维方式都显得不正常的人,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却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强加于社会成员身上的行为标准和情感标准,而这些标准却因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
我们每个人在出生之后就在被动或主动的融入到这个社会环境之下,受着文化的熏陶,身边的人的感染,学习礼仪、生活方式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而成为一个社会化的人。而那些没有竭力融入社会洪流之中的人常常被冠以“这个人不正常吧,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排挤着那些我们所认为的异化的人。
又或者一个人社会化了,但条条条框框下的文化也存在着同样的冲突。就像我们被教导要竞争和成功,却又要仁爱和谦卑;我们各种需要所受到的刺激和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实际受到的挫折。正如广告和各种宣传却并非是每个人的经济和能力所能承受的,而且感受是属于每个个体的,那些虚幻的色彩很容易让人陷入矛盾之中;以及个人自由和他实际所受到的一切局限之间的冲突。
这就需要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去平衡内心交织的矛盾与冲突。在我们从小的教育之下,家长和老师给予我们的都是正面的教育,积极向上、谦卑、成功等等。这样教育或多或少的缺陷就是不会去把海底暗流涌动的一面展示出来,因为有光的地方一定有阴影。似乎像美好的童话世界,这样就造成当我们面对失败和挫折变很容易变的无从所适,面对社会的另一面时显得惊讶与错愕。当这些冲突与焦虑无处安放时,就演变成了神经症。
剔除神经症通常具有的虚幻晦涩的性质,同一文化中正常的人也同样面对,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患有神经症的人大多在童年时期经历了不公平、压迫等等,因此在长大之后面对这些冲突时显得更加敏感和难以应对,而把自己困于桎梏之中 ,对生活失去了方向感。
一般心理学所认为的患有神经症是因为童年的阴影没见解开,认为要从源头来解决心理问题;而霍妮则认为发现一种性格或态度的渊源并不足以解释这种态度,更重要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这种态度。
患神经症的人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的性质就是内心缺乏安全感,表现为过度依赖于他人,内心的自卑感和不足感;自我抑制的倾向;心理紊乱,表现为攻击倾向,对任何事物或人有很大的敌意,内心过度的感到不公和欺压;性方面的怪癖。
一个人的性格和态度并不一定会患神经症,但它却给患神经症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让其肆意生长。如果一个人所秉持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和现实世界不相融和,缺乏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内心冲突,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和错的,可以理解为价值观的崩塌。如果与此同时再加上现实生活当中的失败和各种生活压力就会产生焦虑,焦虑便作为一种动力推动冲突,随之而来冲突就会加剧,两者相互促进使人陷入到桎梏之中而找不到出口。
霍妮讲到了如何区分焦虑和恐惧,焦虑是隐而不露和主观内在对幻想的危险之反应,恐惧则是显而易见的对客观存在的危险之反应。即焦虑本质上是一种涉及主观因素的恐惧。焦虑更多的是想象的危险但,却是一个和处于恐惧之中的遭受同样大的内心感受处境。这也就可以理解一个患有神经症的人所承受的痛苦之大吧。
有时候觉得对于一个没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人,你和他讲多少心理学都不以为然,这是我们的文化所带给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关注点更多的是外在的成功、名望,忽略了心里的感受和需要。而当一个人内心的冲突无法平衡,在愈演愈烈的幻想中游走时,我们才愿意拿起心理学去剖析自己,才转而认为心理学显得至关重要。
我们也可能对自己的焦虑一无所知,我们对待焦虑的态度往往处于完全的无能为力,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软弱和怯懦;我们的文化总是强调理性思维和理智行为,贬低非理性的情感,甚至认为其是低级的,以至于不能容忍非理性和异己力量来控制自己。但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情感却占据了大部分;焦虑是一种警报,因为我们拒绝审视自己而出了问题。
在我们的文化中逃避焦虑的方式有焦虑合理化,通过逃避责任、借口和理由;通过根本否认焦虑的存在,进而转化为生理上的躯体症状,比如生病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麻醉自己,最简单直接的就是酒精和药物 另外一种是通过沉迷于某种活动,比如工作等以使焦虑借此得以得到缓解;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处境、思想和感受。
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都不是引起我们焦虑的原因,焦虑的产生不是由于对冲动的恐惧而产生,更多的是对其的压抑。一个人的神经症愈严重,他的种种抑制倾向也就愈微妙和巨大,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愈深不可测。
对恐惧的压抑随之而来的是敌意的产生,类似于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否则我就会失去爱;我必须压抑敌意,因为如果我感到自己有敌对心理,我就是个坏孩子。
对于患神经症的在敏感、潜在的敌意以及苛刻的要求之外对爱的需要是也贪婪的。真正的爱是一种感受,给人以力量。而病态的爱只是为获取安全感,因为产生这种爱的情境是为了获得安全感,其本身妨碍了这种需要的满足。换句话说,神经症患者愈想得到的愈得不到满足。
通常神经症患者对抗焦虑的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爱,统治与支配他人来获得安全感;另外的则大多是因为无法通过获得爱而得到安全感,进而通过坚守个人的位置,如获得声望、权利、财富。
神经症病人还存在着病态的竞争,无时无刻且无条件的拿自己与他人衡量;想要更大的成就感,使自己显得独一无二;心中隐藏的敌意,即他那种“只有我才应该是最美丽、最能干、最成功的人”的态度。
他总是在追求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一方面他极具攻击性地追求“唯我独尊”,另一方面,他又极其渴望被一切人所爱,这种夹杂在野心与爱之间的处境,造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冲突。
为了获得安全感会尽量避免引人注目,同时也必然会导致生活的贫乏和潜能的扭曲。因为除非环境有利,不然任何幸福、成就的获得都要冒一定的风险和努力奋斗。
病态的犯罪感也是常见的,巨大的夸张到纯粹的幻想,那些看上去仿佛是犯罪感的现象,绝大部分只是焦虑的表现或者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御机制,而非真正的犯罪感。
人总是善于逃避和自欺的,有时候这种欺骗都逃到了无意识领域,以至于连自己都发现不了。
霍妮讲到一个以就事论事的态度解释其自身困境的神经症病人和一个企图以戏剧性的效果展示自身困境以唤起他人怜悯的神经症病人两者之间是有巨大区别的。而心理治疗的任务只能是努力去发现某些处境对神经症病人所具有的意义。而不能说去全权帮助一个人走出困境,所有想要走出来的人都有想要突破和走出来的欲望,不然别人的帮助就显得多余和徒劳。可能还是那句“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
也许读这本书更大的意义在于多了一种可能发现自身的更多的未解之谜,甚至是意识领域之外的东西;我们的文化刻在我们身上的烙印以及我们的文化所面临的困境。而对于每个个体而言,无论上天给予我们好的坏的,都能欣然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