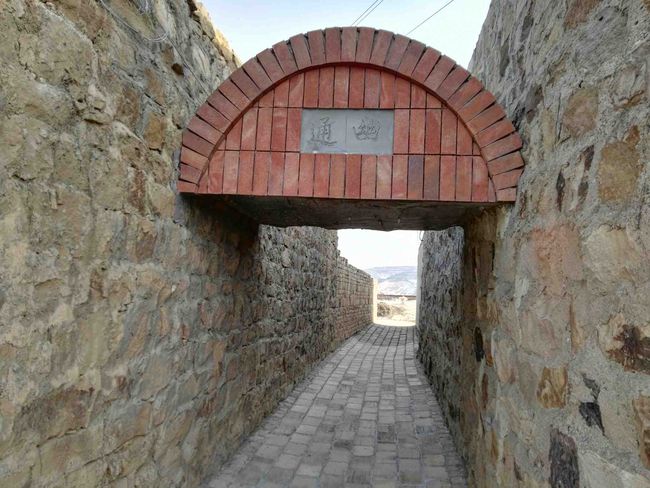- 铭刻于星(四十二)
随风至
69夜晚,绍敏同学做完功课后,看了眼房外,没听到动静才敢从书包的夹层里拿出那个心形纸团。折痕压得很深,都有些旧了,想来是已经写好很久了。绍敏同学慢慢地、轻轻地捏开折叠处,待到全部拆开后,又反复抚平纸张,然后仔细地一字字默看。只是开头的三个字是第一次看到,让她心漏跳了几拍。“亲爱的绍敏:从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但是我一直不敢说,怕影响你学习。六年级的时候听说有人跟你表白,你接受了,我很难过,但
- 底层逆袭到底有多难,不甘平凡的你准备好了吗?让吴起给你说说
造命者说
底层逆袭到底有多难,不甘平凡的你准备好了吗?让吴起给你说说我叫吴起,生于公元前440年的战国初期,正是群雄并起、天下纷争不断的时候。后人说我是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是兵家代表人物。评价我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因变法得罪守旧贵族,被人乱箭射死。我出生在卫国一个“家累万金”的富有家庭,从年轻时候起就不甘平凡
- 想家
爆米花机
也许不同于大家对家乡的思念,我对家乡甚至是疯狂的不舍。还未踏出车站就感觉到幸福,我享受这里的夕阳、这里的浓烈柴火味、这里每一口家常菜。我是宅女,我贪恋家的安逸。刚刚踏出大学校门,初出茅庐,无法适应每年只能国庆和春节回家。我焦虑、失眠、无端发脾气,是无法适应工作的节奏,是无法接受我将一步步离开家乡的事实。我不想承认自己胸无大志,选择再次踏上征程。图片发自App
- 2021年12月19日,春蕾教育集团团建活动感受——黄晓丹
黄错错加油
感受:1.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游戏环节让我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得到了锻炼,也增长了不少知识。2.游戏过程中,我们贡献的是个人力量,展现的是团队的力量。它磨合的往往不止是工作的熟悉,更是观念上契合度的贴近。3.这和工作是一样的道理。在各自的岗位上,每个人摆正自己的位置、各司其职充分发挥才能,并团结一致劲往一处使,才能实现最大的成功。新知:1.团队精神需要不断地创新。过去,人们把创新看作是冒风险,现在人们
- 《投行人生》读书笔记
小蘑菇的树洞
《投行人生》----作者詹姆斯-A-朗德摩根斯坦利副主席40年的职业洞见-很短小精悍的篇幅,比较适合初入职场的新人。第一部分成功的职业生涯需要规划1.情商归为适应能力分享与协作同理心适应能力,更多的是自我意识,你有能力识别自己的情并分辨这些情绪如何影响你的思想和行为。2.对于初入职场的人的建议,细节,截止日期和数据很重要截止日期,一种有效的方法是请老板为你所有的任务进行优先级排序。和老板喝咖啡的好
- 《策划经理回忆录之二》
路基雅虎
话说三年变六年,飘了,飘了……眨眼,2013年5月,老吴回到了他的家乡——油城从新开启他的工作幻想症生涯。很庆幸,这是一家很有追求,同时敢于尝试的,且实力不容低调的新星房企——金源置业(前身泰源置业)更值得庆幸的是第一个盘就是油城十路的标杆之一:金源盛世。2013年5月,到2015年11月,两年的陪伴,迎来了一场大爆发。2000个筹,5万/筹,直接回笼1个亿!!!这……让我开始认真审视这座看似五线
- 扫地机类清洁产品之直流无刷电机控制
悟空胆好小
清洁服务机器人单片机人工智能
扫地机类清洁产品之直流无刷电机控制1.1前言扫地机产品有很多的电机控制,滚刷电机1个,边刷电机1-2个,清水泵电机,风机一个,部分中高端产品支持抹布功能,也就是存在抹布盘电机,还有追觅科沃斯石头等边刷抬升电机,滚刷抬升电机等的,这些电机有直流有刷电机,直接无刷电机,步进电机,电磁阀,挪动泵等不同类型。电机的原理,驱动控制方式也不行。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几个文章会作个专题分析分享。直流有刷电机会自动持续
- 抖音乐买买怎么加入赚钱?赚钱方法是什么
测评君高省
你会在抖音买东西吗?如果会,那么一定要免费注册一个乐买买,抖音直播间,橱窗,小视频里的小黄车买东西都可以返佣金!省下来都是自己的,分享还可以赚钱乐买买是好省旗下的抖音返佣平台,乐买买分析社交电商的价值,乐买买属于今年难得的副业项目风口机会,2019年错过做好省的搞钱的黄金时期,那么2022年千万别再错过乐买买至于我为何转到高省呢?当然是高省APP佣金更高,模式更好,终端用户不流失。【高省】是一个自
- 2018-07-23-催眠日作业-#不一样的31天#-66小鹿
小鹿_33
预言日:人总是在逃避命运的路上,与之不期而遇。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名词,叫做自证预言;经济学上也有一个很著名的定律叫做,墨菲定律;在灵修派上,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法则,叫做吸引力法则。这3个领域的词,虽然看起来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在告诉人们一个现象:你越担心什么,就越有可能会发生什么。同样的道理,你越想得到什么,就应该要积极地去创造什么。无论是自证预言,墨菲定律还是吸引力法则,对人都有正反2个维度的影响
- 《大清方方案》| 第二话
谁佐清欢
和珅究竟说了些什么?竟能令堂堂九五之尊龙颜失色!此处暂且按下不表;单说这位乾隆皇帝,果真不愧是康熙从小带过的,一旦决定了要做的事,便杀伐决断毫不含糊。他当即亲自拟旨,着令和珅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处理方方事件,并钦赐尚方宝剑,遇急则三品以下官员可先斩后奏。和珅身负皇上重托,岂敢有半点怠慢,当夜即率领相关人等,马不停蹄杀奔江汉。这一路上,和珅的几位幕僚一直在商讨方方事件的处置方案。有位年轻幕僚建议快刀
- 《庄子.达生9》
钱江潮369
【原文】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
- 2019-12-22-22:30
涓涓1016
今天是冬至,写下我的日更,是因为这两天的学习真的是能量的满满,让我看到了自己,未来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让我看到了这两年这几年的过程中我所接受那些痛苦的来源。一切的根源和痛苦都来自于人生,家庭,而你的原生家庭,你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你这个灵魂在那一刻选择他们作为你的爸爸和妈妈来的,所以你得接受他,你得接纳他,他就是因为他的存在而给你的学习和成长带来这些痛苦,那其实是你必然要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你去接纳的
- 谁家酒器最绝唱,藏在酒厂人未知?景阳冈酒厂先秦藏品大揭秘
李虓酒评论
文/王赛时中国的酒器酒具历史久远,举世闻名。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到世界各国的大型博物馆,都以能够收藏中国古代酒具而夸耀。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山东阳谷景阳冈酒厂,默默地收藏了两千件中国酒器。这些酒器,就封藏在景阳冈的酒道馆里。其中有一些青铜酒器,一睡就是三、四千年,堪称无声国宝,堪作无字史书!今天,我将引领诸位首先窥视一下景阳冈酒道馆的9件先秦藏品,你自己来说震撼不震撼。提示:这只是景
- 今又重阳
芮峻
今又重阳图片发自App白露成霜菊花黄,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登高远望,君不见,那来时路上少年,青丝已染雪霜。落日一点一点西坠,谁有力量,托住使其回往。转眼缺了大半,又能怎样?江天两茫茫。给我一壶烈酒,我要敬那斜阳,看谁先醉?笑指西天红了一片,借点酒力,老夫聊发一次少年狂。老严.2019年重阳节.杭州
- 郎朗大婚娶公主:所有光环的背后,都是十年如一日的自律
简小尘
近日,关于郎朗大婚的新闻上了热搜,看了新娘的照片,既有天使般的面容,更有魔鬼般的身材,关键是人家还身世好,又有才华,这真的是让所有男人羡慕嫉妒恨哪。有些人不禁会想,“凭什么郎朗的人生就象开挂了一样,可我却每天都活得这么狼狈!”其实,每个开挂的人生背后,都是苦行僧般的自律。01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练琴不能只靠兴趣,更需要自律!我们先来看一下朗朗在小时候的作息时间表:早晨5:45起床,练琴1小时。中午
- 《中华小厨师》单行VS爱藏:姜是老的辣,书是新的好
cicoky
《汉书·郦食其传》有曰:“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吃饱饭是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而吃好饭却是每一个人的最终追求。于是,厨师这一职业孕育而生,其渊源之久,甚至可追溯到4000年前的奴隶时代。职业本身无贵贱,但职业能力却有高低之分。所以一家餐馆生意好不好,厨师的水平决定一切,而站在所有厨师顶端的就被称之为“特级厨师”。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个关于“特级厨师刘昴星”的故事。连载历程1995年第4
- 直返最高等级与直返APP:无需邀请码的返利新体验
古楼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商的兴起,直返模式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通过购买产品或服务,获得一定的返利,并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其中,直返最高等级和直返APP是直返模式中的重要概念和工具。本文将详细介绍直返最高等级的概念、直返APP的使用以及与邀请码的关系。【高省】APP(高佣金领导者)是一个自用省钱佣金高,分享推广赚钱多的平台,百度有几百万篇报道,运行三年,稳定可靠。高省APP,
- 高端密码学院笔记285
柚子_b4b4
高端幸福密码学院(高级班)幸福使者:李华第(598)期《幸福》之回归内在深层生命原动力基础篇——揭秘“激励”成长的喜悦心理案例分析主讲:刘莉一,知识扩充:成功=艰苦劳动+正确方法+少说空话。贪图省力的船夫,目标永远下游。智者的梦再美,也不如愚人实干的脚印。幸福早课堂2020.10.16星期五一笔记:1,重视和珍惜的前提是知道它的价值非常重要,当你珍惜了,你就真正定下来,真正的学到身上。2,大家需要
- 2020-04-12每天三百字之连接与替代
冷眼看潮
不知道是不是好为人师,有时候还真想和别人分享一下我对某些现象的看法或者解释。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就是不断连接与替代的过程。人类发现了火并应用火以后,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兽般的原始生活(火烧、烹饪替代了生食)人类用石器代替了完全手工,工具的使用使人类进步一大步。类似这样的替代还有很多,随着科技的发展,有更多的原始的事物被替代,代之以更高效、更先进的技术。在近现代,汽车替代了马车,高速公路和铁路
- 东南林氏之九牧林候选父系
祖缘树TheYtree
渊源介绍东晋初年晋安林始祖林禄公入闽,传十世隋右丞林茂,由晋安迁居莆田北螺村。又五世而至林万宠,唐开元间任高平太守,生三子:韬、披、昌。韬公之孙攒,唐德宗立双阙以旌表其孝,时号"阙下林家"。昌公字茂吉,乃万宠公第三子,官兵部司马,配宋氏,生一子名萍。萍于唐贞元间明经及第,官沣洲司马(后追赠中宪大夫)。唐太和年间归隐后,迁居仙游游洋,世称“游洋林”;其后裔居游洋后迁移漳州漳浦路下,由路下林第四房平和
- 春季养肝正当时
dxn悟
重温快乐2023年2月4日立春。春天来了,春暖花开,小鸟欢唱,那在这样的季节我们如何养肝呢?自然界的春季对应中医五行的木,人体五脏肝属木,“木曰曲直”,是以树干曲曲直直地向上、向外伸长舒展的生发姿态,来形容具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特征的食物及现象。根据中医天人相应的理念,肝五行属木,喜条达,主疏泄,与春天相应,所以春天最适合养肝。养肝首先要少生气,因为肝喜条达恶抑郁。人体五志肝为怒,生气发怒最
- 大伟说成语之唉声叹气
求索大伟
*大伟说成语*【唉声叹气】叹气:因心里不痛快或不如意而吐出长气,发出声音。因为痛苦、憋闷或感伤而发出叹息的声音。【大伟说】情绪外露,非人类所特有,动物亦有情绪,悲哀和欢乐所表示的情绪亦是不一样的,会嗷嗷大叫也会低吟痛哭。不同的是,人类的情绪更复杂,更多样,更丰富。唉声叹气,可以说是最基础的情绪,因为无奈而举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如何化解,只有独自一人慢慢承受,长吁短叹不知如何是好,其实是无能无力的表现
- 2022现在哪个打车软件比较好用又便宜 实惠的打车软件合集
高省APP珊珊
这是一个信息高速传播的社会。信息可以通过手机,微信,自媒体,抖音等方式进行传播。但同时这也是一个交通四通发达的社会。高省APP,是2022年推出的平台,0投资,0风险、高省APP佣金更高,模式更好,终端用户不流失。【高省】是一个自用省钱佣金高,分享推广赚钱多的平台,百度有几百万篇报道,也期待你的加入。珊珊导师,高省邀请码777777,注册送2皇冠会员,送万元推广大礼包,教你如何1年做到百万团队。高
- libyuv之linux编译
jaronho
Linuxlinux运维服务器
文章目录一、下载源码二、编译源码三、注意事项1、银河麒麟系统(aarch64)(1)解决armv8-a+dotprod+i8mm指令集支持问题(2)解决armv9-a+sve2指令集支持问题一、下载源码到GitHub网站下载https://github.com/lemenkov/libyuv源码,或者用直接用git克隆到本地,如:gitclonehttps://github.com/lemenko
- 梁文道《尽头:怎样是好的阅读和书写》 片段
白夜书摘
1、写小说的人,有时会强烈地感到一种现实的召唤,想去面对和回应现实。这时他们会觉得自己正站在时代中心,就像黑格尔说的,要把时代精神掌握在自己的小说(不是哲学)里面。但是这也很危险,当一个作家像一个时代那样书写,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2、文字是远比语言大块而且湿冷的木头,又距离我们内心的火花稍远,不容易瞬间点燃起来,这处隙缝,给了我们回身的余地,可以再多看一下想一下设身处地一下;人类过往这最后五千年,
- 似乎,发生了很多事情
阿皮Ponder
似乎,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今天,我跟夫人陪着孩子走进来幼儿园,人生头一回以孩子家长的身份参加了小小的班级家长会。在幼儿园,遇见老同学。从2017年开始失联,因为对方遇到了一些事情,跟大家都失去了联系,今日再见面,分外激动,他拉着我一直聊,一直聊。感谢我们的孩子。孩子有点咳嗽,去医院做了检查。叔叔家的两个妹妹开始了高中生活,新的开始。过去看望,遇到一位老师,很是面熟。咨询之下,果然,曾经初中母校的老
- 百善孝为先
杜友顺
2018年11月29日天气~晴星期四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福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家,永远是儿女们幸福温暖的港湾,那里有我们日夜思念的父母,有着彼此的牵挂,无论走到哪里,家永远是避风雨的港湾。今天没事,和媳妇回了趟老家,看看父母,回到家,房间里不算凌乱,可是细心的我发现有的地方已经沾满了灰尘,桌子上父亲不离手的烟灰缸也弹满了烟灰。几个马上就要腐烂掉的水果蔫耷的搭拉着脑袋躺在了
- 2022-11-17
无奇君
又去了一次社康,这次是急性支气管炎……太难了。半夜就猛咳,天天咳醒,还好他戴海绵耳塞睡吵不到他,要不然对他来说也是种煎熬。一累也会猛咳,希望这次是最后一次吃药,吃完就好。又想把头发剪短了,顺便染个色。可是刚刚去看人家还没开门,不是休息日老板好佛系。理发店是个夫妻店,一年多前刚搬来的时候老板还没对象呢,当时聊天老板就说希望能找个对象一起两个人守着店都比上班强。不久后再去他已经有对象了,而且在店里帮忙
- pyecharts——绘制柱形图折线图
2224070247
信息可视化pythonjava数据可视化
一、pyecharts概述自2013年6月百度EFE(ExcellentFrontEnd)数据可视化团队研发的ECharts1.0发布到GitHub网站以来,ECharts一直备受业界权威的关注并获得广泛好评,成为目前成熟且流行的数据可视化图表工具,被应用到诸多数据可视化的开发领域。Python作为数据分析领域最受欢迎的语言,也加入ECharts的使用行列,并研发出方便Python开发者使用的数据
- 冬天短期的暴利小生意有哪些?那些小生意适合新手做?
一起高省
短期生意不失为创业的一个商机,不过短期生意的商机是转瞬即逝的,而且这类生意也很难作为长期的生意去做,那冬天短期暴利小生意查看更多关于短期暴利小生意的文章有哪些呢?给大家先推荐一个2023年风口项目吧,真很不错的项目,全程零投资,当做副业来做真的很稳定,不管你什么阶层的人,或多或少都网购吧?你们知道网购是可以拿提成,拿返利,拿分佣的吗?你们知道很多优惠券群里面,天天群主和管理发一些商品吗?他们其实在
- 辗转相处求最大公约数
沐刃青蛟
C++漏洞
无言面对”江东父老“了,接触编程一年了,今天发现还不会辗转相除法求最大公约数。惭愧惭愧!
为此,总结一下以方便日后忘了好查找。
1.输入要比较的两个数a,b
忽略:2.比较大小(因为后面要的是大的数对小的数做%操作)
3.辗转相除(用循环不停的取余,如a%b,直至b=0)
4.最后的a为两数的最大公约数
&
- F5负载均衡会话保持技术及原理技术白皮书
bijian1013
F5负载均衡
一.什么是会话保持? 在大多数电子商务的应用系统或者需要进行用户身份认证的在线系统中,一个客户与服务器经常经过好几次的交互过程才能完成一笔交易或者是一个请求的完成。由于这几次交互过程是密切相关的,服务器在进行这些交互过程的某一个交互步骤时,往往需要了解上一次交互过程的处理结果,或者上几步的交互过程结果,服务器进行下
- Object.equals方法:重载还是覆盖
Cwind
javagenericsoverrideoverload
本文译自StackOverflow上对此问题的讨论。
原问题链接
在阅读Joshua Bloch的《Effective Java(第二版)》第8条“覆盖equals时请遵守通用约定”时对如下论述有疑问:
“不要将equals声明中的Object对象替换为其他的类型。程序员编写出下面这样的equals方法并不鲜见,这会使程序员花上数个小时都搞不清它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
pu
- 初始线程
15700786134
暑假学习的第一课是讲线程,任务是是界面上的一条线运动起来。
既然是在界面上,那必定得先有一个界面,所以第一步就是,自己的类继承JAVA中的JFrame,在新建的类中写一个界面,代码如下:
public class ShapeFr
- Linux的tcpdump
被触发
tcpdump
用简单的话来定义tcpdump,就是:dump the traffic on a network,根据使用者的定义对网络上的数据包进行截获的包分析工具。 tcpdump可以将网络中传送的数据包的“头”完全截获下来提供分析。它支 持针对网络层、协议、主机、网络或端口的过滤,并提供and、or、not等逻辑语句来帮助你去掉无用的信息。
实用命令实例
默认启动
tcpdump
普通情况下,直
- 安卓程序listview优化后还是卡顿
肆无忌惮_
ListView
最近用eclipse开发一个安卓app,listview使用baseadapter,里面有一个ImageView和两个TextView。使用了Holder内部类进行优化了还是很卡顿。后来发现是图片资源的问题。把一张分辨率高的图片放在了drawable-mdpi文件夹下,当我在每个item中显示,他都要进行缩放,导致很卡顿。解决办法是把这个高分辨率图片放到drawable-xxhdpi下。
&nb
- 扩展easyUI tab控件,添加加载遮罩效果
知了ing
jquery
(function () {
$.extend($.fn.tabs.methods, {
//显示遮罩
loading: function (jq, msg) {
return jq.each(function () {
var panel = $(this).tabs(&
- gradle上传jar到nexus
矮蛋蛋
gradle
原文地址:
https://docs.gradle.org/current/userguide/maven_plugin.html
configurations {
deployerJars
}
dependencies {
deployerJars "org.apache.maven.wagon
- 千万条数据外网导入数据库的解决方案。
alleni123
sqlmysql
从某网上爬了数千万的数据,存在文本中。
然后要导入mysql数据库。
悲剧的是数据库和我存数据的服务器不在一个内网里面。。
ping了一下, 19ms的延迟。
于是下面的代码是没用的。
ps = con.prepareStatement(sql);
ps.setString(1, info.getYear())............;
ps.exec
- JAVA IO InputStreamReader和OutputStreamReader
百合不是茶
JAVA.io操作 字符流
这是第三篇关于java.io的文章了,从开始对io的不了解-->熟悉--->模糊,是这几天来对文件操作中最大的感受,本来自己认为的熟悉了的,刚刚在回想起前面学的好像又不是很清晰了,模糊对我现在或许是最好的鼓励 我会更加的去学 加油!:
JAVA的API提供了另外一种数据保存途径,使用字符流来保存的,字符流只能保存字符形式的流
字节流和字符的难点:a,怎么将读到的数据
- MO、MT解读
bijian1013
GSM
MO= Mobile originate,上行,即用户上发给SP的信息。MT= Mobile Terminate,下行,即SP端下发给用户的信息;
上行:mo提交短信到短信中心下行:mt短信中心向特定的用户转发短信,你的短信是这样的,你所提交的短信,投递的地址是短信中心。短信中心收到你的短信后,存储转发,转发的时候就会根据你填写的接收方号码寻找路由,下发。在彩信领域是一样的道理。下行业务:由SP
- 五个JavaScript基础问题
bijian1013
JavaScriptcallapplythisHoisting
下面是五个关于前端相关的基础问题,但却很能体现JavaScript的基本功底。
问题1:Scope作用范围
考虑下面的代码:
(function() {
var a = b = 5;
})();
console.log(b);
什么会被打印在控制台上?
回答:
上面的代码会打印 5。
&nbs
- 【Thrift二】Thrift Hello World
bit1129
Hello world
本篇,不考虑细节问题和为什么,先照葫芦画瓢写一个Thrift版本的Hello World,了解Thrift RPC服务开发的基本流程
1. 在Intellij中创建一个Maven模块,加入对Thrift的依赖,同时还要加上slf4j依赖,如果不加slf4j依赖,在后面启动Thrift Server时会报错
<dependency>
- 【Avro一】Avro入门
bit1129
入门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总结下基于Avro Schema代码生成,然后进行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开发的基本流程。需要指出的是,Avro并不要求一定得根据Schema文件生成代码,这对于动态类型语言很有用。
1. 添加Maven依赖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roj
- 安装nginx+ngx_lua支持WAF防护功能
ronin47
需要的软件:LuaJIT-2.0.0.tar.gz nginx-1.4.4.tar.gz &nb
- java-5.查找最小的K个元素-使用最大堆
bylijinnan
java
import java.util.Arrays;
import java.util.Random;
public class MinKElement {
/**
* 5.最小的K个元素
* I would like to use MaxHeap.
* using QuickSort is also OK
*/
public static void
- TCP的TIME-WAIT
bylijinnan
socket
原文连接:
http://vincent.bernat.im/en/blog/2014-tcp-time-wait-state-linux.html
以下为对原文的阅读笔记
说明:
主动关闭的一方称为local end,被动关闭的一方称为remote end
本地IP、本地端口、远端IP、远端端口这一“四元组”称为quadruplet,也称为socket
1、TIME_WA
- jquery ajax 序列化表单
coder_xpf
Jquery ajax 序列化
checkbox 如果不设定值,默认选中值为on;设定值之后,选中则为设定的值
<input type="checkbox" name="favor" id="favor" checked="checked"/>
$("#favor&quo
- Apache集群乱码和最高并发控制
cuisuqiang
apachetomcat并发集群乱码
都知道如果使用Http访问,那么在Connector中增加URIEncoding即可,其实使用AJP时也一样,增加useBodyEncodingForURI和URIEncoding即可。
最大连接数也是一样的,增加maxThreads属性即可,如下,配置如下:
<Connector maxThreads="300" port="8019" prot
- websocket
dalan_123
websocket
一、低延迟的客户端-服务器 和 服务器-客户端的连接
很多时候所谓的http的请求、响应的模式,都是客户端加载一个网页,直到用户在进行下一次点击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发生。并且所有的http的通信都是客户端控制的,这时候就需要用户的互动或定期轮训的,以便从服务器端加载新的数据。
通常采用的技术比如推送和comet(使用http长连接、无需安装浏览器安装插件的两种方式:基于ajax的长
- 菜鸟分析网络执法官
dcj3sjt126com
网络
最近在论坛上看到很多贴子在讨论网络执法官的问题。菜鸟我正好知道这回事情.人道"人之患好为人师" 手里忍不住,就写点东西吧. 我也很忙.又没有MM,又没有MONEY....晕倒有点跑题.
OK,闲话少说,切如正题. 要了解网络执法官的原理. 就要先了解局域网的通信的原理.
前面我们看到了.在以太网上传输的都是具有以太网头的数据包.
- Android相对布局属性全集
dcj3sjt126com
android
RelativeLayout布局android:layout_marginTop="25dip" //顶部距离android:gravity="left" //空间布局位置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5dip //距离左边距
// 相对于给定ID控件android:layout_above 将该控件的底部置于给定ID的
- Tomcat内存设置详解
eksliang
jvmtomcattomcat内存设置
Java内存溢出详解
一、常见的Java内存溢出有以下三种:
1. java.lang.OutOfMemoryError: Java heap space ----JVM Heap(堆)溢出JVM在启动的时候会自动设置JVM Heap的值,其初始空间(即-Xms)是物理内存的1/64,最大空间(-Xmx)不可超过物理内存。
可以利用JVM提
- Java6 JVM参数选项
greatwqs
javaHotSpotjvmjvm参数JVM Options
Java 6 JVM参数选项大全(中文版)
作者:Ken Wu
Email:
[email protected]
转载本文档请注明原文链接 http://kenwublog.com/docs/java6-jvm-options-chinese-edition.htm!
本文是基于最新的SUN官方文档Java SE 6 Hotspot VM Opt
- weblogic创建JMC
i5land
weblogicjms
进入 weblogic控制太
1.创建持久化存储
--Services--Persistant Stores--new--Create FileStores--name随便起--target默认--Directory写入在本机建立的文件夹的路径--ok
2.创建JMS服务器
--Services--Messaging--JMS Servers--new--name随便起--Pers
- 基于 DHT 网络的磁力链接和BT种子的搜索引擎架构
justjavac
DHT
上周开发了一个磁力链接和 BT 种子的搜索引擎 {Magnet & Torrent},本文简单介绍一下主要的系统功能和用到的技术。
系统包括几个独立的部分:
使用 Python 的 Scrapy 框架开发的网络爬虫,用来爬取磁力链接和种子;
使用 PHP CI 框架开发的简易网站;
搜索引擎目前直接使用的 MySQL,将来可以考虑使
- sql添加、删除表中的列
macroli
sql
添加没有默认值:alter table Test add BazaarType char(1)
有默认值的添加列:alter table Test add BazaarType char(1) default(0)
删除没有默认值的列:alter table Test drop COLUMN BazaarType
删除有默认值的列:先删除约束(默认值)alter table Test DRO
- PHP中二维数组的排序方法
abc123456789cba
排序二维数组PHP
<?php/*** @package BugFree* @version $Id: FunctionsMain.inc.php,v 1.32 2005/09/24 11:38:37 wwccss Exp $*** Sort an two-dimension array by some level
- hive优化之------控制hive任务中的map数和reduce数
superlxw1234
hivehive优化
一、 控制hive任务中的map数: 1. 通常情况下,作业会通过input的目录产生一个或者多个map任务。 主要的决定因素有: input的文件总个数,input的文件大小,集群设置的文件块大小(目前为128M, 可在hive中通过set dfs.block.size;命令查看到,该参数不能自定义修改);2.
- Spring Boot 1.2.4 发布
wiselyman
spring boot
Spring Boot 1.2.4已于6.4日发布,repo.spring.io and Maven Central可以下载(推荐使用maven或者gradle构建下载)。
这是一个维护版本,包含了一些修复small number of fixes,建议所有的用户升级。
Spring Boot 1.3的第一个里程碑版本将在几天后发布,包含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