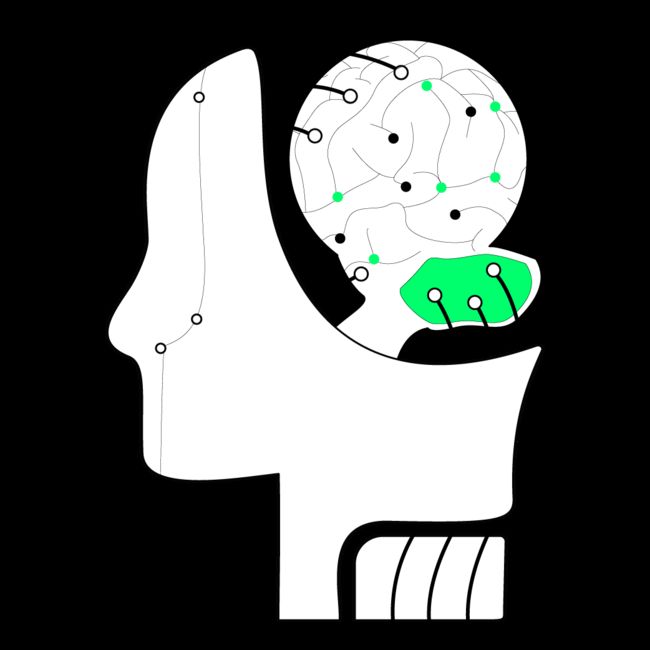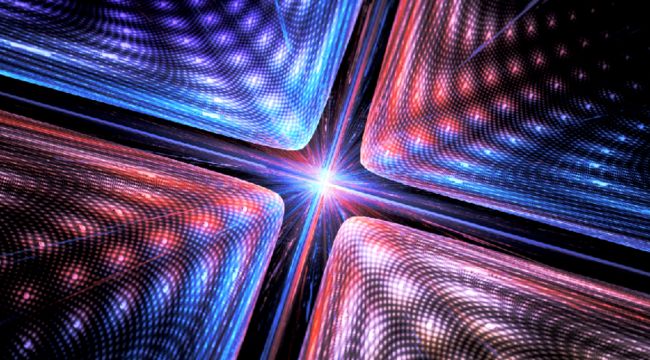实验精神终将胜利:量子纠缠的祛魅七十年
10月4日,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奖项颁发给了法国科学家阿兰·阿斯佩、美国科学家约翰·克劳泽和奥地利科学家安东·蔡林格,以表彰他们在“纠缠光子实验、验证违反贝尔不等式和开创量子信息科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消息一出,“量子纠缠”一度登上了热搜首位。随即,我们看到艰深的物理话题引发热烈讨论。媒体想了千奇百怪的比喻来科普量子纠缠多么奇妙;段子手们说诺贝尔也“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各路高人感叹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并对人生、宇宙、未来发出长篇大论的感慨。
这些内容看多了之后,似乎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感觉:诺贝尔物理学奖,是颁给了某项特别神秘、宏大、不可思议的发现。量子纠缠的下一步,就是时空穿越、心灵感应、四维空间。
被神秘和遥远吸引,是人类的本性。但大家在畅想量子纠缠的“诗与远方”时,可能忽略了另一个问题:这次诺贝尔奖的三位得主,并不是量子纠缠现象的发现者,甚至他们的工作领域并不是理论物理。
与量子纠缠这个概念所带有的神秘与超现实氛围不同,三位诺奖得主的主要工作方向是务实、严谨的实验物理。也就是在数十年间一次次的实验中,人类对量子纠缠的认知,有了缓慢但真实的推进,量子信息科学这样一个全新应用方向才得以打开。
祛魅,是指科学知识中神秘性、神圣性和魅惑力的消解。这个词用来形容人类对量子纠缠的认知历史非常合适。在听多了量子纠缠有多么神奇、多么伟大之后,我们不妨从另一个简朴至极的角度——做实验,来重新回溯这段历史。
这段历史讲的不是科学的尽头是玄学,而是科学终将解释更多,是实验精神终将胜利。
争论起源:微观世界与EPR佯谬
今天我们随处能看到很多关于量子世界、时间与空间的高谈阔论。但这其实并不新鲜,100年前大体也是如此。早在19世纪末,伴随着经典物理学得到了极大发展,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舆论,都开始将目光望向微观系统。20世纪初,量子力学的理论解释工作开始推动。伴随着来自全球的关注,这个领域的争议与讨论也开始丰富了起来。
量子纠缠的概念争议,就来自被称为世纪之争的量子物理辩论。所谓量子纠缠,是一种微观世界中奇特的量子力学现象。处于纠缠状态的两个量子,不论相隔多远都会存在某种关联性。这个显然违反经典物理学的设想,其实是来自一种悖论假说。
1935年,正在与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的爱因斯坦,联合了罗森、波多尔斯基共同发表了论文《物理实在的量子力学描述能否被认为是完备的?》。后人以三人名字的首字母命名其为“EPR”论文。文章中,爱因斯坦质疑了玻尔等人提出的量子力学设想,认为一个粒子只能在局部拥有其所有特性并决定所有测量结果。如果量子系统真的具有强关联态,那么这种管理关系要么会以超光速发生,但这显然违背了相对论;要么当时的量子力学设想具有某种不完备性,缺少前置条件。这个悖论被称为“EPR佯谬”。
由于EPR佯谬是以思想实验的方式提出的。于是玻尔在进行回击时,也主要抓住了思想实验的实验条件不充分、观测手段与观察方法有谬误等方向进行。这里我们无意也没有能力对物理学命题进行深入探讨。但可以发现的是,最初对量子纠缠是否为悖论的讨论,就集中在实验是否可行,以及实验的前提条件、观测手段等等。量子力学的世纪论战,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华山论剑,珍珑棋局,而是发起于实验,聚焦于实验条件是否成立,实验结果是否可信任,实验过程是否可重复。
“做个实验”——也成为接下来数十年量子纠缠探索的真正主题。
实验检索:
光子纠缠与证伪贝尔不等式
为了在实验中探索量子纠缠是否可行,物理学界需要两项最重要的基础:实验介质与实验标准。
在用什么可以证明量子纠缠这一点上,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在1946年找到了办法:用光。
光是一种具有振动方向的波动传导。自然界的光往往是光线随机混合在一起的,但如果通过某种实验手段,让光的振动方向被限制,成为只沿着一种方向振动的偏振光,就可以对光的振动进行观测。光子纠缠易操作,易观察,实验结果受其他因素干扰较少,成了此后对量子纠缠效应的主要实验手段。约翰·惠勒认为,按照量子力学的理论框架,正负电子对湮灭后生成的一对光子应该具有不同的偏振方向。1950年,著名华裔女科学家吴健雄宣布成功实现了光子纠缠实验,生成了历史上第一对偏振方向相反的纠缠光子。从那时起,关于量子纠缠的实验探索正式启动,到如今已经经历了70年岁月。
有了实验方法,下一个问题是实验标准。究竟如何确定量子纠缠效应是否真的能够跨越距离限制?这里就要提到1964年英国物理学家约翰·贝尔提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数学不等式——贝尔不等式。贝尔提出,如果存在隐藏变量,大量测量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将永远不会超过某个值。如何量子纠缠的真实情况符合量子力学的理论预测,那么实验结果将违反贝尔不等式,从而导致超过不等式预设,粒子之间展现出更强的相关性。
从这里开始,2022年物理诺贝尔奖得主们走到了舞台中央。
1972年,约翰·克劳泽发展了贝尔不等式的想法,进行了实际的量子纠缠实验。实验通过一次发射两个纠缠光子,每个光子射向检测偏振的滤光片,以此来观察产生的光子纠缠情况。而实验结果违反了贝尔不等式,与量子纠缠的设想一致。
但在当时,这种实验引发了很多质疑,甚至被指出了很多漏洞。比如实验在制备和捕获粒子方面效率太低、测量方式存在问题、纠缠粒子之间距离太小等等,其结果并不具备说服力。尽管面对着诸多挑战,但克劳泽教授一直坚持着光子纠缠的实验方向,并进行了源源不断地实验改进,最终证明了量子纠缠的超远距离干涉确实存在。
除了约翰·克劳泽之外,其他人也在积极探索证伪贝尔不等式的实验。1982年,另一位诺奖得主阿兰·阿斯佩等人改进并完善了克劳泽的实验方法。在纠缠粒子离开发射源后,通过切换测量设置的方式来确保制备粒子的方法不会影响实验结果。
1998年,第三位诺奖得主安东·蔡林格等人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完成贝尔定理实验。通过多粒子纠缠态的实验,彻底排除了定域性漏洞,以决定性的实验结果证明了量子纠缠真实存在。同时,蔡林格团队的多粒子实验可开创了量子通信与密码学的诸多可能性。1997年,其团队完成了量子隐形传态的原理性实验验证,为量子信息学奠定了基础。2015年,安东·蔡林格团队又完成了无漏洞的贝尔不等式实验验证。
在50年间,一次次的实验跋涉,最终证明所有结果都证伪贝尔不等式,支持量子力学对微观世界的法则设想。
至此我们才知道,量子纠缠是真实存在的。
持续探索:
进入新世纪的大型实验
有了基础方法与基础结论,量子纠缠的科学价值也就愈发明晰。科学界的好奇开始由量子纠缠是否存在,转向了我们能否控制量子纠缠,以及能否通过量子纠缠窥探充满未知的微观世界。这个过程中,不断输出的量子纠缠实验成果,也像很多科学发展一样“沿途下蛋”,打开了量子信息学这个应用学科的发展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激光的发展和应用成了探索光子纠缠的主要路径,这也是我们看到很多量子实验设备都与激光紧密相连的原因。通过激光脉冲,光子纠缠现象可以被更精准、高效地控制和观察。多粒子纠缠态的研究与探索成了学界主流,造价昂贵、高度精密的量子实验设备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随着量子纠缠实验的价值愈发明晰,其带来的量子信息学价值产出更加充沛,同时实验成本不断增大。量子纠缠开始成为国家科技竞争的焦点,以及科技战略的重点倾斜方向。最近几天,大量媒体都在讨论中国在量子纠缠领域研究处于世界第一方阵,其价值与意义也在于此。
2012年,著名的潘建伟小组首次实现了八光子纠缠,并成功将该技术应用于拓扑量子纠错和百公里量子隐形传态实验。2010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实现了4个量子接口之间的纠缠。之后清华大学段路明团队通过光束复分技术,在实验中实现了25个量子接口之间的量子纠缠。至此,量子加密、量子网络等量子信息学成果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2017年,潘建伟团队利用“墨子号”量子卫星完成了全新的量子通信进行试验,实现了在在1200公里的通信距离,以卫星量子诱骗态光源平均每秒发送4000万个信号光子,极大丰富了量子通信的实验手段,并为量子通信走向应用奠定了新的基础。
在光子纠偏之外,以超导微波来诱发量子纠偏,是另一种目前阶段的主要实验思路。也是通用型量子计算机的主要探索方向。2018年,芬兰阿尔托大学教授麦卡·习岚帕团队对两个独自振动的鼓膜进行了量子纠缠,两个鼓膜持续进行了30分钟左右的互动。
对于量子纠缠的实验从未止步,就在今年8月《自然》杂志还发布了德国团队实现14个光子有效纠缠的研究成果。
量子并不代表着神秘莫测的未知。只有实验,更精密、丰富、多元的实验,才能让量子纠缠从神坛走下,来到人间。
应用黎明:
从量子纠缠到量子通信、量子计算
距离第一次光子纠偏实验,已经过去了七十年。虽然在大众舆论范畴中,我们依旧有太多关于量子力学的祛魅工作要完成,毕竟今天的量子就像曾经的电能一样,有很多东西对大众来说是反常识的,但在产学衔接的端口,量子纠缠的数十年实验探索已经产出了应用成果。其中最为大众熟悉的就是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
一方面,这些技术应用了量子纠缠本身的并发特性来实现目标。比如目前的量子通信,主要是通过量子加密的方式来提升信息安全水平,但也有一些量子信息科学成果,与量子纠缠的实验进程密不可分。比如光量子计算机,就充分应用了激光导致光子纠偏的实验现象。目前IBM、谷歌等公司探索的通用量子计算机,也与量子纠缠实验中的超导传递、绝对低温环境等发现紧密相关。
在今天,我们已经在量子纠缠理论得到确认,量子纠缠实验不断发展的帮助下,看到了量子应用的一点点曙光。尽管这种曙光依旧遥远,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达到某种临界点,量子信息学将对目前的信息科学产生不可逆转的巨大影响。
当然,利用量子纠缠无视距离界限传递信息的“真·量子通信”尚且遥远。目前开始探索应用的量子通信主要是信息加密与解密手段。而更加饱受期待的量子计算,还依旧无法摆脱计算任务有限、对温度等环境要求苛刻、造价巨大等限制。在过去的内容中,我们说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每一到两年,就会有公司站出来说我们实现了量子计算机超越经典计算机的“量子霸权”。但每次所谓的量子霸权,都难以自圆其说,无法取得业界共认。
不管怎么说,量子纠缠已经有一条支脉从实验室里走出来,走向了充满更多挑战的产业世界。大环境下的量子计算机发展,建设大型量子计算设备,已经成为科技巨头的兵家必争之地,甚至国家科技竞赛的关键。同时量子加密、量子模拟、量子深度学习等产业不断发展,正在为量子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纠缠”带来更多机遇,吸引更多人才。
我们曾经采访过许多量子科学与量子计算领域的老师,他们普遍认为,量子科学在今天需要更多科普,需要号召更多年轻人加入这个学科。
一方面,舆论反复渲染量子科学的“高深莫测”,甚至污名化搞出量子鞋垫、量子速读,会令很多学生对量子学科产生担忧与畏惧,不看好其就业前景,从而导致学科的人才流失。另一方面,社会中的各种大师,社交媒体上的各路大神,不遗余力发表着各种各样的“量子高论”,其实都与量子科学没有任何关系。这很容易让一个刚刚产生火花的方向,蒙上太多不必要的阴霾。
如果大家真的关注量子纠缠,那不妨多读一些科普内容,关注各大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的量子技术布局。千万不要受到诺奖新闻影响,去很多“量子XX”贴吧读一些民间高手的奇谈怪论。那些东西过于离谱。
不是什么东西都要落到玄学,时空,佛性,四维空间,多元宇宙上去。科学世界也没有“遇事不决,量子力学”。量子纠缠的探索,反而是实验精神的胜利,是人类用理性战胜未知的胜利。
坐而玄谈是一种快乐,甚至是人的本性。但这最多能丰富一下业余生活,结交三五知己。真正推动科学进步的,是实验精神与专业分工,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探索,是不断提出证伪,找寻漏洞,拓展手段,夯实结论。
实验精神终将胜利,我们终将像面对电能、计算机一样面对量子世界。抵达终极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终极成为旅途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