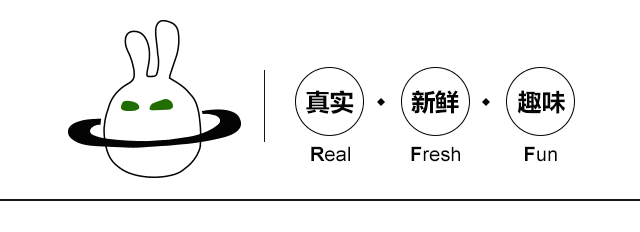我们杀死了那个住在五棵松的中年男人
沿长安街往西,从万寿路到五棵松,曾是北京城里最熠熠生辉的一条玉带。
从万寿路到五棵松,由东到西,短短不过三里地,却密密麻麻挤满了北京城中或大或小的权贵: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军委各总部的家属大院,一座连着一座,在这里依次排开。
公务员分房,是早已逝去的都市传说了,哪怕有,怕也多半远在昌平。如今住在那一带的人,大多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便来到北京,才能赶上分房的好时候。
当年来到北京时,也是一脸懵懂,风华正茂;二三十年过去了,脸上的年轻神采慢慢消失,年轻人们渐渐变成了处长、主任、局长、资深,渐渐地,似乎有了那么一点积蓄,有了那么一点身份,说上两句话,也能管那么一点儿用了。
短短的三里地中,密密麻麻挤满了成千上万个处级、厅级、省部级干部。就像食堂蒸笼里刚出锅的馒头,一揭盖,白花花一片,个个看上去相差无几:住分配的三居室,开十万左右的小车上班,有个在北京四中或八中念书的孩子。
这些看起来灰头土脸的中年人,放出北京城,可能就是让地方官们浑身哆嗦的钦差大臣。
因此,住在万寿路至五棵松一段的中年人,哪怕面目再谦卑,内心也长着三分傲骨。
想来也是——他们刚来北京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子?那时候,鸟巢是一片农田,国贸跑着驴拉车。李彦宏在硅谷做白领,马化腾官司败诉,赔了微软一大笔钱,马云来北京跑销售,被部委几个办事员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改变时代的下海潮过去了,大下岗还未拉开序幕,体制内还是最最光鲜亮丽的工作。
何况,这里是北京。
那份荣耀深深印入他们脑髓,嵌入他们骨肉,在血脉中流淌。二三十年过去了,北京城的东部涌起了无数的写字楼,北京城的北部开辟出一个接一个的创业园,北京城的南部,丽泽和亦庄也拔地而起。唯有西部,尤其是万寿路到五棵松的这一条玉带,二三十年过去了,仿佛不曾有过什么大变。
体制内像一道高墙,把这些当年来到北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年轻人们,好好地呵护了起来。二三十年过去了,他们不曾经历危机,不曾担忧失业,薪水或许是少了点,但过得下去;房价似乎是涨了些,但单位分配的也够住了。
他们没有什么值得忧心的事。
于是那个夜晚,他来了。
毫无疑问。这个住在五棵松的男人,是预备着来接受称赞和艳羡的。因此等众人落席后半小时有余,他方才姗姗来迟。
他必有值得称赞和艳羡的地方。在这桌十几个人的同乡会上,数他来北京最早,资历最深。他目睹北京的沙尘来了又走,雾霾走了又来,身上积淀着京城三十年的黄沙和细尘,轻轻一抖,全是历史的味道。
他往那儿一坐,透着灯光,甚至能看到灰尘以螺旋状升起的姿态。
他必有值得称赞和艳羡的地方。他住在五棵松的部队大院里,在某数字打头的著名军队医院任职。虽负责政治工作,不是技术人才,但这金子招牌足以让他在旁人面前扬眉吐气,无论到哪儿,都是众人争相巴结和讨好的焦点。
如此生活三十年,他从未觉得有什么不遂意的地方。若说真有什么遗憾,无非是国家放开二胎太晚,如今和太太都五十多岁了,哪怕有心,也是无力。
宴会开头令人满意。晚辈们纷纷敬酒,夹菜,给予他情感上的呵护与关怀。他看着眼前的同乡晚辈,个个比他年轻,心里不能不生出几分优越来,回酒时总是说道,好好干,房子车子嘛,以后总会有的,我不也是这样熬过来的吗?
第一道暴击来自于那个小包工头。
“自己做事,很不容易吧?”酒过三巡,他开始热络地同别人攀谈起来。
“是辛苦点儿。马上孩子要上学了。”小包工头应和道。
“唷,上学啊,我记得你还没有北京户口,对不对?没有户口该怎么上学呢?总不能去上民工学校吧。”
小包工头笑:“就上私立学校好了。”
“私立不靠谱,没法在北京高考。”
“没关系。高中准备送孩子出国。”
“可得花不少钱?”
“三五百万总跑不了。好的私利不便宜,小学一年就得十几万。”
他心里咯噔一下。几年不问,这学费竟蹭蹭涨到如此地步了?十几万!他年薪一刨,剩下的那点儿钱,连家里的吃喝都不够!
他决定不再与小包工头纠缠下去,转身去同另一位更加年轻的同乡攀谈——看样子,左不过二三十来岁,不用勉强与他闲聊教育费话题。
在那里,他接受了当天的第二道暴击。
“来北京多久了?”
年轻人:“五年了。”
“也不短了。买房了没有?”
“刚买了,就在东边,朝阳。”
“哎呀呀,东边可不好!”他激动起来,“乱糟糟的,外地人又多!我几年前去看过,整一个大工地,不像话,不适合居住!”
年轻人有点儿诧异地看着他——他似乎忘了,在座的这一整桌,都是外地人。
“不过好在便宜——东边总比西边便宜很多的,三五万吧?”
年轻人面上的诧异更浓了:“现在也要七八万了。”
他心里又“咯噔”一下:“那你爸妈掏了不少钱吧。”
年轻人决定结束话题:“我跟朋友合伙开公司,做新媒体,还房贷还是够的。”
“新媒体?我知道知道,就是写文章,拿稿费吧。哎呀,稿费哪里够呢?我年轻时也喜欢写点儿文章,一篇也就一两百,现在富裕了,千八百总该顶天了。”
年轻人:“五万。”
这次轮到他诧异了,脸上的眼珠子也几乎快瞪了出来:“你写什么文章?能写到五万?”
第三道暴击来自于回五棵松的途中。
因大家都喝了酒,东主为客人叫了网约车。他与一位教授同行。这位教授前不久去医院体检,与他结识。因有求于他,言语态度相当客气而热烈,他颇感受用——无论如何,被教授吹捧一番,这滋味总不会太差。
“这些年轻人不太成器了,”他向教授抱怨,“不好好工作,搞什么生意,做什么媒体,这哪里是长久之道呢?像我们这样,工资是少点儿,但给国家办事,体面哇,牢靠!我看这同乡会啊,以后也不用找这么多人了,就你我几个往来便好。”
“你说得有理。”教授点头。
“哎呀,先送你吧——如今你住哪儿?”
教授笑答 :“刚搬家,去了清河。”
他一头雾水:“清河?清河在哪里,是北京吗?”
“是在五环外了,昌平。”教授说。
“是便宜吧?那理解,理解,只是住那么远,上班可不方便。”
“我已辞职了,”教授说,“我带着专利自己开了公司,跟人联合创业,搬去了那边的创业园。如今上班十分钟,近得很。”
闲聊中到了教授新家。他下车同教授道别,抬头,眼前一个宽敞的别墅区,里头绿树成荫,喷泉水声缕缕不绝,不禁问道:“这得多少钱?”
“总要十万左右一平吧。”
在回家路上,他越想越不对味,冲司机埋怨起来:“你说说,你说说,五环外的房子,卖十万一平,他可不是吹牛吧!这像话吗?就这破地儿!谁要来住啊!宁送我我也不来——对了,师傅,载我去五棵松,你知道那儿吧?那儿才是真正的好地方,市中心!住的全是体面人。有钱跟体面是一回事吗?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有钱便是体面吗?我看未必,我看未必……辞职搞创业?我看他迟早破产!”
司机只当他醉了,专心开车,默默不语。
住在五棵松的中年人们,是幸运的。他们赶上体制内最后一波红利,拿到了户口,拿到了房产,早几年,还能从中捞上那么一点儿油水——如今挤破头进去的年轻人,可一样也别想了。
体制内像一个隔绝所有污染的无菌室,把这些中年人们保护得很好。好到甚至不知东边修起了大裤衩,北边盖上了鸟巢,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住在五棵松的中年人们,也是不幸的。从跨进红墙的那一刻起,很多人的年岁便停止生长了。虽然也知道转基因和互联网,但心还是孩子的心,惦记的仍是当年在马云面前颐指气使的模样。是酒精缸里泡着的标本,隔离了时间流逝。
五棵松的中年人,不要轻易迈过复兴门的结界。出了这道结界,便有被杀死的可能,就像印第安人不能抵挡来自欧洲大陆的天花。
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唯有万寿路到五棵松,每晚过了九点以后,连路灯也熄灭了。这里是如此安静,安静到不敢相信我们仍然身在北京。
这短短三里地内,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庄重的,轻薄的,萧瑟的,权威的,被揉成了一团,积聚在北京城的上空,终年不散。
朝阳的年轻人有诗和酒,这里有户口。
海淀的创业新贵有别墅,这里有央产楼。
这里住着的人们,年纪越大,世界越小。不是他们眼界窄了,是因为这片天地的外沿从来不曾拓宽过,而外头的世界,早已是一日千里。
愿他们生活在经验里,直到大厦崩塌——不对,这座大厦,永远不会崩塌的。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姜汁满头(ID:linlinisdead)
值班编辑:木木兔
▼
推荐阅读
换了9份工作后,我又辞职了
作为第一批秘密使用iphone X 的人,我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