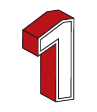一、什么是宏函数?通过宏定义的函数是宏函数。如下,编译器在预处理阶段会将Add(x,y)替换为((x)*(y))#defineAdd(x,y)((x)*(y))#defineAdd(x,y)((x)*(y))intmain(){inta=10;intb=20;intd=10;intc=Add(a+d,b)*2;cout<
地推话术,如何应对地推过程中家长的拒绝
校师学
相信校长们在做地推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市场专员反馈家长不接单,咨询师反馈难以邀约这些家长上门,校区地推疲软,招生难。为什么?仅从地推层面分析,一方面因为家长受到的信息轰炸越来越多,对信息越来越“免疫”;而另一方面地推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营销话术没有提高,无法应对家长的拒绝,对有意向的家长也不知如何跟进,眼睁睁看着家长走远;对于家长的疑问,更不知道如何有技巧地回答,机会白白流失。由于回答没技巧和专业
谢谢你们,爱你们!
鹿游儿
昨天家人去泡温泉,二个孩子也带着去,出发前一晚,匆匆下班,赶回家和孩子一起收拾。饭后,我拿出笔和本子(上次去澳门时做手帐的本子)写下了1\2\3\4\5\6\7\8\9,让后让小壹去思考,带什么出发去旅游呢?她在对应的数字旁边画上了,泳衣、泳圈、肖恩、内衣内裤、tapuy、拖鞋……画完后,就让她自己对着这个本子,将要带的,一一带上,没想到这次带的书还是这本《便便工厂》(晚上姑婆发照片过来,妹妹累得
C语言如何定义宏函数?
小九格物
c语言
在C语言中,宏函数是通过预处理器定义的,它在编译之前替换代码中的宏调用。宏函数可以模拟函数的行为,但它们不是真正的函数,因为它们在编译时不会进行类型检查,也不会分配存储空间。宏函数的定义通常使用#define指令,后面跟着宏的名称和参数列表,以及宏展开后的代码。宏函数的定义方式:1.基本宏函数:这是最简单的宏函数形式,它直接定义一个表达式。#defineSQUARE(x)((x)*(x))2.带参
微服务下功能权限与数据权限的设计与实现
nbsaas-boot
微服务java架构
在微服务架构下,系统的功能权限和数据权限控制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系统规模的扩大和微服务数量的增加,如何保证不同用户和服务之间的访问权限准确、细粒度地控制,成为设计安全策略的关键。本文将讨论如何在微服务体系中设计和实现功能权限与数据权限控制。1.功能权限与数据权限的定义功能权限:指用户或系统角色对特定功能的访问权限。通常是某个用户角色能否执行某个操作,比如查看订单、创建订单、修改用户资料等。数据权限:
理解Gunicorn:Python WSGI服务器的基石
范范0825
ipythonlinux运维
理解Gunicorn:PythonWSGI服务器的基石介绍Gunicorn,全称GreenUnicorn,是一个为PythonWSGI(WebServerGatewayInterface)应用设计的高效、轻量级HTTP服务器。作为PythonWeb应用部署的常用工具,Gunicorn以其高性能和易用性著称。本文将介绍Gunicorn的基本概念、安装和配置,帮助初学者快速上手。1.什么是Gunico
小丽成长记(四十三)
玲玲54321
小丽发现,即使她好不容易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下一秒总会有不确定的伤脑筋的事出现,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人生就没有停下的时候,小问题不断出现。不过她今天看的书,她接受了人生就是不确定的,厉害的人就是不断创造确定性,在Ta的领域比别人多的确定性就能让自己脱颖而出,显示价值从而获得的比别人多的利益。正是这样的原因,因为从前修炼自己太少,使得她现在在人生道路上打怪起来困难重重,她似乎永远摆脱不了那种无力感,有种习
学点心理知识,呵护孩子健康
静候花开_7090
昨天听了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张玲老师的《哪里才是学生心理健康的最后庇护所,超越教育与技术的思考》的讲座。今天又重新学习了一遍,收获匪浅。张玲博士也注意到了当今社会上的孩子由于心理问题导致的自残、自杀及伤害他人等恶性事件。她向我们普及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她说心理健康的一些基本命题,我们与我们通常的一些教育命题是不同的,她还举了几个例子,让我们明白我们原来以为的健康并非心理学上的健康。比如如果
2021年12月19日,春蕾教育集团团建活动感受——黄晓丹
黄错错加油
感受:1.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游戏环节让我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得到了锻炼,也增长了不少知识。2.游戏过程中,我们贡献的是个人力量,展现的是团队的力量。它磨合的往往不止是工作的熟悉,更是观念上契合度的贴近。3.这和工作是一样的道理。在各自的岗位上,每个人摆正自己的位置、各司其职充分发挥才能,并团结一致劲往一处使,才能实现最大的成功。新知:1.团队精神需要不断地创新。过去,人们把创新看作是冒风险,现在人们
Cell Insight | 单细胞测序技术又一新发现,可用于HIV-1和Mtb共感染个体诊断
尐尐呅
结核病是艾滋病合并其他疾病中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结核病由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tuberculosis,Mtb)感染引起,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病)由人免疫缺陷病毒(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type1,HIV-1)感染引起。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张国良团队携手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吴靓团队,共同研究得出单细胞测序
c++ 的iostream 和 c++的stdio的区别和联系
黄卷青灯77
c++算法开发语言iostreamstdio
在C++中,iostream和C语言的stdio.h都是用于处理输入输出的库,但它们在设计、用法和功能上有许多不同。以下是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区别1.编程风格iostream(C++风格):C++标准库中的输入输出流类库,支持面向对象的输入输出操作。典型用法是cin(输入)和cout(输出),使用>操作符来处理数据。更加类型安全,支持用户自定义类型的输入输出。#includeintmain(){in
瑶池防线
谜影梦蝶
冥华虽然逃过了影梦的军队,但他是一个忠臣,他选择上报战况。败给影梦后成逃兵,高层亡尔还活着,七重天失守......随便一条,即可处死冥华。冥华自然是知道以仙界高层的习性此信一发自己必死无疑,但他还选择上报实情,因为责任。同样此信送到仙宫后,知道此事的人,大多数人都认定冥华要完了,所以上到仙界高层,下到扫大街的,包括冥华自己,全都准备好迎接冥华之死。如果仙界现在还属于两方之争的话,冥华必死无疑。然而
爬山后遗症
璃绛
爬山,攀登,一步一步走向制高点,是一种挑战。成功抵达是一种无法言语的快乐,在山顶吹吹风,看看风景,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然而,爬山一时爽,下山腿打颤,颠簸的路,一路向下走,腿部力量不够,走起来抖到不行,停不下来了!第二天必定腿疼,浑身酸痛,坐立难安!
Nginx负载均衡
510888780
nginx应用服务器
Nginx负载均衡一些基础知识:
nginx 的 upstream目前支持 4 种方式的分配
1)、轮询(默认)
每个请求按时间顺序逐一分配到不同的后端服务器,如果后端服务器down掉,能自动剔除。
2)、weight
指定轮询几率,weight和访问比率成正比
RedHat 6.4 安装 rabbitmq
bylijinnan
erlangrabbitmqredhat
在 linux 下安装软件就是折腾,首先是测试机不能上外网要找运维开通,开通后发现测试机的 yum 不能使用于是又要配置 yum 源,最后安装 rabbitmq 时也尝试了两种方法最后才安装成功
机器版本:
[root@redhat1 rabbitmq]# lsb_release
LSB Version: :base-4.0-amd64:base-4.0-noarch:core
FilenameUtils工具类
eksliang
FilenameUtilscommon-io
转载请出自出处:http://eksliang.iteye.com/blog/2217081 一、概述
这是一个Java操作文件的常用库,是Apache对java的IO包的封装,这里面有两个非常核心的类FilenameUtils跟FileUtils,其中FilenameUtils是对文件名操作的封装;FileUtils是文件封装,开发中对文件的操作,几乎都可以在这个框架里面找到。 非常的好用。
xml文件解析SAX
不懂事的小屁孩
xml
xml文件解析:xml文件解析有四种方式,
1.DOM生成和解析XML文档(SAX是基于事件流的解析)
2.SAX生成和解析XML文档(基于XML文档树结构的解析)
3.DOM4J生成和解析XML文档
4.JDOM生成和解析XML
本文章用第一种方法进行解析,使用android常用的DefaultHandler
import org.xml.sax.Attributes;
通过定时任务执行mysql的定期删除和新建分区,此处是按日分区
酷的飞上天空
mysql
使用python脚本作为命令脚本,linux的定时任务来每天定时执行
#!/usr/bin/python
# -*- coding: utf8 -*-
import pymysql
import datetime
import calendar
#要分区的表
table_name = 'my_table'
#连接数据库的信息
host,user,passwd,db =
如何搭建数据湖架构?听听专家的意见
蓝儿唯美
架构
Edo Interactive在几年前遇到一个大问题:公司使用交易数据来帮助零售商和餐馆进行个性化促销,但其数据仓库没有足够时间去处理所有的信用卡和借记卡交易数据
“我们要花费27小时来处理每日的数据量,”Edo主管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的高级副总裁Tim Garnto说道:“所以在2013年,我们放弃了现有的基于PostgreSQL的关系型数据库系统,使用了Hadoop集群作为公司的数
spring学习——控制反转与依赖注入
a-john
spring
控制反转(Inversion of Control,英文缩写为IoC)是一个重要的面向对象编程的法则来削减计算机程序的耦合问题,也是轻量级的Spring框架的核心。 控制反转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依赖注入(Dependency Injection,简称DI)和依赖查找(Dependency Lookup)。依赖注入应用比较广泛。
用spool+unixshell生成文本文件的方法
aijuans
xshell
例如我们把scott.dept表生成文本文件的语句写成dept.sql,内容如下:
set pages 50000;
set lines 200;
set trims on;
set heading off;
spool /oracle_backup/log/test/dept.lst;
select deptno||','||dname||','||loc
1、基础--名词解析(OOA/OOD/OOP)
asia007
学习基础知识
OOA:Object-Oriented Analysis(面向对象分析方法)
是在一个系统的开发过程中进行了系统业务调查以后,按照面向对象的思想来分析问题。OOA与结构化分析有较大的区别。OOA所强调的是在系统调查资料的基础上,针对OO方法所需要的素材进行的归类分析和整理,而不是对管理业务现状和方法的分析。
OOA(面向对象的分析)模型由5个层次(主题层、对象类层、结构层、属性层和服务层)
浅谈java转成json编码格式技术
百合不是茶
json编码java转成json编码
json编码;是一个轻量级的数据存储和传输的语言
在java中需要引入json相关的包,引包方式在工程的lib下就可以了
JSON与JAVA数据的转换(JSON 即 JavaScript Object Natation,它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非
常适合于服务器与 JavaScript 之间的数据的交
web.xml之Spring配置(基于Spring+Struts+Ibatis)
bijian1013
javaweb.xmlSSIspring配置
指定Spring配置文件位置
<context-param>
<param-name>contextConfigLocation</param-name>
<param-value>
/WEB-INF/spring-dao-bean.xml,/WEB-INF/spring-resources.xml,
/WEB-INF/
Installing SonarQube(Fail to download libraries from server)
sunjing
InstallSonar
1. Download and unzip the SonarQube distribution
2. Starting the Web Server
The default port is "9000" and the context path is "/". These values can be changed in &l
【MongoDB学习笔记十一】Mongo副本集基本的增删查
bit1129
mongodb
一、创建复本集
假设mongod,mongo已经配置在系统路径变量上,启动三个命令行窗口,分别执行如下命令:
mongod --port 27017 --dbpath data1 --replSet rs0
mongod --port 27018 --dbpath data2 --replSet rs0
mongod --port 27019 -
Anychart图表系列二之执行Flash和HTML5渲染
白糖_
Flash
今天介绍Anychart的Flash和HTML5渲染功能
HTML5
Anychart从6.0第一个版本起,已经逐渐开始支持各种图的HTML5渲染效果了,也就是说即使你没有安装Flash插件,只要浏览器支持HTML5,也能看到Anychart的图形(不过这些是需要做一些配置的)。
这里要提醒下大家,Anychart6.0版本对HTML5的支持还不算很成熟,目前还处于
Laravel版本更新异常4.2.8-> 4.2.9 Declaration of ... CompilerEngine ... should be compa
bozch
laravel
昨天在为了把laravel升级到最新的版本,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如下错误:
ErrorException thrown with message "Declaration of Illuminate\View\Engines\CompilerEngine::handleViewException() should be compatible with Illuminate\View\Eng
编程之美-NIM游戏分析-石头总数为奇数时如何保证先动手者必胜
bylijinnan
编程之美
import java.util.Arrays;
import java.util.Random;
public class Nim {
/**编程之美 NIM游戏分析
问题:
有N块石头和两个玩家A和B,玩家A先将石头随机分成若干堆,然后按照BABA...的顺序不断轮流取石头,
能将剩下的石头一次取光的玩家获胜,每次取石头时,每个玩家只能从若干堆石头中任选一堆,
lunce创建索引及简单查询
chengxuyuancsdn
查询创建索引lunce
import java.io.File;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org.apache.lucene.analysis.Analyzer;
import org.apache.lucene.analysis.standard.StandardAnalyzer;
import org.apache.lucene.document.Docume
[IT与投资]坚持独立自主的研究核心技术
comsci
it
和别人合作开发某项产品....如果互相之间的技术水平不同,那么这种合作很难进行,一般都会成为强者控制弱者的方法和手段.....
所以弱者,在遇到技术难题的时候,最好不要一开始就去寻求强者的帮助,因为在我们这颗星球上,生物都有一种控制其
flashback transaction闪回事务查询
daizj
oraclesql闪回事务
闪回事务查询有别于闪回查询的特点有以下3个:
(1)其正常工作不但需要利用撤销数据,还需要事先启用最小补充日志。
(2)返回的结果不是以前的“旧”数据,而是能够将当前数据修改为以前的样子的撤销SQL(Undo SQL)语句。
(3)集中地在名为flashback_transaction_query表上查询,而不是在各个表上通过“as of”或“vers
Java I/O之FilenameFilter类列举出指定路径下某个扩展名的文件
游其是你
FilenameFilter
这是一个FilenameFilter类用法的例子,实现的列举出“c:\\folder“路径下所有以“.jpg”扩展名的文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C语言学习五函数,函数的前置声明以及如何在软件开发中合理的设计函数来解决实际问题
dcj3sjt126com
c
# include <stdio.h>
int f(void) //括号中的void表示该函数不能接受数据,int表示返回的类型为int类型
{
return 10; //向主调函数返回10
}
void g(void) //函数名前面的void表示该函数没有返回值
{
//return 10; //error 与第8行行首的void相矛盾
}
in
今天在测试环境使用yum安装,遇到一个问题: Error: Cannot retrieve metalink for repository: epel. Pl
dcj3sjt126com
centos
今天在测试环境使用yum安装,遇到一个问题:
Error: Cannot retrieve metalink for repository: epel. Please verify its path and try again
处理很简单,修改文件“/etc/yum.repos.d/epel.repo”, 将baseurl的注释取消, mirrorlist注释掉。即可。
&n
单例模式
shuizhaosi888
单例模式
单例模式 懒汉式
public class RunMain {
/**
* 私有构造
*/
private RunMain() {
}
/**
* 内部类,用于占位,只有
*/
private static class SingletonRunMain {
priv
Spring Security(09)——Filter
234390216
Spring Security
Filter
目录
1.1 Filter顺序
1.2 添加Filter到FilterChain
1.3 DelegatingFilterProxy
1.4 FilterChainProxy
1.5
公司项目NODEJS实践0.1
逐行分析JS源代码
mongodbnginxubuntunodejs
一、前言
前端如何独立用nodeJs实现一个简单的注册、登录功能,是不是只用nodejs+sql就可以了?其实是可以实现,但离实际应用还有距离,那要怎么做才是实际可用的。
网上有很多nod
java.lang.Math
liuhaibo_ljf
javaMathlang
System.out.println(Math.PI);
System.out.println(Math.abs(1.2));
System.out.println(Math.abs(1.2));
System.out.println(Math.abs(1));
System.out.println(Math.abs(111111111));
System.out.println(Mat
linux下时间同步
nonobaba
ntp
今天在linux下做hbase集群的时候,发现hmaster启动成功了,但是用hbase命令进入shell的时候报了一个错误 PleaseHoldException: Master is initializing,查看了日志,大致意思是说master和slave时间不同步,没办法,只好找一种手动同步一下,后来发现一共部署了10来台机器,手动同步偏差又比较大,所以还是从网上找现成的解决方
ZooKeeper3.4.6的集群部署
roadrunners
zookeeper集群部署
ZooKeeper是Apache的一个开源项目,在分布式服务中应用比较广泛。它主要用来解决分布式应用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数据管理问题,如:统一命名服务、状态同步、集群管理、配置文件管理、同步锁、队列等。这里主要讲集群中ZooKeeper的部署。
1、准备工作
我们准备3台机器做ZooKeeper集群,分别在3台机器上创建ZooKeeper需要的目录。
数据存储目录
Java高效读取大文件
tomcat_oracle
java
读取文件行的标准方式是在内存中读取,Guava 和Apache Commons IO都提供了如下所示快速读取文件行的方法: Files.readLines(new File(path), Charsets.UTF_8); FileUtils.readLines(new File(path)); 这种方法带来的问题是文件的所有行都被存放在内存中,当文件足够大时很快就会导致
微信支付api返回的xml转换为Map的方法
xu3508620
xmlmap微信api
举例如下:
<xml>
<return_code><![CDATA[SUCCESS]]></return_code>
<return_msg><![CDATA[OK]]></return_msg>
<ap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