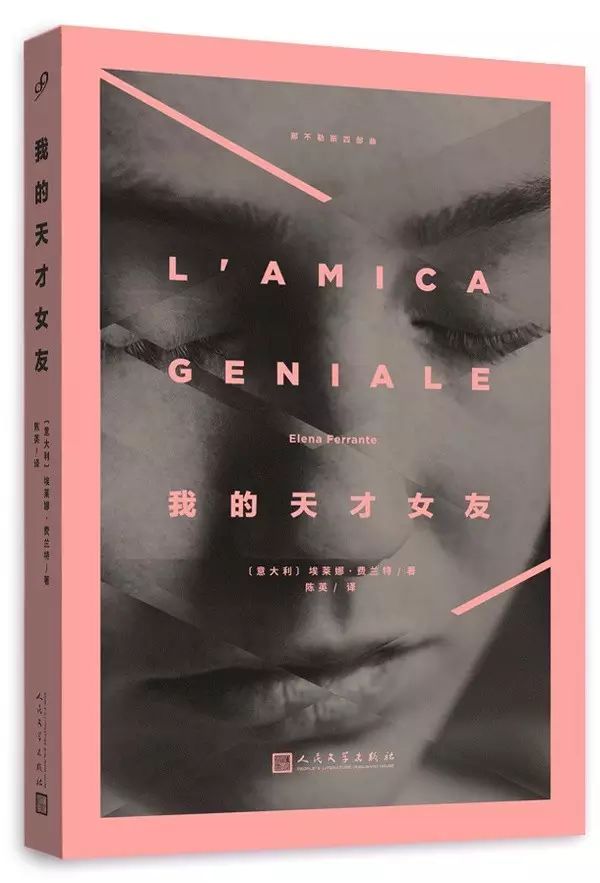只有你身为女人才会知道这些丑陋的秘密
埃莱娜·费兰特,一位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从不露面的神秘作家」。尽管她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但自1991年第一本小说出版之始,她便从未公开过自己的性别和任何个人信息。「我相信人们应当在署有作家名字的那本书里去寻找作家,而非从写作自身私人生活的那个作家本人身上去寻找。」
我们决定用「她」来指代埃莱娜·费兰特,是因为从其最为出名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失踪的孩子》)中得出定论:除非作者是一位女人,否则很难对女性关系产生如此细腻的洞察和体会——四部曲描述两个女孩长达60年的史诗般的友谊。这不是一个歌颂女性纯洁情谊的故事,相反,同性关系间的矛盾、摩擦和尖锐在埃莱娜的笔下展露无遗。
节日快乐,女朋友们。在如此特殊的一天,分享一篇 Financial Times对埃莱娜·费兰特的专访。耐心读完之后,你是否会对女性或者女性关系有一些新的感悟和定义。亦或是,你的女性朋友的某些「天才瞬间」会突然闪现在脑中。请将它们分享给我们。我们将选取留言上「点赞数」最多的前十位获得者,送出《我的天才女友》。
文|Liz Jobey
编译|Daniela Petracc 、黎诗韵
来源|Financial Times
摄影|Getty
1991,在第一部小说《讨厌的爱》即将出版之际,该书的作者给意大利某出版商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书一旦被写出来,就不再需要它的作者,如果它真的足够好的话,迟早会找到自己的读者;反之则不会……此外,难道推广费不昂贵吗?我会是你们出版社成本最低的作者,我会让你免除这些费用。」
她是不是成本最低的作者也许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是最神秘,也是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作者。当她以埃莱娜·费兰特为笔名出版的七本小说陆续被翻译成英文后,她俨然成为当今在世最著名的意大利文学小说家。九月,她出版了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失踪的孩子》。迄今为止,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在美国销量已达到75万册,在英国逼近25万册。
随着费兰特的名气越来越大,外界对作者本人的猜测也随之高涨:她的书真的是她的意大利出版人桑德罗·费里写的吗?又或者是费里的妻子兼商业伙伴桑德拉?费兰特真的是男人吗?(不太可能,如果你读过这些书的话。)也许它们是她的英译者安·戈德斯坦写的?
在那封早期的信中,费兰特仅留下一条与外界沟通的渠道:「我将只接受书面采访,但即便是书面采访,我也倾向于控制到最少,若非必要则不为之。」上个月,她同意为这本杂志的特刊接受一次难得的采访。
通过这些难得的交流,我们对她的生活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她出生并成长于那不勒斯;小说涵盖的时期显示,她的童年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她学习古典文学,已婚(或者曾经结过婚),有了孩子(她告诉《纽约时报》,她的写作「经常与我对他们的爱发生冲突」)。
在意大利,距她的第一部小说出版10年后,她的第二部小说《被抛弃的日子》才正式出版。它的开头是——「一个四月的下午,午饭过后,我丈夫宣布他要离开我。他是在我们收拾餐桌时这么说的。」——将读者直接拖拽到即将到来的强烈情绪宣泄之中。
2013年,就在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出版后不久,《纽约客》的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写了一篇文章肯定费兰特的天赋:「她的小说强烈、激烈的个人化……它们似乎在毫无戒心的读者面前悬吊着一串令人血脉贲张的忏悔钥匙链。」「往往是惊人的坦率:虐待儿童,离婚,母亲,想和不想要孩子,性欲减退,身体的排斥,叙述者在一段传统的婚姻中挣扎着想要保持自己连贯的身份。」这些主题贯穿在那不勒斯系列的后三本中,这些故事的中心是一对同在那不勒斯长大的朋友——埃莱娜和莉拉。通过成为作家的埃莱娜的讲述,她们的友谊透过诸多人物的复杂关系得到展现,而这些人物之前的复杂关系也带领读者领略了那几十年的抗争、方兴未艾的女权主义与社会变迁。
因此,费兰特的书已经成为一种文学魔咒,尤其对女性而言——她们发现她笔下的情感是如此准确,又是如此真实,就仿佛从中看到了自己。
那不勒斯四部曲英文版
Q&A
Q: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A:青春期晚期。
Q:你说,有很长一段时间,你没有出版的意愿,甚至对别人会读自己作品也不抱期待地写作,那最初写作对你有什么作用?
A:我写作是为了学习如何写作。我想我有话要说,但每一次尝试都取决于我当时的情绪和心境。我觉得自己缺乏天赋和足够的写作技能。我通常偏爱第二个假设,第一个假设令我自己感到恐惧。
Q:你的小说总是关注女性生活,关注女性在私人层面和社会层面如何对男性作出反应。当你决定出版作品时,目的是为了对女性谈论女性经验吗?
A:不,那时我还没有一个计划,现在仍然也没有。当时我决定出版《讨厌的爱》的唯一原因是,我觉得我已经写了一本可以永久脱离于自己并绝不为此后悔的书。
Q:你的第一本书《讨厌的爱》和第二本书《被抛弃的日子》之间有10年的间隔,这个间隔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A:其实这中间没有间隔。在这10年里我写了很多东西,但我并不信赖它们。我写的故事满超负荷,很节制,其中却没有真相。
Q:你的书中很少有积极的男性形象,大多数男人要么是软弱的,要么是夸夸其谈的,或者是缺席的,霸道的。这是你所成长的社会的一个反映,还是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中两性的权力失衡?这种失衡近几年是否改善或改变?
A:在我成长的那个世界,人们会认为一个「男人」(父亲、兄弟、男朋友)以教育你、教你如何做一个女人以及「为你好」等等理由打你是很正常的。幸运的是,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仍认为,真正值得信赖的男人是少数。也许是因为塑造我的那个环境太落后了。又或者(我倾向于相信这点),男性权力——不管暴力地还是精致地施加——仍是执意让我们屈从。每天都有太多女人被羞辱,不仅仅是从象征层面上。而且在现实世界中,太多女性因为她们的不屈服受到惩罚,有的代价甚至是死亡。
Q:你的小说似乎关注很多边界——情感、地理、社会的边界——以及关注穿越或者打破这些边界时会发生的事。这种影响是否仅局限于特定年龄或阶层的女性?还是说适用于所有的女性?
A:对界限的意识对所有的女性来说都是重压——我谈论的是总体上的女性。当我们自我约束时,这不能成为问题:对一个人来说,自我约束是重要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别人设定的界限里生活,当我们不尊重这些界限时,我们也无法喜欢自己。男性突破界限不会自动导致消极的后果,反而会是一种好奇心或者勇气的标志。女性突破界限——尤其是没有男性引导监督的前提下,会令人无所适从:是一种女性魅力的丧失,是逾矩、堕落和疾病。
Q:你时常用词语「溶解」或「消失」指代一种情绪的崩溃。这是你在自己身上体验到的一种感觉吗?还是说从他人身上看到的?
A:我在我母亲身上,在我自己身上,在许多女人身上都观察到这种现象。我们体验过太多阻碍我们欲望和野心的束缚。现代世界常常令我们遭受我们有时无法承受的那些压力。
Q:小说的叙述者发现母亲这个角色很难。它吞噬她们,损耗她们,她们渴望逃脱这个角色,并且当她们这样做时,她们得到了解放。你会认为,如果女性不必承受作为一个母亲的负担,她们会更坚强吗?
A:不,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怎么对自己讲述有关母性和育儿的问题。如果我们继续以一种田园诗般的方式,像很多母亲手册里做的那样,当我们遭遇作为母亲会遇到的那些令人沮丧的事时,我们还会一直感到孤独和内疚。今天,一个女性作家的任务不是止步于(描写)怀孕的身体、生产和养育后代的快乐,而是要诚实地继续挖掘,直至它最黑暗的深处。
Q:那不勒斯系列在人物和情节上,与你早期的三部小说有相似之处。是否可以说在某些程度上,你讲的是同样的故事?
A:它们是不同的,但绝对都是同一种疾病的症状。生命的创伤是无法治愈的,你一次又一次地写下它们,希望迟早构建出一种叙述,能够一劳永逸地对它们作出解释。
Q:我们能假设那些故事就是你自己的故事吗——正如读者假设的那样?抑或可以说,这(种假设)只是代表了他们自身想象力的失败,即现代人总想在作品中寻找作者的蛛丝马迹的现象?
A:那不勒斯四部曲当然是我的故事,但只是在我赋予它小说形式,并通过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将现实注入文学这个层面上。如果我只是想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我会选择和读者建立一个不同的契约,即表明我所写的是自传。但我当初没有选择自传的方式,将来也不会,因为我相信,成功的小说能承担更多的真相。
Q: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决定要隐藏自己的身份——正如你所说的,要从出版和推销书籍的事务中保持「缺席」?
A:我相信,在今天如果不能通过保证自主空间,使之远离媒体和市场,来保护写作的话,将是一个错误。我自己小小的文化战斗,主要是和读者的战斗,到现在已经持续二十年了。我相信人们应当在署有作家名字的那本书里去寻找作家,而非从写作自身私人生活的那个作家本人身上去寻找。抛开文本和他们的写作技巧的话,剩下的将只有无聊的八卦。让我们重建书籍本身真正的核心地位,如果将来适当的话,再讨论将无聊八卦用于推广的可能性。
Q:你觉得名声总是会给作家的作品带来损害吗?还是说它对任何有创造力的人来说都会这样?
A:我不知道。我只是认为,如今让一个人变得比他的作品更出名是不对的。
Q:你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你是你小说的作者吗?如果你的小说作者身份被曝光,你觉得会有人因此不安,或给你的生活造成麻烦吗?
A:起初我担心我会给那些我所关心的人带来痛苦。但是现在,我感觉不再需要去保护我所爱的人了。他们知道写作是我的生命,他们让我待在我的小角落里。唯一的条件是,我不能再做让他们蒙羞的事情。
Q:你如何与你的英译者安·戈德斯坦共事?请你评估一下,你被翻译过的作品是否传达了你「真实」的声音?
A:我完全信任她。我相信她已经尽她最大的努力带着最大的善意让我的意大利语融入到英语中去。
Q:你的一个自我批评是有关于《被抛弃的日子》这本书的,你说你害怕它的某些部分可能是「虚有其表的好文章」。那么对你来说,「好」的写作和「真实」的写作之间有什么区别?或者至少,你觉得你最好的写作方式是什么?
A:精彩的文章就是,真实叙述的艰辛和快感取代了任何其他顾虑,包括对形式文雅与否的担心。我属于那类会否定终稿,宁愿保持粗糙原稿的作家,因为这样能保证更高的真实性。
Q:你说,今天谈论女性作家,「我们必须使用先进的工具,深入挖掘我们的差异」。还有其他作家这样做吗?你能举一些你喜欢的女作家或一般作家的例子吗?
A:名单太长了——饶了我吧。当下的女性写作非常宽阔,富有活力。我读了很多,我最喜欢的那些让我惊叹「我可绝对写不出来」的作品。这些作品让我「悔其少作」。
Q:我知道很多女性看过你的书后给你写信,男性会这么做吗?
A:起初男性比女性多,现在(给我写信的)女性的数量已经超过男性。
Q:当你终于出版了一本书,你需要一段时间的复原和恢复吗?你有休闲期吗?
A:不,我心里总是有事情让我烦恼,将它写出来才让我心情愉快。
Q:你曾经说过,如果现在公布身份,会是「非常可悲的前后分裂」。那你现在仍会感到来自成功的压力吗?当你走进一家书店或一个机场,看到自己的书被放在一整面墙上出售,你会有什么感觉?
A:我小心地避免遭遇这样的场景。出版总是让我焦虑。我的文字被复制成上千本,总让我有一种傲慢的感觉,这让我感到有愧疚感。
Q:你是否感觉你的身份正在逐渐浮出水面?对一些文学领域的记者来说,揭露你的身份将会被视作一个独家新闻。
A:独家新闻?真是荒唐的做法。除了书之外,谁会对我的其他东西感兴趣?对它们(书)的关注都似乎已经太多了。
Q:你提到埃莱娜——那不勒斯系列小说的角色之一,你说如果没有另外一个角色莉拉,她将成不了作家。对您而言也是这样吗?
A:我认为写作似乎是由我生活中与他人的偶然碰撞来驱动、滋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的,如果我变得无懈可击,如果其他人不再能让我陷入混乱,我想我会停止写作。
Q:你在写另一本书吗?
A:对,但是——现在——我怀疑自己会不会将它出版。![]()
《我的天才女友》
没看够?
长按二维码关注《人物》微信公号
更多精彩的故事在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