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语言:梁文道、陆川、金韵蓉、梁钰、曾焱冰想告诉你……
![]()
时间会治愈一切,阴霾总会过去,我们真的希望爱可以永恒,也只有爱,才能带给我们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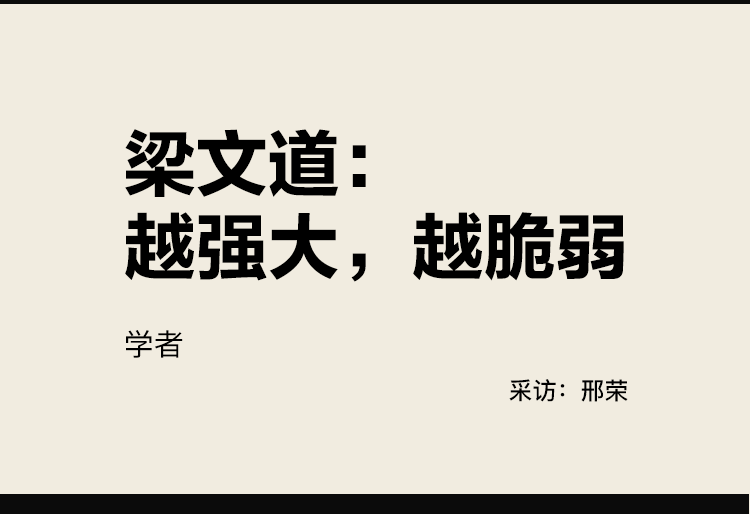

香港有实行严格的居家隔离措施吗?
没有其他省市那么严重,部分大楼会要求登记和测量体温,市面也没以前那么热闹,最近才开始人多起来,但我觉得随着海外输入个案多了,又会有转折。香港是一个比较靠自律的城市,大部分人自动自觉不出门,政府也带头,比如公务员起码有两个礼拜是在家上班,春节之后,虽然没有行政命令,很多公司也自动自觉跟进,调整上班时间和工作方式。
疫情期间,你的日程会怎样调整?
有一些工作被取消或延后,比如上半年安排的一连串线下活动。但作为互联网公司,我们反而有些工作比平常增加了,我的一档音频节目,有一整个月的时间是每天更新。以前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年出行,是一个搭飞机肯定比搭公交多的人,平常一星期至少要坐两趟飞机,而最近这个月都没去过机场,这是十年都没有过的经历。我发现,原来很多时候也不用到处飞,很多东西可以在家完成。
同时,因为一直在家,我陪家人、陪我家的小猫的时间也比平常多了。我家的猫因为癌症,今天下午去世了,在它生命最后这两个月的时光,好在我能天天在家陪伴它。
意外增加了在家的时间,这对与家人相处会有什么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
我想起来一个笑话,因为我学佛,一位法师曾经说过,很多学佛的人学了一会儿,就觉得我证悟了,但你要测试自己是不是证悟的最好方法,就是跟家人一起住一个礼拜不出门。
家人是至亲,但事实上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大城市的人,大多是离乡背井在异地生活和工作,跟家人的圈子几乎是完全隔开的。过年我们回到家里,如果只有几天,还可以保持当年在家的状态,但再久,就勉强不来了。夫妻间也是,平时大家各自出门工作,每天相处的时间有限,但当这种状态被打破,大家都会遭遇一些困难。
最近一些经典著作被关注,比如《鼠疫》《枪炮、病菌与钢铁》,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我觉得很好,我最近也有介绍其中一些作品,因为它们跟我们眼下的疫情有间接或直接的关系,也说明我们今天面对的,不是人类历史上完全崭新的挑战,那么前人的经验和想法,对我们会有帮助和启发。这就是经典的作用,历久弥新。
你觉得阅读在这种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力量呢?
阅读,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你沉浸其中的时候,把你从眼下的现实抽离出去,暂时逃离熟悉的环境。当你合上书,刚刚书里面那种陌生感也随之回到现实世界,于是你看待你的房间、你的家的眼光会不一样。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奇妙感觉,刷新你对本来生活的场景的体验。
最近这段时间有读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书吗?
有一本小说蛮有意思的,我很喜欢,叫做《罗盘》,是法国小说家马蒂亚斯·埃纳尔的作品。
从非典到H1N1,再到这次的新冠肺炎,你觉得我们在应对疾病的方式上面有变聪明吗?还是一点进步也没有?
当然还是有变聪明的,比如我们中国人面对这种呼吸道传染病,本能反应就是找口罩,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这都是我们之前积累的经验。但是说全面的进步,坦白讲不一定。但我们又面临更危险的处境,因为互联网时代很多的假消息和谣言被更广泛地散布,这些是当年我们不曾面临的危险。
面对这些新的危险,我们要怎么应对?
我通常给他人的劝告是我们慢一点。我们每天获取的信息量比17年前多得太多了,看到一个消息,我们很容易不由自主地相信它,然后转发、评论和分享,但其实并没有能力,也来不及查证这些消息的可靠程度。所以我们至少可以慢一点,忍一忍,不要让自己随便成为从众的人。
SARS、H1N1、新冠肺炎,经历这三场疫情的心态和方式,有什么变化?
变化很大,因为SARS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传染病,当时做了十来年的媒体工作者,我很容易把它当成职业挑战,从工作的角度去处理,需要自己保持客观和抽离的状态。H1N1的时候,我被感染了,在家禁足了十几天,虽然不算严重,很快就治好了,但我有了一个亲身体验的经历,更懂那些身在其中的人的感受。这一次,因为既有站在局外作为媒体人的视角,也有亲身经历的感受,我的心情会更复杂一些。
作为H1N1的亲历者,那段经历带给你一些什么思考?
当时一开始觉得挺爽的,因为病情不太严重,治疗得很好,除了头两三天发烧,之后就是在家恢复,所以就好像多了一整段时间名正言顺不用出门,不用去电视台做节目。但慢慢地,我就开始想,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幸运,两星期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别人会承受多大打击?所以这次疫情,我特别关注这样一群人,他们手停口停,如果无法正常工作,怎么生活?他们是不是有防护装备?那些被迫流落街头的人怎么办?环卫工人怎么办?这不仅仅是出于感伤或同情,社会里的人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的生活跟他们也不是完全隔开的,如果他们受到感染,这个瘟疫会不断蔓延,最终影响所有人。
同时我也会想,我连自己是怎么感染的都不知道。在病毒侵袭的时候,我们完全出于无知和被动的状态,生命那么脆弱。
有时候似乎觉得人类好像很强大了,能够制造飞机、火箭、人工智能,但是现在这种时候,脆弱感就又被带回来了。
没错,甚至有时候我们越强大,现代社会越发达,说不定在某些程度上比以前越脆弱。比如这次就让我们看到,全球化在带给我们各种好处的同时,也使我们变得多么脆弱。1918西班牙流感,花了很长时间才达到全球规模,但现在疫情传播的速度是这么快。
之前我们担心经济问题,担心没办法复工复产,国外产业链要转移,但现在我们复工复产了,人家没有订单给你。许多地区想自己生产口罩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么一个看起来简单的商品,却因为一种材料需要进口,就是做不出来。而看起来先进的电动车,就因为其中一个零件要在湖北生产,全部生产线都要停工。那么,全球化的意识是什么?就是我们彼此依存,让经济生产的效率和规模不可和以前同日而语,但也会在遇到危机时,一个地方出现纰漏,就大家一起瘫痪。
你觉得这次疫情后,全球化浪潮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如何发展?
目前来看还很难讲,因为现在反而是我们每个人要做决断的时候,每个国家、每个机构、每个人,做什么,都会影响最终的走向。如果全世界都可以在这场疫情里面,迅速从其他国家获得经验,去处理自己的问题,如果大家可以在自己行有余力的时候,向别人伸出援手,我们就可能走向好的一面。
之前网友说,2020年就是勾掉所有目标,只留下一个——“活着”。你觉得是一种调侃,还个很现实的目标?
我觉得非常现实,它听起来像调侃,但坦白讲,人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我们要学会跟日益增加的风险共存,也需要学会利他,要考虑其他人,尤其是面对传染病,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表面上跟你没有关系的一个人,他完全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怎么做才能避免自我思维的膨胀呢?
从个人来讲,就要有更宏观的视野,想象他人痛苦跟处境的能力,这是一种共情的想象力。对这种能力的需求,已经越来越迫切了。
记住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一个最老生常谈的东西,就是我们有没有在自己犯过的错里学懂东西。马克思说,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是悲剧,发生第二次就是闹剧。但我们总是会这样子重犯历史上犯过的错误。以前我读历史,老师说我们学历史是为了见古知今,是要学懂,不要犯第二次错误。
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看人类的发展?
对人类的未来,我一向比较悲观,但我也总觉得还能做些事情,至于做这件事情的背后,是不是怀有什么希望,那倒反而不是,更多也许只是因为责任。就好比坐在一艘轮船上面,既然看到前面有一座冰山,就该不顾一切去发出警告,试图改变航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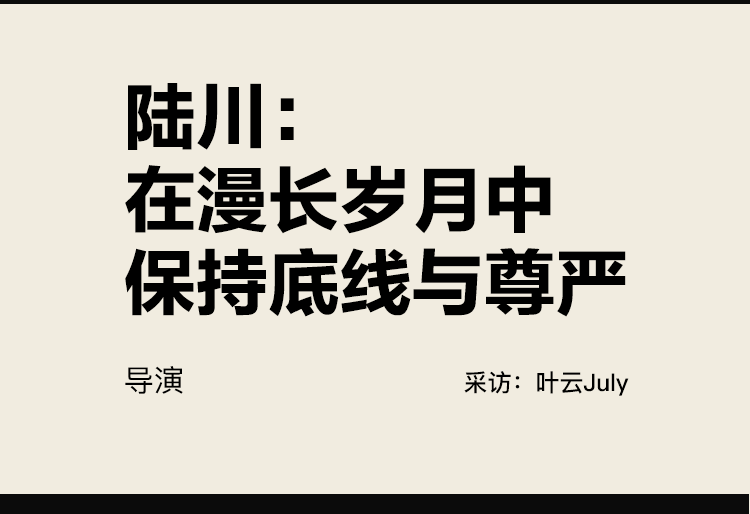

毫无疑问,疫情的爆发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节点,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是沉重的一击,强制人们重新思考关于真相和责任,关于自然的启示。
最近我也逐渐复工,继续完成新片《749局》的后期,时常,我感受到一种近乎压迫感的关联性。剧本是几年前写成的,筹备两年,拍摄共九个月,2018到2019年间,我在重庆花了两个多月去组织拍摄“封城”“大撤离”“空城”这些场面。
电影杀青后不到半年,就在新闻中看到了极其相近的镜头,心中悚然。
这部片中有我自己的青春记忆和成长印记,有关我第一次踏入军校,第一次进入数字局工作的经历,但那时因为动作场面很多,每场戏都拍得费时费力,大结局部分更难,包含了六个动作段落,其中在749某实验室楼顶的一场戏,动作组整整拍了两个多月都没有过关,差点抑郁。说这些和自己较劲的过程,在于这是少年马山在追寻自我的途中得到了真正的成长。
这一场疫情,让很多人也慢下来思考生命和死亡的问题。很多事情,无论时间过去多久,都不会被忘记。我总是怀念拍摄《可可西里》的日子,就像一场战争。亓亮非常虚弱,差点昏倒,松永措是一直打点滴坚持拍戏,我就是掉头发,一头秀发所剩无几。这部戏也损害到了我的心脏。我们当时只想努力地去为中国电影做一部不一样的电影,想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一笔。
写《黑洞》剧本时,我在一个小旅馆里被关了一个月。构思剧本的时候,贴了一墙的纸条。纸条上大概有一百多个人物的名字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情感关系,阴谋算计。写到后来这些东西全在脑子里了。每天打一万多字,写到最后一集就不行了,没吃什么就呕吐,喷在电脑上,送到医院被诊断为植物性神经紊乱。
通过这些回忆再反思今天面对的问题,似乎都有迹可循。
我有个深刻的感受,这场疫情给存活在地球上的这几十亿人,上了沉痛的一课。
不断出现的灾难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似乎是一种强制性调节机制,这么想,或许可以让自己保持心安。
说句大实话,大多数人的责任是过好日子,保护好自己的家庭和钱包。反思和记录,真相找寻注定是少数人的事,高风险的事,是拿健康,甚至生命来换的。
每个人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也是一场考验,能在漫长岁月中保持底线、尊严、品格,也很难,甚至更难。
上映于2011年的电影《传染病》,还有2013年的《流感》,最近被大家重新拿出来回看,因为有太多和现实几乎完全吻合的情节,观众今天也是意图在电影里寻找真相和科学。《传染病》是根据SARS的事实改编,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灾难是有可能卷土重来的,人类的错误也可能会重蹈覆辙。
事实是,疫情确实会改变很多事情,但没有必要恐慌,也没有必要纠结,因为人类有自己强大的惯性,人类的成长总是因为惯常的思维和轨道而受到阻碍。人类对伤痛的记忆也是最靠不住的,疫情结束不用几个月,大多数人肯定会对那些还在喋喋不休讨论疫情伤痛的人投以狐疑的目光。
身为电影人,我们肩上的责任就是把真相嚼透了,再把本质“变成”电影,给观众思考也好,希望也好。我之前说,拍电影是给有执着追求和理想主义的人,简单说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次疫情从北京派往湖北的医护人员、专家、防控人员,有一些是从汇文中学英雄班出来的。时势造就英雄,在抗疫的特殊时期,在前线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医务人员、记者、志愿者等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也是汇文毕业,上的就是这个英雄班,有和英雄们站在一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曾经给《长江日报》在武汉的记者詹松写过一封信,向他们致敬。
最近疫情在世界各国都有蔓延,在外工作留学的很多华人都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他们的困境。不要犹豫,向全世界各个惊慌失措陷入灭顶之灾的疫情国家输出我们的医疗援助队,输出我们的医疗物资,输出我们的抗疫经验,把拯救世界拯救世界人民的责任扛到自己的肩膀上。
你会发现,这是建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国际形象的最好时机。你会发现这是对全球华人最好的支持。比打任何嘴炮都重要。中国有句老话,事实胜于雄辩。
我们先要对自己人人道,别人对我们才会人道。向外,是大国输出的责任;向内,是每个人对自我成长和生命的交代。
或许,疫情带来的很多人精神上的创伤,还会持续更久。其实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被治愈的——时间可以治愈一切。我发现,很多事和时间相比,胜利者永远是时间。不过,我真的希望爱可以永恒。
隔离期间,我经常去父母家蹭饭,陪着父亲喝点小酒,边喝也边讨论着父亲的小说和我的剧本。也终于有时间给儿子上英文课,陪他玩。
等疫情过去后,我希望可以偷偷揣一瓶啤酒,坐在电影院里看一部爽片,和兄弟们聚一聚,好好喝场大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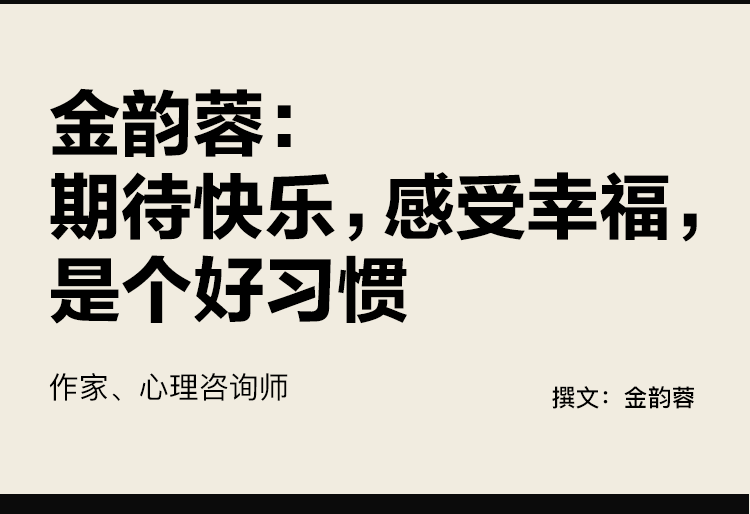

坦率地说,即使在病毒还没有来袭之前,我们就已经生活在一个很难与之对抗的集体焦虑情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突然变得很难容忍前面开得稍微慢一点的汽车;进了电梯,哪怕外面还有人却不由自主地伸手按关门键;看见孩子各种慢吞吞的拖沓,就控制不住想大声吼叫;也已经很久没有办法再静下心来读完超过千字以上的文章。
让人措不及防的疫情又试图在我们已然焦虑的情绪上叠加了愤怒和恐慌。还好,观看历史,人类素来拥有在逆境中扭转乾坤的生存能力,也总是能在看似前路已断的困境中转个弯,又发现柳暗花明的突围小径。所以,病毒也许可以一时掌控和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情绪,但经此一役之后,我们又夺回了情绪的掌控权并更好地生活着,这就是击溃它和对它最好的震慑。
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怎么才能夺回对情绪的控制权并更好地生活。
首先,我们要允许坏事有可能发生。
允许它,并不表示我们束手就擒,不反击,不作为。允许,是不逆势而为,不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困兽之斗,以免消耗更多无谓的精力,并进一步造成原本可以避免的更大损伤。允许,是豁达的释然,但又有勇气对天对地对自己说:是的,我知道它发生了,我看见了,我感受到了,但它不能再对我造成第二次的伤害。
大部分的人都会在经历创伤后出现愤怒的情绪:“为什么是我?”“为什么那么不公平?”“为什么我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没有发现端倪?”……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愤怒像创可贴一样暂时盖住了伤口,让我看不见血肉模糊的自己,也感受不到那深入骨髓的疼痛、恐惧、孤独或羞辱。一天一天过去,那伤口还是提醒我所受到的伤害,并操纵着我的情绪。
所以,允许,是积极的心理作为,是在伤害发生后敢于直面伤痛的停损机制,也是不被坏事或厄运俘虏的第一道防御工事。
接着,我们需要筑起第二道防御工事,那就是对自己承认这些伤害所带来的负面情绪是真实存在的。
很多时候,我们故意不承认我们有负面的情绪,是因为它会让我们看起来太脆弱,或者是还无力面对。所以我们用尽力气把它隐藏在心里的某个角落,故作无事状地告诉自己没有这回事。但让人恼怒的是,这些看起来被隐藏得很好的情绪并不会安静地在角落呆着,它反而会用各种方法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而且我们越不理它,它的动静就越大。
我在医院的心理卫生中心工作时,常被内科医师请求到病房会诊。很多病人临床上确实表现出了身体的疾病症状,但在经过各种医疗仪器反复仔细的检查后却找不到病灶。这些让各科医师头疼不已的病症,有个心理学上的优雅名字“身心症 ”(Psychosomatic),也就是病人的身体不适并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它纯粹就是因为那些求助无门,只好到处闹腾的心理情绪所造成的,而且根据世界心理卫生组织的统计,大约70%以上有情绪障碍的人会以攻击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郁结。
所以,“允许生命中坏事可能发生”的第一道心理防御工事构筑之后,还需要通过“承认它所带来的情绪”这第二道防御工事来加强围堵它的工作。
接下来,就要利用把这些负面情绪用合理的方式给发泄出来,做好第三道的歼敌工作。这是我们启动自我疗愈的重要阶段,但是它在战术上还是有些讲究,需要有军事长才的战略和技巧。
把坏情绪赶走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大声嚷嚷”,没错,就是尽可能大声地公告周知。情绪是我们身体里最大的一股能量,既然情绪是物理学概念上的能量,我们就要用物理学的方法,也就是利用相同或相似频率的能量彼此之间产生共振,来撼动、瓦解,进而释放它。实验证实,当我们大声喊叫时,50%的声波会经由耳骨传送到体内的硬组织骨骼里;而剩下的50%声波,则会随着声带传送到身体的软组织血液和脂肪组织里。这两股声波会分进合击,跟体内的情绪能量,尤其是愤怒的情绪能量产生共振,然后像动画片里的大块黑乎乎的邪恶岩石一样,慢慢地出现裂痕,最后轰然倒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高山上或大海边对着空旷的远方大喊几声之后,会觉得身心舒畅的原因。不过,我在前面提到了需要用“合理的方式”,而不是随意地对着先生孩子或餐厅服务人员大声咆哮。有时候,我会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选一部一定会让我悲伤或开心的电影或美剧,一面看,一面大哭或者大笑;或者在家跟着MV唱歌,专挑那种调子太高根本唱不上去的歌,每当我声嘶力竭地唱完之后,脸上也早已布满冲刷掉了坏情绪的泪水。
把坏情绪倒空之后,接下来就要把腾出的空间让给理性的、积极的好情绪了,这个步骤也是我们向坏事进行绝地大反攻的最辉煌的战役。
我很喜欢英国诗人、思想家John Ruskin的一段话:阳光令人愉悦;雨水令人清醒;风声令人奋起;雪花令人欢快。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坏天气,只有不同的好天气。
这就是“期待快乐”的好习惯和“感受幸福”的能力。记得我在医院从事心理治疗工作时,同事们和我都最烦在节假日之后的第一个上班日在门诊当值,因为那天门诊一定从一早开始就大排长龙,节日越重要之后来看诊的人就一定越多。这个现象我们称为“节后忧郁症 ”(Post -holiday Blues),是那种因为期待了好久或计划了好久的节日终于过完了,欢乐之后的曲终人散最是叫人神伤。因此,许多人为了害怕失望就干脆放弃行动,他们不结婚,不要孩子,拒绝过节,甚至拒绝快乐。
我的一位已独居五十多年、膝下犹虚的英国老师,日子过得简单但不悲戚。她曾经告诉我:“如果你失去了期待快乐的信心,那么就再也没有人或事能让你快乐的了!”这句话我一直牢牢地记着,在每一个艰难时刻,都用它来为自己打气。所以,如果在因疫情肆虐,而不得不失去珍爱、健康、自由或信心的时候,我们最后能为自己扳回一城的方法,就是启动谁也夺不走的“期待快乐”和“感受幸福”的能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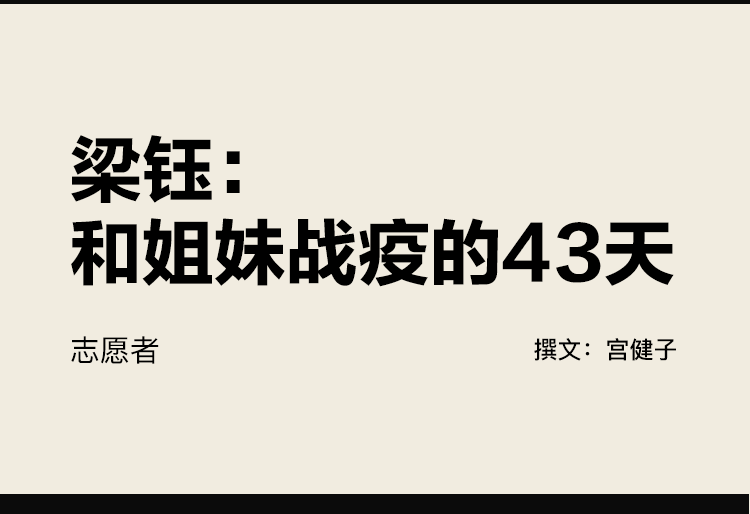

250万的捐赠金额,60多万条安心裤,30多万条一次性内裤,十几万片卫生巾,还有一万多支护手霜……湖北疫区一共1000家医院,覆盖率近五分之一。
姐妹战疫,作为疫情其中一个小小的民间志愿者团队,让很多人听到了她们的声音,看到了她们的行动。
回想最初的几天,梁钰和她的“姐妹行动组”一共只有三个人。如今的志愿者组织结构图上,有不少人的名字后都标上了“已退休”。
3月18日20:29,梁钰更新了微博:“我们的海南方舱妹妹平安回家啦!妹妹真的很棒,收起长发,穿上棉衣,瞒着爸妈支援武汉,工作强度超大,出发太急物资没准备充足,月经期血和尿混在一起也从来没有在战场叫苦退缩,妹妹是战士!”
这是梁钰发起“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第41天。随着各省援鄂医疗队的分批撤离,前线抗疫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而梁钰的微博依然坚持更新捐赠状况的每日公示:“截至3月19日22:00,#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募捐及协调捐赠共计:安心裤613,305条、一次性内裤320,883条、卫生巾160,776片、护手霜10,852支,覆盖205家(支)医院和医疗队,超84,500人。”过去的一个多月中,公示图里的捐赠名单不断拉长,地图上收到物资的医院越来越多, “配送中”的数目逐渐清零,团队捐赠通道正式关闭。
关于姐妹战疫的起点,梁钰坦言没想那么多,就是同理心唤起了她。“我看到女医护穿脱防护服的视频,下意识地就会觉得她们穿那么久,那来月经怎么办?”
2月6日她在网上询问了一圈,发现没有办法公开募款,就单纯地想是不是可以自己捐一些。之前捐过物资的朋友帮梁钰联系了一处医院,2月7日梁钰在淘宝上一家家寻找从湖北发货的店家,表明采购物资的意向,问对方是否愿意发货。终于,有一个商家同意了。梁钰一度以为,这里就是这件事情的终点了。
刚开始不知道事情的严峻,以为几万块的规模还可以捐一些医院,但当梁钰通过朋友联系到了当地的工作人员,发现物资缺口实在太大,她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原来不只是医护人员,病患也需要安心裤。新冠肺炎患病过程中,一直发烧打针躺着,整个人虚弱无力呼吸困难,更别说起来换卫生巾了,人非常容易感染。”
通过微博发声,很多想要捐赠的企业和个人找到梁钰,工作量一下子爆增。2月8日晚上,小熊和莓辣性教育平台的色阿加入,三个人前三天一共统筹了定点捐赠的71万元的物资,超过11万条安心裤,覆盖到了武汉、黄冈、孝感的20家医院。
征集需求,找商家,找车队物流,联系医护,跟踪接收,所有的事情都是梁钰和志愿者团队自己来。最大的压力不是物资的数量,而是情况瞬息万变,需要做太多沟通。比如说前线对接的医护人员,手机可能被消毒液泡坏了,突然两天没有消息;也有医院突然说,他们要上去现场,没有办法来接收,而梁钰他们组织的物资运输车辆正在路上……各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
共情也是一种消耗。梁钰回顾道:“在电话里我们会听到她们很繁忙的现场,特别是听到姐妹们用乐观的语气和我们说前方的情况,还很小心翼翼地,怕麻烦我们。”前线的医护人员也在这种为数不多的对外联络中释放着交流的渴望。“今天有人给我们捐泡面,好开心!”她们给梁钰她们发来用紫外线灯照射防护服消毒的照片。“这样晒一下,防护服又可以多用几天。没有卫生巾没关系呀!我们克服克服就好啦!” 这些来自一线的声音,让梁钰和她的伙伴们特别心疼,简直没办法想象“不穿内衣内裤”“血和尿都混在一起”,她们只能尽可能多地筹集物资,尽快送到前线去。
姐妹战疫队伍的壮大,是在一种非主动和极大需要的情况下展开的。“担心事情变得复杂,但疫情还在继续,发现的物资缺口也越来越大,要保证物资尽快到达姐妹们手中,公开透明地把这件事情做好,只靠我们几个实在力不能及。”
在前期,三个人面对巨大的工作量,到了晚上12点才吃上一口饭,几乎没有时间睡觉。志愿者小熊则是一边忙着敲电脑,一边让妈妈给她喂饭……
2月10日,梁钰第一次在微博上发布了招人的消息。上万条私信一下子涌进来,她会选择特别主动热情、非常愿意争取机会的人。“志愿者的工作相当于996,最重要的是爱有多强烈,因为不够热忱是撑不下去的。”在对接组志愿者的招募中,梁钰更是有意识选择了抗压能力特别强的,去面对来自一线的信息。
2月14日晚,“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一期志愿者招募正式结束。此前的一篇招募公告中,梁钰详细列出了每一个组的主要任务和要求,分为对接组、信息组、媒体组等,其中信息组的工作任务是“与物流组对接核实物资物流情况;与对接组对接核实医院对接情况;与募捐组对接核实募捐款项运营;为公示组提供准确无误的数据。”
团队搭建完成后,九个组同时工作,每组都设置有详细的工作规范和流程,甚至统一的作息时间。梁钰在每个小组跟进,做汇总决策。“我们所有的人都很担心,每天都有可能出意外,基本上真的是每天都在出‘意外’。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所有的人都是时刻精神紧绷。”
在每日更新的数据中,团队出过一次错误,数多了404片卫生巾。3月6日,梁钰在微博上发布第二次公告:“在2月11日的公示进度中,我们将7,800片卫生巾误写为7,880片,将324条安心裤写为324片卫生巾。我们在次日公示中已经进行了勘误,并承诺由志愿者团队自行向一线再捐赠80+324=404片卫生巾,以弥补公示的首次失误。捐赠于3月5日送抵一线,现进行公示。如果未来在工作中有任何纰漏也会第一时间向公众解释,及时改正。”
梁钰微博的照片墙已经被长长的蓝色公告海报占满,密密麻麻,包括数字、表格、地图、饼状图。几乎能够在上面找到一切想要了解的信息。梁钰和团队觉得“做了什么就应该告诉大家”,“做事透明比漂亮更重要”。
3月7日晚上10点半,志愿者们截下一张实时地图作为行动满月纪念:大家的头像带着橘红色定位标志分散在世界各地,像一团团跳动的火焰。在自己的“工作回忆录”中,对接组的组长Doris写道:“想到最近看到的一首诗: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我由无数的我构成/这是多么开心的事/我由无数的他者构成/不要哭。”


2020年开篇是艰难的,但这段艰难的时光也给我们很多内心的启发。不管家是大是小,是奢华还是平凡,在这个屋檐下,我们在一起,互相保护着,紧紧地在一起。
每年春节前,朋友都从南方寄来两箱漳州水仙,这种号称“凌波仙子”的水仙花沉睡在泥土中时,是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土坷垃,扒开土块,洗清尘埃,才得见它白而透着青绿的球茎,摆入深盘,放在阴凉处,慢慢浇水,等待它抽芽,长出繁茂的花苞,然后盛开。
而今年,这些水仙并没有在春节期间盛开。它的花期足足晚了两周。朋友抱歉地说,也许是被假水仙骗了。我说不是的,是它比较晚熟,而且善解人意。恰是在因疫情禁足后的两周,家中花瓶里所有鲜花都已经凋零的时候,它绽放了。“芳心尘外洁,道韵雪中香”,这绽放的翩翩凌波仙子,给这寒冷而让人心碎的2020年早春,带来了无限生机,让紧闭的家门内,有了浓浓春意。
也是在这个早春,因肆意的病疫,我们不得不禁足在家,而对“家”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仅仅是这一盆水仙花,还有女儿种的多肉,家中栽种的蝴蝶兰,以及陪伴了我们十几年的阳光榕,都像通晓人情一样,在屋内温暖的阳光下抽出新芽,绽放花朵。
植物予人的是生命力,是希望,也是陪伴和慰藉。与植物一样安抚人心,并给生活带来趣味的,是家里那些平日收藏的艺术画作。
在我的书桌前,是一幅法国版画家艾斯黛博(Estebe)的小版画,美柔汀技法让黑白效果的小兔子格外细腻温柔,画面中唯一的色彩是橙色的小小胡萝卜,一张可爱的小画也是送给属兔的女儿的生日礼物。左边是一幅从德国老书店淘回的植物绘画,我爱植物与花朵,爱一切相关的艺术画作。与它相邻,挂放的是南京艺术家卞少之的水彩画《蓬莱松》,笔触轻松灵动,水色流动间,是一种潇洒的情怀。卞少之是获得过英国约翰莫尔奖的中国画家,也是我的朋友,我在他的画展上收得这幅小画。同时收藏的还有另一幅油画,画面上是一匹木马和骑马的国王,背景远远的是中国水墨意境的山水。我第一眼就爱上了这幅画。少之对它的解读是:即使是国王,踏遍千山万水,还是赤子之心。
家里的墙壁上、条几上、空白墙壁前,都有我爱的画作。这里面还有冯君蓝的那幅作品《草芥》、画家尹齐的版画《狗》、日本版画家铃木隆太的多幅版画作品,还有我的老师,水彩画家黄有维的水彩画《雪山》等等。当然这里面也有我自己的拙作,对绘画的喜爱让我也开始研习水彩,而这些是长久的精神滋养,无论外界风雨交加,病疫肆虐,都让人可以安居于室,平复心境。
作家马特·海格曾说,“不要相信什么好坏、输赢、胜负、高潮低谷。在你的最低处和最高处,无论你是快乐还是绝望,平静还是愤怒,都有一个最核心的‘你’是始终不变的。这个‘你’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这个最核心的“你”便是一个人内心积攒的能量,它来自对生活的热情与信念,对他人的爱,以及细细碎碎的情趣与爱好。这一切交织在一起,让人在艰难和厄运面前依然有所憧憬与依托,可以为痛苦在现世中寻找到出口与治愈的良方。
在可以“治愈”我们的良方中,美食更是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位置。这次因疫情而来的禁足闭关的日子里,每日三餐,显得格外重要。
我的日常作息是早上四点半起床,享受无人打扰的独处时光。写作、画画或冥想。八点多,随着女儿初醒朦胧的呼唤,在亲吻她之后,便开始准备早餐。
法式吐司在清晨的阳光下是金灿灿的颜色,同样闪光的还有松软的美式炒蛋、香肠和新鲜的橙汁。如果前一晚恰好卤了牛肉或炖了鸡汤,那一碗香喷喷的牛肉面或鸡汤馄饨也会格外动人。
平时的一天,我们有大部分时间会各自在公司、学校,有时有应酬、课外课程,有时还会出差,一天算下来真正面对面相处的时间,清醒时候的,最多也就五六个小时。但现在,是一天24小时的相处。在这段漫长的宅家时间中,也让人感觉到了一种久违了的温暖。就像自己小时候度过的那些假期时光,也是一家人凑在一起,每日三餐围坐餐桌旁,热烈地聊着有趣的事,分享着八卦和故事,和彼时的灯光一样温暖,是心底关于家的底色。
很多年以前,我写过一本书,叫《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这个书名后来变得耳熟能详,也成了人们爱用的示爱语。这句看似平平常常的话,却戳中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让人们开始从一个细小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生活和情感——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表白,而是温柔温暖的相伴,吃饭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和更精彩的日常。
一张餐桌的意义,也不再只单纯是美食的承载,它还变成了人们沟通、表达、社交的舞台。这不仅仅是指在奢华的晚宴或热闹的聚会上,即使日常的一餐,也有同样的意义。
当我铺上美丽的桌布,用手边的鲜花、小装饰物布置好餐桌,摆好与菜肴搭配的餐具和闪亮的酒杯,有精致的筷子架和平整的餐巾布,女儿会兴奋地奔去找出蜡烛,点燃它,散发出摇曳的光芒。
是的,即使日常的晚餐,这样小小的仪式感也会给家人带来幸福。我们用鲜花、美食和种种奇思妙想装扮出的餐桌,不是为了炫耀昂贵的器皿或自我炫技,而是通过它,表达出对用餐者浓浓的爱意与关怀。
当女儿长大后,她会离开父母和父母为她营造的这个家,去过自己的生活。也许有一天,她身处逆境的低落,或正经历人生中成功的喜悦,在她举起酒杯、点亮蜡烛的刹那,也许会想起这一刻我们在一起摇曳的烛光和碰杯时清脆的叮咚声,会回忆起这温暖相聚的时光,这些温暖的底色,会成为她克服困境向前走的动力,成为她发现并享受生活中美好的能量。
2020年开篇是艰难的,但这段艰难的时光也给我们很多内心的启发。不管家是大是小,是奢华还是平凡,在这个屋檐下,我们在一起。门紧紧关闭着,一切危险都被挡在外面,冰箱里有满满的食物,床上有温暖的被褥,我们还可以和爱的人、爱的一切在一起,互相保护着,紧紧地在一起。
编辑:张静Mia Zhang、朱凡Juvan Zhu、叶云July Ye
美术:罗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