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国公司正将鞋盒大小的卫星送上太空
本文刊载于《第一财经》YiMagazine 2019年3月刊
记者 | 叶雨晨
编辑 | 华薇薇
高恩宇的微信头像是一粒漂浮在宇宙中的水滴,这是刘慈欣所着的科幻小说《三体》里的致命武器。他喜欢穿一件藏蓝色的飞行员夹克,这件衣服设计的特别之处在于,胸口处有一枚尼龙粘扣,可以随意粘贴不同的徽章。这也是他每回去酒泉发射场观看卫星发射时的战服,徽章会随着每次发射卫星的代号不同而变换——为每一次太空任务专门设计制作任务徽章是航天人的传统。

2017年8月,他创建了卫星公司微纳星空。这是一家从事微纳卫星系统研发制造,自主研发微纳卫星平台和核心组件的航天科创公司。2018年,微纳星空成功完成了3星交付发射,并于同年12月获得近亿元的战略投资。在创业之前,高恩宇在中国航天系统从事火箭、卫星的总体设计。
微纳星空的办公室位于北京西北郊的中国航发大厦,这里距离中国航天的“神经中枢”北京航天城只有一站公交车的距离。微纳星空拥有3间联通的实验室,在最里面一间需要无尘操作的实验室正中,摆放着一颗正在总装测试的卫星,星上软件测试也在同步展开。
上天之前,每一颗卫星通常需要24小时不间断地在实验室运转小半年的时间,以便抓住瞬间闪现的软件故障进行修复。之后还要再经过一组模拟火箭发射和太空环境的硬件系统测试,才可能最终完成卫星研制,运送到发射场,装载在火箭上发射。在到达指定轨道后,这颗卫星每天将有两次机会飞跃中国国境,这时候还需要通过遍布全国各地的测控站传回卫星信息,以监测卫星的稳定性,并传回数据用于科学研究。
自苏联和美国于60年前开始将火箭送上轨道以来,人类和太空之间的关系正在以无法预见的方式发生变化,而人造卫星是目前发射数量最多、用途最广、发展最快的航天器。

不同于以往人们对于卫星的认知——正常卫星大约有一辆公交车那么大,重量大约有3200公斤——微纳星空的卫星体积仅一个鞋盒大小,重量在10公斤左右,被称为“微纳卫星”。过去几年,美国卫星公司Planet Labs已经将鞋盒大小的数百颗卫星发送到绕地轨道上,并命名为“鸽子卫星”(Dove),每颗卫星都搭载了经过编程的高倍望远镜和摄像头。它们被送入轨道,组成庞大的卫星群,用来观测地球的不同区域。
卫星制造公司通过生产、销售卫星实现盈利,卫星运营公司借助卫星群送回的地面影像图和数据开发出了更多的商业模式,比如对冲基金拿来观察大型商超门前的停车位,以评估购物旺季的客流量;农场主会用来评估农作物的健康状况,预估理想收割时间;间谍们用来监控军事扩张和跟踪活动。
多亏了现代软件、人工智能技术、电子工业和材料的进步,以及一代雄心勃勃、立志打破常规的企业家,以卫星为核心,贯穿卫星发射、卫星制造、卫星运营的产业链已经开始在中国形成。2018年,中国商业太空领域出现了两百多家卫星公司、火箭公司、载人飞行公司。与此同时,原有的老玩家也纷纷获得新融资,并且兑现了讲过的故事,2017年中国发射的商业卫星数量只有8颗,到了2018年已经发射了40多颗。
确切来说,这轮卫星发射热潮得益于国家的政策红利。2014年《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发布,在军民融合政策的影响下,2015年出现了第一批民营航天公司。曾经资本因为投入周期长、资产重对这个行业望而却步,但在大洋彼岸,一场卫星小型化的浪潮早就在旧金山湾区和加州山景城之间发生。Planet Labs、OneWeb等创业公司因为微小卫星研制周期短、研制成本和发射成本低、发射方式灵活等诸多优点,打破了过去几十年传统航天业的固有商业模式,也让中国的投资人开始对这个行业有了兴趣。
“传统的卫星造价也要超过几亿美元了,但对于我们这些卫星应用公司来说,是否能在轨运行十年并不重要。我们希望卫星既便宜,又可以标准化,如果10颗小卫星通过组网可以实现,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张弓说。他曾经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负责气象和遥感数据处理,现在是创业公司佳格天地的CEO。这家公司通过购买和合作两种渠道获得空间遥感卫星的数据,用以实现对农作物耕种面积的预测、适宜区规划、自然灾害和病虫害的预测预警等,进而通过农作物的估产延伸至农业保险费用厘定、农业贷款评估等金融服务。
对于一家初创的民营卫星公司来说,从小卫星做起意味着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研发周期。
卫星本质上是一个计算机,通过星务、电源、测控和数传、结构、热控和姿轨控六大系统,来感知当前的方位、温度、太阳的位置,调整自身的工作方式,就像一辆漂浮在太空中的自动驾驶汽车。想要产品化必须像Planet Labs一样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卫星平台,把卫星制造从体制里的定制化生产改造成工业化生产。
2017年年底,微纳星空拿到了第一颗卫星的订单,这是一颗以科研为目的的10公斤级卫星。卫星的研发总共花费了10个月,首先需要通过电性星验证几个单机零件是否匹配,把软件跑通;之后再做一套初始样件,对这台与上天的卫星差不多的设备做“过实验”(overtesting,过度实验),在温度、速度、重力作用等极限状态中测试;最后才能进入正样阶段,制造真正要上天的产品。
这也是一套卫星平台的搭建过程,经过2018年3颗卫星的研制,微纳星空的10公斤级卫星平台已经逐渐成熟。一旦平台成熟,新用户的订单就可以直接进入正样阶段,大大缩短了研发时间。
“即便是成熟平台,在正式上天之前,卫星平台的产品也要至少满足出厂前累计加电400到500小时的要求。”高恩宇补充道。

天仪研究院CEO杨峰。
天仪研究院同样在搭建自己的卫星平台,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杨峰崇尚“小步快跑,快速迭代”的商业法则,这也是腾讯做产品的理念。
与高恩宇是技术出身不同,杨峰出国读完硕士之后进入国内一家能源央企工作,2007年辞职创业,进入物联网行业,但由于业态过于超前公司倒闭。经同学介绍,他干起了给航天五院总体部的软件开发外协的工作,身上带有典型的创业者气质。他的搭档任维佳曾是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结构热控室主任、载人航天应用系统结构主任设计师,曾先后参与了从神舟三号到神舟八号6艘飞船,天宫一号、天宫二号两个空间实验室以及空间站等任务,现在主要负责天仪研究院的卫星研发。
天仪研究院最开始嗅到的商业机会来自科学实验微小卫星。“航天人做大事做惯了,看不上小东西。对于很多想要做太空实验的科学家来说,想在太空验证其理论研究成果需要排队很久,微小卫星的平台可以为他们提供短周期、低成本、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杨峰说,“天仪想要存活下来,就得避开”国家队“(指国有航天企业)找到适合的生存空间。绝对不和‘国家队’产生任何竞争,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政治保护。”

天仪研究院自主研制的卫星“青藤之星”在实验室进行测试。
2016年11月,天仪研究院在酒泉发射自己的第一颗卫星“潇湘一号”时,距离公司成立只有7个月。第一颗星的研发周期不到一年,这创造了业内纪录。
与高恩宇的谨慎不同,杨峰认为出岔子是正常的,SpaceX是目前最成功的火箭公司,也是发射失败最多的火箭公司。
2018年1月,天仪研究院曾发射了两颗小卫星,其中一颗在太空中死机变成了废铁。作为补偿,天仪研究院为客户重新设计了该卫星,并负责后续发射事宜,这是天仪一贯的售后服务。
“实际上第二颗卫星是被我们玩坏的。”杨峰解释道:“在与原载荷客户充分沟通之后,我们决定充分暴露它的问题,让它的各种能力达到极限,然后我们迅速更新软件版本,完善卫星平台,之后所有批次的星虽然也会存在bug,但至少不用担心生死的问题了。”
2018年,从发射数量上看,中国发射卫星最多的单位是航天科技集团,总共发射了200多颗卫星,排名第二的是中国科学院,数量为大几十颗,第三名由天仪研究院和长光卫星并列,发射12颗。通过快速尝试,现在天仪研究院的卫星平台已经进化到可以实现3到4个月制造一批卫星的速度了。除了缩短研发周期,如何降低卫星成本一直是关键,这也是所有卫星公司正在着力解决的问题。
高恩宇在体制里工作时有大量的时间用在了跑流程上。写报告、等领导审批、立项拿钱、组织设计、组织采购、研制、总装集成测试、找火箭、最后运输至发射场与火箭对接完成发射。卫星研发周期往往要3到5年之久。但创业之后微纳星空简化了卫星的研制流程,几个子环节同一时间内并行突破,有效缩短了研发时间,降低了管理成本。
“降低成本有两部分——管理效率高、产品的自主化率高。最核心的还是要把重要单机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核心的星上计算机现在都是用的自己的产品,包括软件和硬件。”高恩宇说。
在徐鸣的观察中,造卫星和造手机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将各种部件组在一起。他是猎豹移动联合创始人,再次创业成立的聚焦低轨宽带5G通信卫星的银河航天,现在是国内估值最高的民营卫星初创公司。不过做手机可以在全球工业体系中找到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也可以去找高通、三星、LG、夏普,任意选择配件的供应方,相比之下,航天的供应链成熟度就要差很多了。
天仪研究院部分使用工业级材料取代军工材料,比如星箭分离器的现成器件要60万元——实际上就是一个铁盒子、一个弹簧,外加一个开关。经过几百次实验之后,天仪把星箭分离器造了出来,大大降低了成本。“依靠现有的工业进步,很多材料经过加工、改造,完全可以满足需求,原有的供应链体系拓宽了。”杨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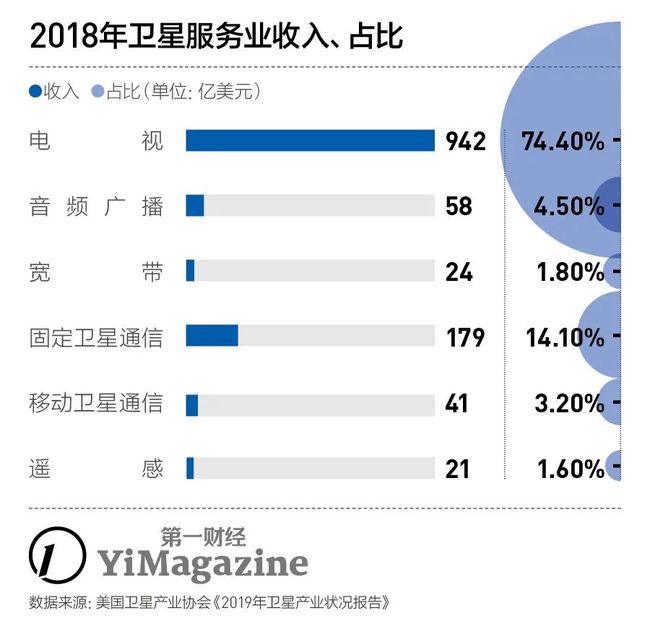
卫星成本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发射成本。如今微小卫星的国际发射价格基本上在每公斤3万至5万美元。即便是在发射服务性价比极高的中国,发射成本也在1.5万至2万美元之间。在卫星的成本中,发射成本甚至能占到1/3至3/4。

如果能将发射价格降下来,发射频率提上去,简化发射流程,仅微小卫星的发射市场就可能是达到千亿级规模。这也是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商业火箭公司看中的机会。蓝箭航天将在2020年年底首飞的朱雀2号就至少可以将发射成本降低一半。
蓝箭航天的总裁张龙在39岁时决定加入蓝箭航天成为一位创业者,此前他的工作单位是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下属的中国长城工业集团,主要工作内容是将中国制造的火箭卖给白俄罗斯、巴基斯坦等航空力量不足的国家。他是除合伙人之外蓝箭航天的第一名员工,当时公司在北京西奥中心的办公室只有100平方米,桌椅都是他亲手组装的。现在蓝箭航天已经是全球第三家(另外两家是SpaceX和Blue Origin)拥有液氧甲烷火箭发动机技术的火箭制造商。
在火箭的研发过程中,最难的是发动机,行业内的普遍说法是“没有十个亿、三五年,根本听不到响”。但多年以来,发动机和飞行控制等重要系统在中国只有体制内的个别院所能够生产,购买价格昂贵,并且这些院所重点保障国家项目,因此交货周期无法保证,想要降低火箭成本并控制研发周期只能自己生产。
发动机的最大难点不是技术,而是用作燃料的火炸药只能通过采购获得,供应链又非常封闭,想要搞到这种原料的难度不亚于当年马斯克去俄罗斯买导弹,现在更是几乎不再对外销售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蓝箭航天最终选择了做液体火箭。“2017年,团队又因为做液煤火箭还是液氧甲烷、做多少量级的发动机争论了一番。”张龙说。中国在液煤火箭发动机的研发上已经有所积累,但是仅有少数企业生产航天用煤油,甲烷则随处可见,且价格是煤油的1/3,出于成本考虑,蓝箭航天最终选择做液氧甲烷火箭。“在吨位选择上,未来最有商业价值的卫星在500公斤到1吨之间,而且都是组网发射。按着这个趋势,我们认为火箭的运载能力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1.5到2吨是最合适的。另外国际上这种类型的火箭竞争偏弱,只有印度和意大利的两个型号和国内的两款火箭。”张龙解释。
在商业市场上技术永远只是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创业者来说,政策法规和准入才是最大的门槛。NASA的航天专家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技术积累,已经逐渐退出了低轨道这个环境的探索,国家转向深空探索、月球背面等看不到直接产出的领域投资,低轨道完全放开,政府不再做相应的项目和计划,并且通过政府来引导企业开发这个方向,NASA用大量的资金来支持SpaceX和OneWeb。在中国,虽然军民合一已经上升为国策,但是具体的操作办法只有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才能逐步变得更清晰明朗。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中国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卫星发射中心,在这片毫无生气的戈壁滩上已经完成了第101次发射任务,其中有一次是属于蓝箭航天的,但拿下这张民营火箭发射许可证并不容易。
2015年蓝箭航天刚成立时,张龙和CEO张昌武去见投资人,被问到最多的3个问题是:火箭能不能造出来?国家让不让发射?发射场可不可以用?2018年3月,成立3年的蓝箭航天终于取得了保密资质可以申请发射许可,为了保证第一发火箭在10月27日如期发射,张龙在2017年年底就建立了工作组,先后拜访了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主管发射时间表的军委装备发展部、主管发射场进场许可的战略支援部队等部门,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才跑清楚流程,之后的材料又修改了无数遍。
差不多同时,杨峰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火箭哪怕有空位也不愿意给民营公司发卫星。当时的申请表还是针对国家体系的,里面的型号名称、经费来源、主管单位这些内容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填。”
另一方面,对于卫星应用公司来说,只有形成足够大的星网才有应用价值。
佳格天地的核心技术之一就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图像解析和数据分析算法,通过土地纹理、地垄方向、光合有效辐射,自动用不同颜色标注出客户的土地位置、土地面积、土地等级,可以看到该区域目前以及过去几年的耕种情况,查阅农作物在过去几个月的长势情况以及当前成熟度,预测最佳收获周期等。“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假设你只有一两颗卫星,你做出来的东西就很难标准化。现在国内的卫星市场还没有任何一家能够达到这种标准化的程度。”张弓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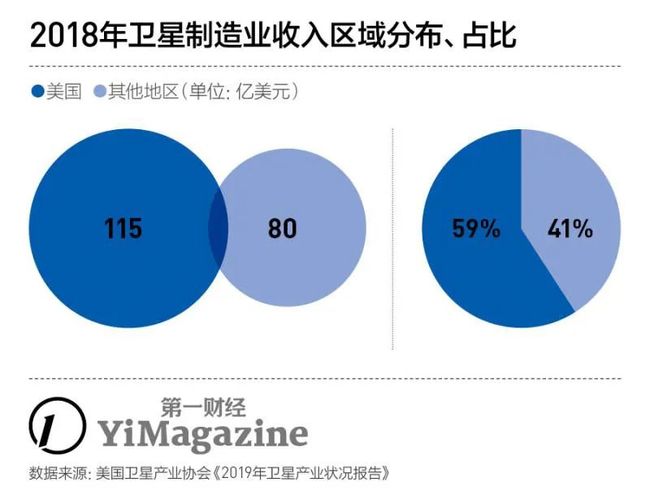
如果以天仪研究院一颗卫星100万至300万元的制造成本计算,想要实现星网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目前,获得1.5亿元B轮融资的天仪研究院、获得过亿元A+轮融资的九天微星、获得近亿元A轮融资的微纳星空已经算是行业内第一梯队的公司了,但与国外动辄几十亿美元的融资比起来还是太少。
在外人看来,天仪研究院擅长市场营销。不管是带着工程师团队录制《天天向上》等热门综艺,以平均每月至少两次的频率公开亮相并发声;用心经营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博——它在知乎拥有5000名粉丝,回答点赞数接近2万;还是设计生产精美的太空周边产品,天仪研究院都是所有卫星制造商中最会讲故事的公司,但杨峰觉得自己是为了融资迫不得已才走到台前的。
“以前我们一直看重的是具体的成绩,但是现在发现不对,这样纯苦哈哈地干活不对,要虚实结合。”杨峰说。
2018年年初,杨峰在寻求新一轮融资的过程中见了不少投资人,他们的反馈是,“你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故事不够性感。”投资人想听的不是一个科学家艰苦创业的故事,而是像肯尼迪说人类要登月的时候,那种激励一代人去实现梦想的故事。马斯克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不仅讲了一个性感的故事,最终还实现了。投资人的耐心有限。“融到C轮的时候,开始要求你商业模型要跑通,要有收入,有利润。但是我们这个行业现在远没到这样一个阶段,大家都在吹泡泡,但泡泡迟早是要破的,我们讲故事的阶段已经过去。C轮死可能是未来两年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主营业务是研制固态火箭的零壹空间CEO舒畅说。
“对整个行业来说资金都是最主要的问题,这是一个资金消耗量大、短期内很难产生内容的行业,卫星已经算是这个产业链中回收最快的环节。从投资机构的角度看,商业航天经历了无人问津到被人追捧,2018年下半年大家已经恢复理性。因为技术壁垒和资金壁垒,再要出现新的公司已经比较困难,未来的资源会越来越往头部的几家聚拢。”中科创星的董事总经理张辉说,他投资了微纳星空、九天微星等卫星产业链上的公司。
2018年春节档,电影《流浪地球》成为最终赢家,拿下45亿元的票房,虽然这样的硬科幻电影本身并不能对高度严谨的太空事业产生什么直接帮助,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民众对太空事业重要性的认识。
一个好的现象是,杨峰现在去挖人的时候不用再做自我介绍了。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翻译。
![]()
![]()
常点在看,保证及时获取推送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