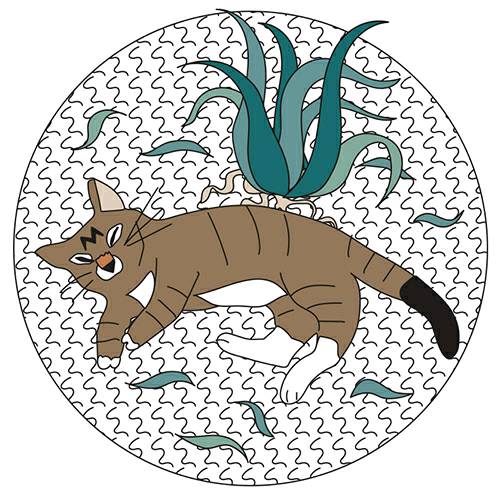文/y亦大
♥
又做了同一个噩梦。那些面露凶光的黑毛怪物险些追上我。还好我灵机一动,挤进变了形生了锈的铁栅栏。可代价是折断了右腿。
努力睁开眼睛,因为昏昏沉沉断断续续的睡眠,嗓子眼总像有股升腾着的火气,惹得人只想干咳。
把枕着的脑袋扭转个方向,自言自语,老子算是幸运还是不幸呢,无聊生活啊,这种充满生命威胁的冒险,只能出现在我的梦里。
压麻了的左腿没法随性挪动。哦对,还真是断了条右腿。
嗓子眼的无名火气总算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正前方是那把老嘎吱响的木椅子,她平日不让我坐的。
不管三七二十一,正好能让我往地上摔,以泄怒火。
♥
正想翻身把右腿从左腿上甩开,大门的锁眼吧嗒作响。我很快打消了念头,手心微微出汗。怎么还心虚地紧张起来了呢。
自己和自己打赌,这回她是径直走过来探视我,还是在厨房先磨磨蹭蹭地啃完一个苹果。
其实通常,她会在开锁后的二十秒内进屋,和我礼节性地打招呼。
有那么一次,她在冰箱里掏了个苹果,咬的咔吱作响,足足耽搁了十分钟。于是我就记住了。
直接忽视一个病号的感受,是她的不对。
♥
她不出所料屐着拖鞋径直朝我走来,和大部分时间一样,脚步很轻却很沉。
我压制着想要上扬的嘴角,可喉咙里还是逃逸出一声轻哼。
我回来了。
呵,老样子。她张望着在门后露出脑袋,眼神和我对视,于是她长舒一口气,却抠门得挤不出一个微笑,倦容好像她每晚敷的乌漆麻黑的面膜,厚厚地堆在下巴上,马上就要挂不住坠落一般。
她让我觉得,每个白天她都在被无数个黑毛怪物追赶,像蜈蚣一般每天都要折断一条腿。
哦。
我伸了伸懒腰,假装没有察觉她身上散发的微苦气息。
♥
白天出门的时候,她会在一堆五颜六色的玻璃喷瓶里挑选再三,把五颜六色的液体喷得满屋子飞窜,强迫我的嗅觉接受各种刺鼻的拷打。
等到她出门的时候,那些刺鼻的味道就一路尾随她出门,很难分辨头天晚上那种轻轻的苦涩,是消失了,还是被掩盖了。
但等傍晚归来的时候,她的身上又带进来这种和阴天一样的气息,破坏我长长的午休后懒腰里抻出来的无忧无虑。
♥
哎。但是她应该从来不知道我会担心她。怕她哪天战斗回来,一条健全的腿都不剩了。
我一直觉得,就算和她分手了,我就算做回那个浪子,我也可以全身而退,当然,除了那条断腿。
但是,她不一样了。她要是断了腿,应该会为冰箱里没有苹果而愁,为买不起五颜六色的玻璃喷瓶而愁,为买不起那些我觉得根本不重要、和五颜六色的喷瓶一样虚伪的五颜六色的衣服而郁郁而终。
♥
想这些的时候,可能我喉咙里又抑制不住地逃逸出一声轻哼。我慌乱地用干咳掩饰过去。
她从那把嘎吱作响的老旧木椅上转过身。你怎么啦。她问我。声音捏得很细,假装她自己不需要人同情。
像她这样的人,最要面子。情绪都溢到额头了,还要我配合她,假装看不见。
我无需回应她。
她早就习惯了她的自言自语和我的不理不睬。向来我们之间的交流就很少,她尤其甚少提及自己白天的工作。
要不是她在家会花很长的时间在键盘前码字,晃得梳妆台上的玻璃喷品互相倾轧,我真的会以为她是个调香师或药剂师。
♥
她一动不动坐在那把木椅上的时候,我真不喜欢看她的背影。因为不怎么好看。而且,因她的背影比她的表情和她的寡言更让人难以揣测。
她用力敲击的,那都是什么,我无聊的时候经常猜想这个来打发时间。可能是和对我说话时捏细了的声音一样,被捏细了的字和情绪吧。
不过,自从断了条腿,整天无所事事地打发白天的时间,她对我,除了礼节性的照顾,和出于一个女子本能的母性,看不到其他的情绪了。
我们很少有肢体接触。睡觉的时候,我宁可打个地铺,而不愿两人把一张单人床,活生生睡出双人床的距离。
♥
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疗伤于此,我是她的一部分,我属于她。但是她不属于我。她是我视野里唯一的一个人。她是我的全部。
我这下可算是真真实实地弄清楚那一天到头挥之不去的嗓子眼升腾的火气所为何事了。
就算我觉得我可以全身而退,除了那条断腿,继续去做我的浪子。但,我还是不想离开她。
不想离开那沉的屐着拖鞋的脚步。
不想离开那不怎么好看的背影。
不想离开那该死的不论是苦味还是浓郁刺鼻的虚伪的香味。
不想离开那坠到下巴上的毫无微笑的疲倦。
不想离开那无数遍的,冷漠的,我回来了。因为每次,她都真的回来了。
♥
算了。就算我们互看不顺眼。我能陪她的时间也就那么多。她年轻的时候,我也年轻。她依旧年轻的时候,我忽然就老了。呵呵。
如果我老了的时候,腿还是折的,那我也要想办法逃走。
至少这样我还能想像她,像往常一样,吧嗒开锁,没有从冰箱拿苹果磨磨蹭蹭地啃,而是径直走向我,告诉我,她回来了。
而不是那脸上身上沉得挂不住的阴天气息,终于化成雨,打湿她的脸。
喵。
献给某只,以及很多只,没有屋檐躲雨的流浪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