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 | 玻璃变形记
如果你关注家居设计,或者曾在欧洲的创意设计店流连忘返过,又或者是个瓶瓶罐罐爱好者——你也许对以下这组多功能玻璃器皿不会陌生。
这组容器系列,就是通过把切割过的玻璃酒瓶进行拼搭组合,实现容器的多功能运用。 我们印象中那些被遗弃在街角巷尾的邋里邋遢的玻璃酒瓶,因为这样的“变形”,连着它们自身固有的黄、绿和棕色,都摇身一变得如此优雅。
作品的名字也玩了一种文字变形游戏,将“变形”的英文“Transform”和“玻璃glass”结合,造了一个新词:“Transglass”即“变形玻璃”。还附带暗示了玻璃材料的一个特性——透明(Transparent)。

绿色的人体(Green Figure),玻璃瓶与镜子,65x30x35cm,2008年
它的作者是英国玻璃艺术家爱玛·伍弗顿(Emma Woffenden),这是她和设计师丈夫的跨界之作。在爱玛的个人创作实践中,她对现成品进行直接使用或间接转换,玻璃酒瓶是她常常使用的材料。她将它们视为肢体的一部分。于是我们见到在她的许多作品里的身体形态基本上是靠酒瓶的变形完成。

粉碎的荡秋千的人体(Shattered Swing Figure)玻璃瓶、玻璃与金属,110x100x50cm,2009年
她也对酒瓶进行再翻制,给它们上色或直接用别的材料(例如玻璃钢或青铜)来创作截然不同的形体。酒瓶的外表被隐藏了,取而代之的是似人又非人的形体——更像是外星生物。
姐妹(Sister),玻璃瓶上色,240x102x80cm,2009年
到这里,或许不难看出,艺术家对“身体”这个主题的迷恋。“变形”是她作为一个雕塑者创作的主要方法,而玻璃是她的语言。
来看看英国艺评人、撰稿人Martina Margetts对她学生时代的一段描述:“回到伍弗顿还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学习的1991年,她开始用三维(雕塑)的方式工作,用(玻璃的)自由吹制和模吹工艺 ,开始关于身体的探索。她撷取身体的局部同时作为形体和象征。”
爱玛常常在一件作品里巧妙糅合玻璃成型的不同技法。譬如将吹制玻璃得到的圆的、管状的形体进行切割与组合,创造出模棱两可和似是而非的形体。这些形体虽不能一言以蔽之,它们并不是无形。她说:“我感兴趣的点在于未成形(unform)而非不成形(deform)。我着迷于事物诞生之前的状态,总是那些开始的、初生的东西,事物的早期本质。”
变形 Transformer,玻璃钢、茉莉酮酸酯, 91x64x20cm, 2012年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爱玛早年的作品中,她先是尝试将两种形体捆绑在一起进行变形。譬如《警棍》(Baton),可以很显然看到她运用自由吹制的形体两两结合或一个自由吹制与另一个模吹的形体相结合,创造出了几种有意思的形态,之后几乎都成了她的标志。“玻璃”看上去是一个坚硬的材料,但在表达柔软方面却有先天优势,这是因为它在高温下是液态的,而且在吹制过程中,它总是从一个小椭圆形“泡泡”开始,再经过手的塑形成为一个长的或扁的椭圆形等。高温下的玻璃,就像个发烫的透明橡皮泥,只不过需要更大、更多的力气和技巧去改变它的形态。由于本来就是靠着艺术家身体的力量去影响材料的形态,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与身体互动的结果。爱玛的早期作品中更多地是对玻璃作为身体形态的探索。
再如《角/喇叭》(Horn)——”Horn”这个词既有角也有喇叭的意思——《小拱》(Small Arc)等等。 她给作品取的名基本上都很形象,而就像本文开头引入的她的设计作品的名字一样,这些英文名字也有多重含义,观众解读到什么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似乎她更多的是在旁观着她创造出的形体,任由它们从她眼皮底下劳作的手里蹦出来,完成了它们自己,然后她好像只是取了原本就属于它们的名字。
角/喇叭 Horn,玻璃, 65x25x30cm
她也运用玻璃的透明性,但并非把它打磨地透亮,而是在把玩玻璃透与不透两者的界限,如1999年的作品《呼吸》(Breathe):一件半透明的土丘形状玻璃上洞开一个小圆洞,透过半透明的躯干往里窥,隐约可见里面另有一根管状玻璃,像是一根通道,也像是一个器官(如果形容外部是“身躯”的话),而作品的名称恰如其分地赋予了这件作品一种拟人感。

呼吸(Breath),玻璃,15x20x10cm,1999年
这件作品其实是《切断的装置》(Severed Installation)中的一件。整个装置包含了:两件玻璃,分别被放在两张带轮子的桌子上,周围拉着半透明的帘幕,一只灯管悬挂在其中一件玻璃上。仿佛它们在手术台上躺着,一个还需检查,一个在默默呼吸。
切断的装置 Severed Installation,玻璃、防水油布、桌子、灯,1999年
随着爱玛开始将玻璃的形体用绳索捆绑在桌子、椅子等家具上,这些玻璃物件儿似乎更鲜活了起来,开始参与到艺术家有意识地组织中去。
她说:“有时候觉得自己记得正在出生时候的事…那是非常糟糕的感觉。脚先被拉出来,脖子感觉被勒住了…真的有我的脖子被什么可怕的东西困住了的感觉”。在她的一些作品里,我也能感觉到那种对胚胎、生育之初的遐想,譬如这件《蛹塔》。

蛹塔(Pupae Tower),玻璃与金属架,295x100x45cm,2001年
渐渐地,这些作品开始流露出更多重的含义。我认为她从身体形态进入到身体与心理的联系的探索中。

我从未真正了解她(I never really knew her),玻璃瓶,颜料,镜子,玻璃与木头,122x95x64cm,2009年

凝视( The Gaze),玻璃瓶、木、玻璃、颜料,42x60x41cm,2006年
在爱玛近年的作品中,出现了越来越多诡异的形体,但仍然延续了她那标志性的“酒瓶”状形体,以及与绳子、现成家具等惯用材料相结合。这些身体通常以一种杂交的方式呈现,而所携带的隐喻更加丰富。譬如这件《我叫她,妈妈》(I Call Her, Mother)里:好像一个人坐着被紧紧绑在椅子上,全身白色,除了它的头是透明玻璃,一只脚也是透明玻璃,另一只脚已被椅子扎进“肉”里。仔细一看两只脚分明就是两条椅腿,自己被绑着支撑起自己的身体。玻璃增添了一种不安稳感,也暗示了透明皮肤下血肉可见的真实。从正面看, 两腿之间的物体似乎暗示着女性生殖器,而从侧面看,又俨然成了男性生殖器官勃起的状态(雌雄同体),又与似乎“张着大口”的“头部”在形态上互补,形成极具冲击性的张力。整件作品让我想到女性生育时那难以名状的痛苦。

我叫她,妈妈( I Call Her, Mother)聚酯纤维、塑料管、绳子、颜料、玻璃,150x45x55cm,2010年
我猜测她用酒瓶这种一般意义上被认为是廉价材料做作品,一方面是因为随手可得,一方面也是一种聪明的回避。因为玻璃材料昂贵,而又很容易做出精美华丽的装饰效果,玻璃这种过于取悦的一面不是她所追崇的。她曾说:“我不喜欢什么东西过于美丽,因为那不能解释所有的事情,一切都是平衡的。”但这并不代表她的作品是粗糙的,她所展现出作品那看似简单和不费力的表达其实需要对细节处理地尽善尽美,才能使它们有润物细无声的气质。
爱玛的作品虽然用玻璃来隐喻,但从主题到表现手法依然是很西方。下面这位艺术家虽然也是欧洲人,但我总觉得她的美学中含有很大程度上东方的“隐”的哲学。她也将玻璃变形为无数细小碎片再重组成诗意的空间。
比利时艺术家西尔维·范登胡克Sylvie Vandenhoucke,从她的作品里感受到的是微小、简素、宁静和神秘,仿佛一位充满哲思的诗人。中国的诗人善于把不可触摸的情绪表达为可感知的意境。一句“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将飘渺的梦比作飞花、幽幽的愁比作丝雨,瞬间让人心领神会。西尔维的艺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西尔维擅长用碎玻璃。早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院学习首饰与金属,光影之间的互作与平衡常成为牵动她创作的主题。微小之物总能引起她的注意,她说:“从小时候开始,我就爱极了一个整体之上那些极小的细节,就像一棵树上的那些叶子。”她的创作,微小到细枝末节,广大到整个空间,与周围的环境最大限度地融为一体。
她曾经在法国Sars-Poteries玻璃博物馆驻地创作,最后在博物馆的一个空房间里呈现了五件作品。乍一看过去,你会想问,作品在哪里?习惯于看见奇异形状或绚烂色彩的眼睛搜寻不到刺激点。只见通间洁白的房间,天花板上点缀着法式古典装饰浮雕,四扇french window外绿意盎然。唯一显眼的恐怕就是房间墙壁上挂着的两面大镜子。然而,再看过去,就会发现一部分空间被几条黑线给框了起来,墙上还挂着两幅白色的“画”,镜子里倒映出一个细细的白色圆圈。

轮廓(Outline), 碎玻璃、木架,75x75x150cm
那几条黑线仿佛在空间中凭空勾勒出了两个正方体,名为《轮廓》(Outline)。它们一样尺寸大小,一个叠在另一个身上。都是用碎玻璃做的,增加了“摇摇欲坠”的感觉,并且弱化了线条,使它真的就像几条笔迹。看得久了,它勾勒的空间渐渐浮出视网膜,你会开始质疑,它们只是几条黑线还是的确是两个白色正方体叠在了一起?因为它对应的房间的另一头镜子前,摆着一个大小似乎一模一样的白色长方体。

会话(Conversation Piece,玻璃、泡沫、木,150x75x75cm
这件作品的名字叫《会话》(Conversation Piece),通体白色,西尔维用了15000到20000片碎玻璃做成。它像那件《轮廓》的“实心版”。“会话”这个名字来自十七世纪的一种画有上流社会人们集会的肖像画,后引申为会引发讨论的有趣物件。回到西尔维的这件作品,显然随着越靠近它,人们越会发觉它的细节之多,它处变不惊地待在原地,像是在等待观众参与到会话里来。
旁边的墙上,作品《路线》(Itinerary)是碎玻璃钉子在墙上缠绕的一个圆。同样的间距,使思维游荡在相同的韵律上,时间在这里周而复始。光影轮番在这些细碎间漏过,让人蓦然想起墙边一隅和着窗外树叶一起摇曳的光。
白墙上还挂着两幅似乎什么都没有、白茫茫的作品,走近了看又不禁审视其细节的充沛,无数个发光的白色小圆片整齐有序排列,每一个小圆片上又有一个小洞,像鳞片又像某种生物的卵,像溅起的水花全被摞在一起。还有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独角兽》(Unicorn)——让人联想起里尔克关于独角兽的诗“悄悄走来/如掠夺的/失助牡鹿闪目求助/象牙架般的四条腿/在轻灵的平衡中移动/身上祥瑞地泛起一道白光/平静鲜亮的兽额上/独角笔立灿如塔映月华/行步时岿然不晃……白色(比什么都白)流光溢彩”。这件作品如这乌有兽一般,纯净、坚韧和神秘。也让我想起画家阿涅思马丁(Agnes Martin)那静谧而饱含感情的画布。另一幅叫《葱茏》(Verdures),也是这个展览的名字。Verdures这个词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翻译为好,它也有覆盖的意思,暗示了这些作品创作的方式,又十分诗意地概括了这整个展览,这幅作品就是其直观的一个缩影。同样的,它由上千片白色的碎玻璃组成,像是一大片悉悉索索的玻璃叶子,絮而不乱,随光而影绰。它们吸引了你我就如同那树和叶子对艺术家的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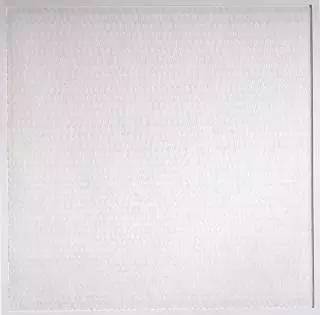
独角兽 (Unicorn),碎玻璃,92.7x92.7x6.2cm,2009年

葱茏(Verdures),碎玻璃,47.8x47.8x4.6cm,2010年
创作这些作品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但很精巧。西尔维用的是覆盖的方式,她先将碎玻璃烧成拇指大小的小片,并在头尾留有两个小洞,这样就可以被挂起来或是勾在某物身上借力,我想这种方法也许是早年首饰设计的学习给她的灵感。然后她再将这些烧成的碎玻璃小片一层层地覆盖在模型的表面。
她的工作方式就像编织,玻璃就是她手中的线,她在一片一片地重复着劳作,将时间封存在作品里凝成专注的气韵,将对光影的追逐留在玻璃片间遐想。她的作品如此轻巧,却一定需要精心的布置与绝对的专注。正应了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关于“轻”的那句阐述:“对我来说,轻是与精确和坚定为伍,而不是与含糊和随意为伍。”几乎可以想象那背后她一丝不苟地将玻璃小片钉起来时手指翻飞的样子。
其实玻璃本没有形,它只是一种材料而已。所谓“玻璃变形记”所讲述的都是艺术家自己的故事。爱玛讲了一个关于身体的故事,这里面有她想象中的生命之初的样子,讲一个关系的简单与复杂;西尔维讲了一个关于宏大的微小、整体的部分的故事,让你像穿越在棱镜内外,既可以尊重外空间的既定存在,也可以得到一种仿佛内观的视角,感受到那细小如尘埃的力量。这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和玻璃没什么关系,但却是玻璃让她们找到了讲故事的语法。
(谢文蒂,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陶瓷与玻璃系硕士,现工作于深圳美术馆。)
⊙ 本文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三联生活周刊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长按二维码 即刻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