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世界·公益阅读】惊奇档案:黑洞 ——当代文化中“熟悉的陌生人”

以“读”攻毒——科幻世界相伴,助力全民战“疫”
黑洞
——当代文化中“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索何夫
本文刊登于《科幻世界》2019年6月刊。
作为少数产生了全球范围广泛影响的自然科学新闻之一,今年4月初,远在5300万光年外的M87星系因为“第一张黑洞照片公布”,成功地成了热点议题。按照常识,人们对于与自己距离越遥远、相关性越低的新闻的关注度也会越低,为何这次却会如此例外呢?
答案并不难找——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当代文化产业已经成功地将“黑洞”概念植入了普通人的宇宙观之中。在现代,几乎没有哪个天文概念如同“黑洞”一样,在当代文化中被反复提及,却又如此广泛地遭到各种误解。

图片来源:欧洲南方天文台
拜20世纪80年代之后射电天文学的发展及信息化革命所赐,我们这个年代很少看到一个接受过基础教育、具有必要的阅读能力和阅读渠道的人,会对“黑洞”这个词一无所知;但另一方面,又极少有人能把“黑洞是什么”说出个所以然来。这是因为:黑洞是所有天体中最“简单”的一种,一个黑洞最多只能具有三个有意义的物理量:质量、角动量和电荷量;同时,这种最“简单”的天体,却在当代文化中拥有比其他任何天体都更加复杂的“解释”和衍生传说。
“黑洞”作为天体的诞生

射电天文学兴起后,人类不再被迫通过狭窄的可见光窗口对宇宙管中窥豹,大量天体由此得以确认,“黑洞”正是其中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概念之一。
公元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三年,爱因斯坦首次公开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以重新诠释引力场的本质和引力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之后数十年中科学/科普工作者有意无意塑造的“启示降下,举世皆惊”不同,在那数以万计的士兵正忙着把血肉填进东西两线弹痕累累的战壕、掩蔽部与碉堡的年头,着实没有太多人还有余力去思索宇宙中的基本力以及它们的基本运行原理这种“没什么用”的东西。之后,史瓦西通过广义相对论第一次对“史瓦西半径”这个概念做出的描述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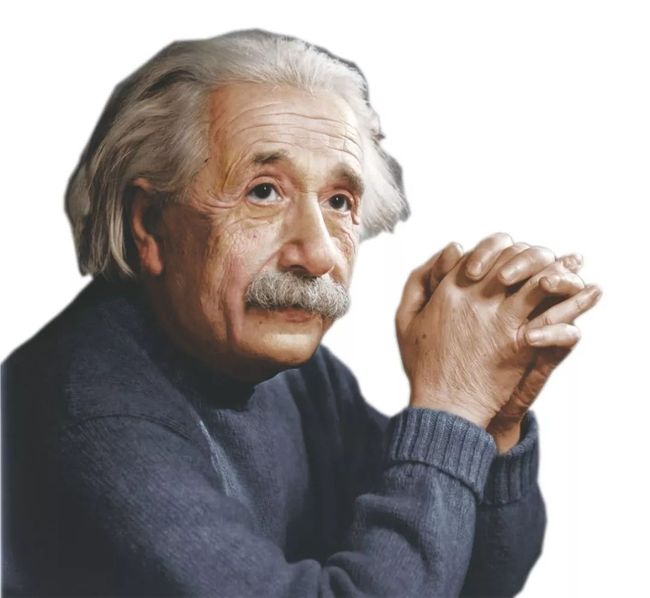
一战后的短暂和平里,人们忙着革命、清算、憎恨、狂热,接着又迎来下一次世界大战,只有少数理论物理学的专家,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讨论和研究着广义相对论方程。在那个时代,刚刚成型的早期科普的侧重点,是如何辨别酸碱、常见物质的固液气三态转化这类“对人们直接有用”的常识,正在“青春期”的科幻文学则处在早期太空歌剧“一言堂”、遍地“大角星牛仔宇宙历险记”的五毛钱小本子时代,要指望大众传媒普及黑洞及相关概念,不啻天方夜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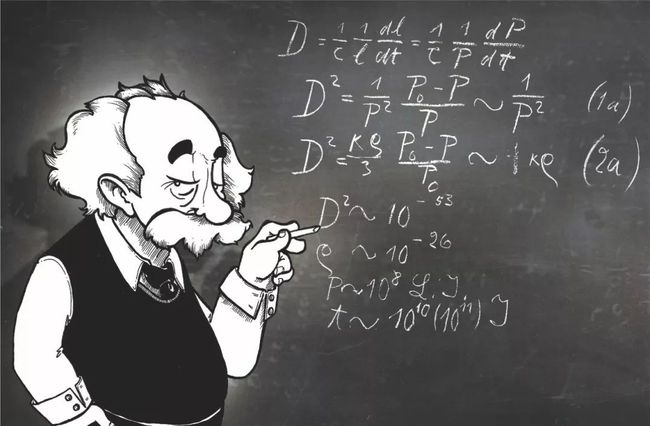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大战中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日后射电天文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作为冷战副产品的“太空竞赛”则让天文学脱胎换骨,从“一小撮老巫师的占星术”,变成大众认知度颇高的显学,顺带也大大提携了原本不为人知的理论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
1960年前后,对广义相对论的研究让“黑洞”得到了更加清晰的描述,之后脉冲星的发现也大大刺激了人们对搜寻“实际存在的黑洞”的兴趣。但此时这个概念仍长期停留在天文台和大学课堂的小范围讨论中,直到20世纪70、80年代,一系列被认为是“疑似黑洞”的强X/γ射线源被逐渐发现并报道,“黑洞”这个词才流入为大众所熟知的文化领域,并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创作与文化消费的对象。
“黑洞”在科普中传播

撇开占星术这类形而上学不谈,特定的天文现象/概念在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化)领域受到强烈追捧,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6世纪至19世纪,彗星与火流星就一直牢固地在各种文化产品中占据着一大片“自留地”。19世纪发现谷神星后,小行星热也曾经轰动一时,顺带让不少职业/业余天文观测者靠出售“命名权”大赚一笔。
与这些“前辈”相比,成为20世纪末文化“新宠”的黑洞,有着众多特殊之处。
首先,无论彗星热还是小行星热,抑或星座文化,都与大量业余爱好者分不开,但观测黑洞这种压根儿不发出可见光的天体,远远超出了业余爱好者的能力范畴。

其次,此前的彗星热和小行星热大多与神秘主义有关(星座文化在这一点上尤为典型),但相对来说,当代文化对黑洞的追捧往往与广义相对论及其通俗化假说密切相关。
这是因为,黑洞的种种极端物理特性,经常成为各类入门级天文科普读物中特别突出的重点,毕竟,要建立“宇宙是宏大而奇特的”这一基本印象,有什么比黑洞更合适呢?
讽刺的是,“黑洞”在被科普界广泛关注的同时,伪科学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早在黑洞概念刚刚被描述出来时,就有所谓继承伟大东方传统的“占星学家”信誓旦旦地声称,“罗睺”与“计都”(古代中国天文学虚拟的两颗无法观测到的星球)就是黑洞。后来,又有冯·丹尼肯和撒迦利亚·西琴等“大师”(这两位都是“众神战车”理论的“专家”)的拥趸擅自将他们所谓的“第十二颗天体”指为黑洞——仅仅就物理学常识而言,这也不可能。此外,声称“百慕大三角深处存在着微型黑洞”“传说中的复仇女神星是黑洞”等无稽传闻,也时时能带着一大串感叹号出现在某些网络社区的边角旮旯或路边摊小报上……
“黑洞”作为文化形象的兴起

在诸多与黑洞相关的文化产品中,人们最常想起的特征往往是“时空扭曲”。这颇有点儿直击广义相对论本质的味道。由于该概念的巨大发挥潜力,几乎所有涉及黑洞的“硬核”科幻作品,都一定会在这方面发挥一把。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克尔黑洞”与“白洞”假说在文化领域的共同传播,“黑洞=超空间通道”的简单等式成为当时正借着《星球大战》东风趁势而起的太空歌剧中的绝佳“万金油”,被普遍用于解释如何维持一个跨星系的巨型国家,或者进行距离以光年计的军事力量投送。当然,这些试图描述投送过程的作者们,通常仅仅是听说过“相对论”这个词而已,所谓“技术描写”经常透着传统奇幻文学中“缩地术”“仙境之门”的味道。
影视作品的编剧们自然也不会落后。在拍摄于20世纪末的科幻恐怖片《黑洞表面》中,那艘前往太阳系外的特殊探索飞船的超光速移动原理,就是通过特殊引擎“生成黑洞”(更准确地说,是生成与黑洞类似的时空扭曲状态)、“进入另一个世界、再从这个世界抄近路航行、最终返回原有宇宙”来实现传统推动手段所无法实现的星际航行。前两年一度 “刷屏”的烧脑大作《星际穿越》也走了同样的路子,只不过在该片中,急于离开地球为全人类寻找新的理想乡的主角,不但靠着黑洞的帮助进行了星际旅行,甚至成功跨越了维度,在高维度上与过去的处于低维时空的自己产生了接触与互动。由于设定背景过于艰深,这些戏份往往被观众忽略,或被视为某种奇幻桥段,但事实上,这类桥段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不得不奇幻”——对于一部商业电影来说,要向广大观众讲解广义相对论着实是困难且无意义的,这也是“科学与艺术的妥协”的必然结果。
当然,除了空间(尺缩效应),重力场对时间的扭曲作用(钟慢效应),更能天然地刺激创作者的灵感。在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科幻小说中(比如乔治·马丁早年的“联邦帝国”系列中短篇),经常出现用于减缓时间流速的“时间翘曲设备”,以替代50、60年代类似作品中更常见但“技术含量不足”的人工冬眠装置。这类设备经常被描述为部分借助了“人造黑洞式的重力场”,与《黑洞表面》中的特殊引擎技术异曲同工。至于最为人熟知的“钟慢效应”,自然是《星际穿越》中“地上几分钟、天上二十年”的一幕:在巨型黑洞“卡冈图雅”的重力场影响下,那颗表面覆满浅海、不断被超级巨浪定时扫荡的行星,成为特大号的“时间胶囊”。虽然在卸掉科学术语和技术外壳后,这不过是在各路人类文化中深植已久的“烂柯人”式故事的太空改编版,但至少“黑洞”给了这类故事离开荒山野岭、在遥远的宇宙中以更加“科学”的方式上演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演绎得最为另类又足够“硬核”的,当属赛博朋克的开山祖师、“太空壮剧”代表作家弗诺·文奇的《天渊》系列——这一系列将光速/思维速度/智能与重力场强度联系起来,在星体较少、思维速度与运算速度最快的银河边缘是所谓“超限界”,再往里则是能够实现超光速的“飞跃界”和不能达成这一点的“爬行界”。在群星璀璨、被庞大的银心大黑洞引力场牢牢束缚着的银河最深处,则是光速“凝滞”、思维和智能趋于无法维持的“零意识深渊”。
黑洞“大质量、强引力”的特点,也为这类大尺度的“太空壮剧”提供了不少素材。但凡是无比强大的“上古超文明”,基本上不拿黑洞玩玩都没脸见人。在《星球大战》正史(早期版本)设定中,被银河帝国当成秘密武器研究区域的“无底洞”星团,便是史前超级文明将一系列大质量史瓦西黑洞强行“搬运”到一起形成的。在有着“鸿钧老祖”级别文明出场的太空歌剧中,黑洞几乎都会被强行拽出来为那些“老妖怪”刷一波存在感。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末,随着霍金提出“黑洞蒸发”理论时对“微型黑洞”的描述被众多媒体单独截出、广泛传播,以及当年风行一时的“巨型对撞机会制造出足以毁灭地球的微型黑洞”等耸人听闻的传言,不少科幻小说和科幻游戏中也不断冒出“黑洞武器”概念。由于大多数写手缺乏必要的理论知识的,仅仅将它描述成了某种“非常厉害的大炸弹”,让“太空中的18世纪海战”又增添了一种劲爆的弹药,但不得不说,这些描写也让更多对理论物理和天文学毫无兴趣的年轻人熟悉了“黑洞”这个词汇。
有趣的是,或许是因为“黑洞”这个词汇本身就有让人“望文生义”的误导性,在众多不那么追求真实性与科学性的边缘科幻/科幻冒险类文化产品中,黑洞往往扮演着“陷阱”与“障碍物”的角色。在2005年的电影《勇敢者的游戏2》中,作为那场极端“真实”甚至近乎致命的飞行棋游戏最后终点的Zathuna星球,并不是什么桃花源或者黄金乡,而是一颗位于星系中央的大质量黑洞——它既是飞行棋游戏的终点,也是主角重新确认自我与兄弟间关系的“旅行”的终点,同时还是他们返回自己世界的通道和新生活的起点,倒是一次性契合了当代文化为“黑洞”打上的好几个常见标签。
当然,“黑洞”在当代文化中演绎的故事远不限于此。在上世纪末兴起的“多元宇宙”题材作品中,我们所处的宇宙被设想为一个质量和体积都极端巨大、引潮力则相当有限的黑洞,“宇宙的边缘”则是这个黑洞的事件视界,一旦突破视界,就能进入另一个宇宙之中。科幻作家王晋康甚至在短篇小说《决战美杜莎》中,“剑走偏锋”地描述了另一种黑洞的“用途”:为了将自己和人类文明曾经存在的证据保留到尽可能遥远的未来,小说主角将自己的意识“铭刻”在了一颗行将塌缩为黑洞的大质量中子星上,让黑洞的视界成为抵御无情时光的最强壁垒与“封印”!
不过,比起这一小部分相对较“硬”的作品,大多数大众文化产品仍然倾向于以人们的“常识”为基本导向,让“黑洞”在浩大的商业化文化体系中不断改良、变异。
从某种意义上讲,“黑洞”在当代文化中的高“出镜率”,和大多数人对它事实上的一无所知,并不矛盾:这正是当代文化在市场导向下“投受众所好”,根据受众印象而非客观真理描述事物的必然结果。在正视这一事实的同时,需要思索的是:如何在这种状态下,通过当代文化体系进行有效科普,不再让科学概念成为“熟悉的陌生人”,甚至被伪科学和反科学者所利用。这将是未来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责任编辑:刘维佳】


【为满足广大幻迷战“疫”期间的阅读需求,科幻世界微信公众号(scifiworld)上线“公益阅读”板块,至2月底,推送大量免费的优质科幻小说资源,让科幻陪伴我们共度时间也共渡时艰,做精神上无忧无虑的“快乐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