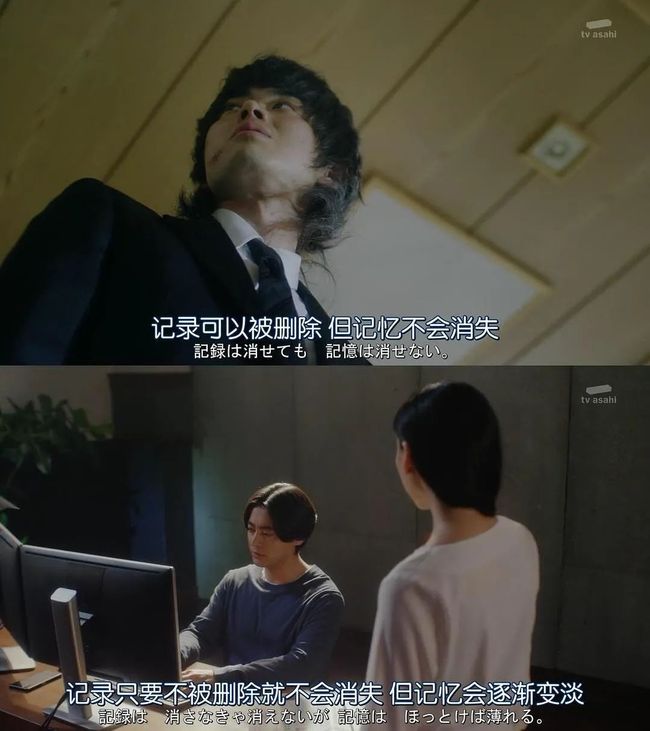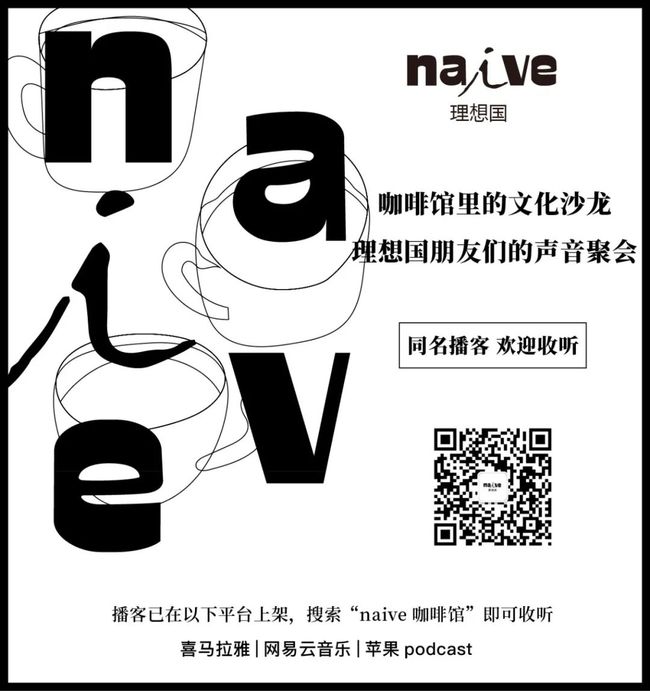他们说,“你连活着都不怕,为什么怕死呢?”
EG,理想国编辑
扫描二维码,即可进入Naive咖啡馆

*播客将在“Naive咖啡馆”公众号更新,为了方便大家收听,长节目同时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音频平台上线,在以上平台搜索“ Naive咖啡馆 ”也可以收听。
本期话题
2. 人对自身幸福程度的评估受什么影响?
3. 老舍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人生选择;
4. 自杀不一定是非理性的,但仍然是糟糕的;
5. 关于永生:永生人仍然是人,不是神;
6. 关于现实讨论:公共社会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稳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稳态,而且都有权利去维护这些不伤到别人的稳态。
嘿,Siri,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荣青:一个人从出生到跟随社会的主流价值,然后意识到要去反思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到死亡,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想过这个问题:人生的意义在于什么?其实我那天还问了一下 Siri,Siri说我现在没办法回答,就好像我很难剧透一个直播节目一样。
EG:其实什么样的人生都挺有意义的。如果以贝纳塔在《生存还是毁灭》里的提法,我们先来说一点好消息,就是我们的人生还是有一定意义。比如说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我今天要喝一个快乐水,最后喝到了,完成了这个目标,我就像养成游戏打了一个卡一样,实现了一点积分。
但是它还可以再大一点,比如说你会让你的父母因你的存在而更开心一点,或者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当然还有别的什么亲朋、同事、恋人、子女,你满足了他们,然后大家其乐融融,这也是一种意义。甚至你为更大的群体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你的社区,你的时代,你的物种甚至所有的生物——我很难设想什么叫为所有生物做了贡献,但是权且这么说——就有不同层面的意义。
然后我们会发现,第一,这个意义好像多数不是为自己,即便是为自己的时候也要取决于评价,而评价不是凭空出来的,可能是你从小被调教出来的一个价值系统。你接受了一个惯常的观念,然后按照观念去为自己设定目标,也许不一定适合你,但你说我终于是为自己做了一件事情,它本质上是为别人给你施加的任务做了一件事,完成一个系统给我的任务,这个月不完成,下个月可能就换任务了。
如果我们尺度放得足够大,到了生态圈,甚至到地球、太阳系、宇宙,有啥意义吗?好像宇宙也不缺我们发个火箭上去,反正都是太空的垃圾。张博洋说“宇宙这么大,我到底算个啥”,所以只能想想明天几点起、吃点啥这种问题。这就是我们最好乐于接受的一种生存处境。
赫恩曼尼:因为谈到人生的意义,我个人是比较赞同特里·伊格尔顿在《人生的意义》这个书里得到的结论。人生意义不是对某个问题的解答,而是关乎某种方式的生活。
特里·伊格尔顿。英国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文化评论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他更愿意相信这种人生的意义,它不是形而上的,是一种伦理性的。我们不能脱离生活来谈人生的意义。相反,人生的意义是生命值得过,也就是说人生的意义让人生具有一种品质,一种深度,一种丰富性,一种强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生的意义就是人生本身。所以刚才雪峰老师说得很对,没有哪种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用一个量化的标准和一个非常确切的标杆来衡量别人,衡量人的个体或群体。
然后下面想开一个新的维度,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相信人生是值得过的。
《斯通纳》作者约翰·威廉斯写过另一部作品《奥古斯都》,主角屋大维本来想成为一个学者,但是舅公恺撒遇刺身亡之后,他就不得不扛起重任,踏入了政治的命途,所以他就假装去联合那些意图谋杀他的人,然后跟昔日的好朋友变成了敌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卷入派系斗争的罗马重新和平。
当时他的女儿尤利娅参与了叛乱,反叛自己的父亲,甚至他女儿想要置他于死地,在公正和情感之间,他决定先把女儿放逐出去。当他要前往广场,为自己亲生的女儿定罪的时候,遇到一个旧时的好朋友,那个人问他说岁月待你仁慈吗?然后他说我为罗马带来了自由,但是我自己却无福消受,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种自由了。那个人就问他说,您的权威,您拯救罗马,您见到的罗马值得你付出一切吗?这个时候奥古斯都的回答是:我得相信是值得的,我们两个都得相信是值得的。也就是说不管人生怎么样,不管它是什么,至少我们要相信它是值得一过的。
约翰·威廉斯。美国作家、编辑、教授。
EG:唱反调的时刻终于到了啊。屋大维如果知道自己开启了后面子子孙孙杀来杀去的历史,我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人生的“值得”还是看我们要以怎样的语境去解读,每个人的人生都值得,当然也等于每个人的人生都同样值得,同样值得也等于同样不值得。
所以对我们已经活着的人来说,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把人生进行下去,你很难不进行下去。这个时候我找点理由说人生值得,或者说人生不值得,如果“值得”能够更支撑你,或者“不值得”能够更支撑你,哪个管用你都可以用。而对于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决定权其实不在他们手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决断,真的可以好好想一想。
电影《生命之树》
“你连活着都不怕,为什么怕死呢”
站在道德的高地上不冷吗?
荣青: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其他人也觉得他没有意义,那么这个人可以自杀吗?
EG:这要看“可以”是什么。如果说它是一个权利的话,当然啥时候都可以,自己的生命自己把握;但是如果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说,这个可以是不是应当或者是不是推荐,那就有不同的判断。
一般来说极少看到有社会是鼓励自杀的,像允许自主安乐死和协助安乐死的那些国家,其实已经是很宽容了,但即便是这样,我们很少看到有鼓励自杀的一个文化范畴。
这可能是因为它有社会影响,大家都希望自己生活得美满幸福,充满前途与光明的奔头的东西不要被戳破,如果时不常就有人搞自杀的话,可能就会影响我的心情,这是一个挺功利的想法。当然还有一些切实的影响,比如说亲朋好友,他真的跟你有切实的关系,很在乎你,只要你在那里他就高兴,或者说你如果过得不好,他会帮帮你,但是你消失了——一个人从网络中消失,就等于网络要重组,甚至消失掉,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的虚拟人生会改变甚至消失掉一部分,这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见到的,不管是因为保守,还是因为温情。
《人生删除事务所》
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对自己生命的自主权,比没有这样的一个自主权可能还是会追求到一个更合理的结果吧。以前我在豆瓣上看到一个网友写家人在癌症晚期,痛得不得了,想跳窗,被救下来了,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帮到她,你给她吗啡也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再一个我们有这样的道德压力。在没有辅助安乐死的法律支持的环境下,这个人的处境好像少了一个必要的合理的选择。
赫恩曼尼:我们一般谈到自杀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说法是觉得自杀的人好懦弱,会说:“你连活着都不怕,为什么怕死呢?”这种我觉得这种说法本身是有问题的,它假定了活着经历的困难比决定去死这件事难。
以前我经常在豆瓣上收到豆邮,说可能不想活了或者怎么样,我经常会劝他们说:活着就会有好事发生。但是这个劝也不一定真的会有好事发生,而且选择自杀的人也不是说认为以后就没有好事发生了。对大多数选择自杀的人来说,他们不是不相信以后生活会改善,而是说即使以后会变好,在中间经历的痛苦和忍受的折磨,是他们暂时不能承受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一个选择自杀的人就是非理性的,去谴责自杀者说你为什么这样选择。我认为我们应该给自杀者以道德上的自由。
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我称之为“青春期式的死亡想象”,比如说被老师骂了,或者被家人批评了,然后我们就想说我死给你看。实际上死就是毁灭掉所有,你其实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青春期的时候总会想象自己是看得到的死后发生的事的,并希望用这件事来惩罚别人。
有一位犹太籍的奥地利哲学家叫让·埃默里,他写过一本讨论自杀的书,叫《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他建议大家不要用“自杀”这个词,而是用“自死”,就是“自由死亡”。他觉得“自死”是人的一种特权,它的存在是一种“本己”的事情,是为了用一个让所有的驳斥都哑口无言的“不”字,来抵抗每一种失败,尤其是最后到来的那一种。
所以我们往往会说自杀的人妥协,但很有可能他恰恰是因为不妥协,所以才选择了自杀。我们没有做这样的选择,但是埃默里建议我们要尊重自杀者的选择,不否定他们对于生命的参与感,他们曾经参与过生命。而且不要高高在上地谈论他们,而是用一种平静的、自由的、平常和无拘的方式去谈论他们。
这就谈到另一个问题,其实自杀并不是对“人生无意义”的最好回应,自杀可能不是你唯一的选择,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这要看个体怎么决定。木心在《素履之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生命好在无意义,才容得下各自赋予意义。假如生命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却不合我的志趣,那才狼狈不堪。”
所以说我想对那些想要自杀的人说,一是活着就会有好事发生,让他们相信这种好事会发生;第二,我觉得人就要各自赋予意义,把自己的故事写下去,不要把它让给别人,要自己自主地掌握这种意义。
活着本身就是在对抗虚无,如果你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你就缓和一下自己对意义的这种回应,然后试着活下去。
EG:赫老师刚才不是说有的人说活着都不怕,死怕啥?好像活着是一个占据道德高点的形象。贝纳塔其实举了另外一个情况,人生都这么惨了,你看我还活着,你凭什么相信人生乐观?我是相信了人生很惨我才活着的,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点naive了。不管我们占据什么样的道德优劣,或者强势弱势的地位,不管你怎么想,其实都没有更好。
而且还有一点,有的时候自杀或者死了,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有的时候是最好的选择,但最好的选择不等于好选择,可能最好的选择也是个坏选择。对。就好像说我们总要上班,然后找了一堆工作,拿了一堆offer,我们选了一个最好的,你不还是去做社畜吗?
死这个事儿总归是很糟的,就是我们这个书,本来想叫《活着很糟,死也很糟》。在你所有的选择里,哪怕它是最好,它也是很糟糕的。
《瑞克和莫蒂》
我们只有现在,那对未来瞎操心干什么?
EG:虽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其实看不到永生的可能,但是它毕竟是个可能性,可能我们也会拿这个来鼓励自己,总有一天可以永生了。这未必是好事情。
《奇葩说》也讨论过这个题目,具体是关于冷冻,把你的生命先暂且延续下去,看看后面有没有机会让他再延续下去。正好我们这本《生存还是毁灭》里面也触及了冷冻这个例子。你会发现其实两边的论点是高度重合的,但是组织方式不太一样。
哪怕冷冻这个事情成立,然后你能够不断地这样延续生命,但这严格说不叫永生,它只叫“医学永生”或者叫“极寿”,就是寿命极长。因为你还是可以“横死”。
“横死”是哲学界比较喜欢的一个词,它区别于自然死亡。为了逃避横死,人们建立社会契约,这个是一个霍布斯式的逻辑,就是为了逃离那个人对人是狼的丛林状态,哪怕把所有的权利交给利维坦,只要让我活着,只要别让我天天面对死亡恐惧就行。霍布斯的要求是相当低的,但即便是这样低的要求,如果你让我面临死亡恐惧了,我也不再服从你。但是,如果只是靠冷冻延寿,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选择就只剩下横死了。
这种恐惧反倒让我们发现,可能永生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因为你生命越长,你横死的几率越高,但是如果我们连横死都可以免掉,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被吃空五脏还能再长出来——好像普罗米修斯也没有特别的幸福,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如果我们考虑到社会架构,比如说突然现在活着的人全部永生了,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处境?比如我知道不会死,是不是可以去搞几件死刑案去办办?但反过来说,如果只有一部分人不会死,你对这一部分人会抱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而这些人就藏在我们中间,就好像无症状携带者,我们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而如果这些人都特别厉害,他们本来就占据了社会的优势阶层,他们就很容易迅速地自我联合,然后把我们这些会死的人当做药渣,就像《大护法》,好像就更可怕了。
《大护法》
赫恩曼尼:我记得很小的时候读过季羡林先生写的回忆录,他讲因为他活得很久,所以身边的朋友都一个个离开,他相当于一个人目送了所有人的离开,那种巨大的孤独感是非常痛苦的。考虑到这一点,可能对我来讲,我也不会去选择这个选项。
另外一点,在永生的情况下,我们赋予意义的那些活动其实是维持不下去的。比如说孩子在18岁的时候离家,他知道他的父母会在家里等他,但是他们的寿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才要去多跟他们交流,不要留下遗憾。如果人能永生的话,这种时间的焦虑感其实越来越少,人和人之间也是这样。
我觉得谈永生这个话题就是说,死亡给了我们一个deadline,然后我们在中间挣扎出一些意义,我们才会被自己的才华吓到,才会知道自己这么活着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情,不然就会很痛苦。
EG:其实所有我们这些脑洞,不管是看起来有点现实的,还是看起来毫无现实根据的东西,都是基于我们现在的处境。如果我们的处境本身变了,所有这些设想就不成立了。我们站在一个台子上,不可能踢倒台子去做一些二阶的活动。
有一句名言叫做“我们只有现在”。樱木花道就说过。奥古斯丁的神学观念也说:过去也好,未来也好,不过都是现在的一个投射。这句话我们可以把它打出来,贴在我们平常中看得见的地方,我们只有现在,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只争朝夕,可以把它理解成享受当下,可以把它理解成替未来瞎操心干啥。
公共社会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
“你只是不开心,我们是想活路”
荣青:今天我们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尤其是谈到关于某些问题的时候,你很难避免有些人会来抬杠,你们怎么看这种盲目乐观的人,甚至出来反对你批评的声音?
EG:其实心智结构上我觉得跟反对自杀有类似性——他会不开心,因为他的认知协调性是维持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权且叫保守或者主流。有其他的生命刺激他去想问题,他确实是不开心。
但是公共社会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稳态,而且都有权利去维护这些不那么伤到别人的稳态,我是让你不开心,但是这好像没什么。如果我不表达出来,我跟我那些志趣相投的人没有办法凝结,我们可能更不开心。我们总要取一个权衡,在满足底线的情况下,大家都互相给条活路。你只是不开心,我们是想活路,对吧?公众讨论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各种意见都应该去表达出来,才能找到同好。
像我们在书的宣传语里呈现的,“你不是一个人”。哪怕你是个悲观者,你浑身冒着紫光,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这个很重要。在那些做心理治疗的圈子里,包括团体治疗为什么有特别的效果,就是这10个人坐成一圈聊天的时候,发现原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怪物,这个非常重要。
赫恩曼尼:对,这种心理治疗有两个原则,第一是告诉他,你不是一个人,第二,你并没有被困住,你可以做出改变。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期,信息是非常庞大的,而且过载,每天都在输入信息。在信息过剩的时期,那些能够成功处理这些信息,然后让这些信息为自己所用的人或组织,就是我们所谓的有“信息素质”的人,英文叫做information literacy。有信息素质的人界定了在信息上不同的阶层。如果那些不愿意面对负面消息,不愿意面对真相的人,选择以粉饰太平的方式把真相掩盖下去,其实我们说这些人的信息素质是偏低的,他们筛选信息并让这些信息为己所用的能力是偏低的,然后就会形成阶层。
刚才提到了权利的问题,一位研究美国建国史的史学家戈登·伍德提出,公民社会的公民应该有一种潜质——对于负面消息要保持行动的欲望。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个体,是不是有意愿为我所在的社区、地区或国家发生的不幸而付诸行动的这种欲望。如果一个群体,他并不关心除了自己以外的问题和事物,也不关心自己的存在能为他所在的共同体做些什么,并且他们对于这种灾难困境也没有反思的能力,也没有行动的意愿,那就只能依赖一个更强有力的政府,就是刚才说的利维坦来替他们选择和行动。
《瑞克和莫蒂》
赫恩曼尼:我们谈到自杀的时候总会非常的阴沉,觉得生活没有希望,然后这段话也是曾经鼓励到我的,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特雷莎在加尔各答孤儿院的墙上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叫做do it anyway,我喜欢把它翻译成为《还是要建造》。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人们经常是无理性的,没逻辑的,以自我为中心,但还是要原谅他们。如果你善良,人们也许会说你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但还是要善良。
如果你真诚、真实、诚实,别人也许会欺骗你,但是还是要诚实和真诚。你多年建设的成果可能被人一夜之间摧毁,但是还是要建设。
你今天做的好事,明天就会被人遗忘,但还是要做好事。
倾尽全力给世界你的全部,也许这远远不够,但还是要尽其所能。
你看最终就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从来不是你和他们之间的事。
我每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被鼓励到了,不管你所做的事情的结果是什么,但是你还是要去做,do it anyway。想把这个分享给我们的读者,也许会鼓励到你们现在的生活。
往期回顾
点击图片,即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