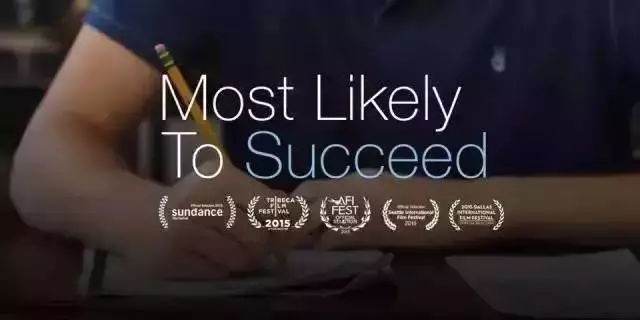“书堆里长大的孩子,语文成绩却不好。”
这是张佳面临最多也最不想解释的质疑,女儿在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绘本馆中泡书长大,她比谁都明白,孩子得到了多少书籍的滋养……可是——
“如果语文成绩不好,阅读有什么用?”
这是大部分家长惯有的逻辑:学奥数,为了数学能力变强;学英语,为了能和外国人沟通无障碍;多读书,为了语文成绩变好看。
“成绩,真的是唯一答案吗?”重庆咕噜熊绘本馆走到第7年,张佳陷入更深的教育思考,她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这座由分数、标准答案、小升初、培训班、竞赛等堆砌成的教育工厂里,一点点剥离掉自己的独特性。她的孩子苗苗,那个笑起来照亮所有人的小太阳,似乎有了心事。
内心丰盈的小诗人
在张佳记忆里,苗苗是个小诗人,2、3岁就能说出稚嫩又诗意的句子。
比如,妈妈刚讲完《巨人和春天》——春天娃娃穿着绿披风,转头,苗苗脱口而出说:“春天娃娃也穿着粉红披风。”苗苗领着妈妈来到小区里,小手指着远方,那里一树树桃花,晕红了眼。
和爸爸的对话也常常诗意暖心。出差回家的爸爸问:“你猜爸爸哪儿想你了?”苗苗背着小手,一副小大人的模样,“爸爸的眼镜想我了,因为爸爸只有带上眼镜,才能看得清我;爸爸的胡子也想我了,因为爸爸亲我的时候,胡子会扎到我。”
那一刻,苗苗爸爸冒起了幸福的泡泡,他欣喜着女儿有着他说不上来的答案,这是成人思维里没有的答案,更是爸爸想要保护的答案。
这美好的一切,和张佳的教养方式密不可分。
2007年,苗苗还是胎宝宝时,张佳就开始为她读故事,那时,她心里就存了一个疑问:到底,该给孩子怎样的故事呢?
从教育报辞职后,张佳带着这个疑问跑遍了全国的书馆,直到遇见“咕噜熊”,这个以台湾原版绘本为特色的绘本馆,让她深深着迷。
“只为更精准的翻译和更美好的语言。”
2010年,重庆第一间绘本馆——咕噜熊绘本馆迎来了第一位小读者苗苗,张佳无比心安地看着女儿沉浸在书海。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她精心挑选的台版绘本,初期30万元的投入,大部分用来采购每本100元左右的台版绘本,为女儿,为阅读,为更多孩子读到好书,值。
绘本馆陪伴着苗苗成长,张佳常常拿出台湾译本和大陆译本对比着读给苗苗听,让她感悟语言的奥妙,不同表达给人带来不同的心灵感受。
苗苗的表达力突飞猛进,连吃饭也会不时冒个小短句,“手是最智慧的汤匙。”张佳至今忆起,都忍不住赞许那个听风说雨的小苗苗,“说得多好啊!”
和标准答案硬碰硬
可苗苗的语言创造力竟在上小学后一点一点消失,让张佳没想到的是,学得多看得多,竟成了女儿学语文的障碍。
冲突常常始料不及。
一道形容蝈蝈叫声的原文填空题,标准答案是原文:蝈蝈的叫声像一曲音乐大合奏,苗苗却这样描述:蝈蝈的叫声像一曲丰收的歌。
“多美的诗句啊,劈头盖脑迎来一把大叉。苗苗问我为什么,我只能说这道题是让你抄写原文。”苗苗很不解:“那多无趣啊。”
而更多冲突,张佳也无法解释。
一把把大叉打进了苗苗的心里。不管多努力,语文成绩也就80分上下。有一段时间,苗苗考语文前还会极度焦虑,睡着后也频频醒来。张佳的焦虑,也蜂拥而至。
苗苗学语文变成一个扭曲的莫比乌斯环。常常是这样:日常学习—成绩不佳—张佳着急,考试加压—苗苗无所适从—张佳减压—日常学习。
周而复始,无始无终。
你需要一个标准孩子吗?
难道是教育方法出了问题?
张佳把苗苗的语文试卷发给一些教育专家,得到的答案是:苗苗拥有不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语文成绩不好不代表语文素养不好,苗苗只是没有找到方法去应付标准的考试答案。
找到方法应付考试,这个说法,让人沮丧。
和张佳一样,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给孩子自由,希望他们成为特别的个体。但这种理想的教育方向与现实发生着强烈碰撞——考试和升学。这些在台面上不断弱化的字眼,仍无时无刻不在隐隐作祟。
再开明的家长,也忍不住填满孩子的课余生活,多报了几个补习班和兴趣班。一位媒体人这样评价:小孩的教育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家长的“密集恐惧症”。整个族群密度太大,生存空间太小,大人很焦虑,把这种压力都放在孩子身上,要提早开发,尽量开发。
中国孩子没有太多退路。
就像美国家长可能会说:“我最亲爱的女儿将来做医生,那她们是我的医生女儿。如果她们将来去卖冰淇淋,那她们是我卖冰淇淋的女儿。她们开心就好。”
但到了中国家长这里,难免会演化出现实路径:“如果你去卖冰淇淋,当医生的同学到你这来买冰淇淋会笑话你!努力熬过读书阶段就好了。”
还能怎么办?“熬”成了读书阶段的群体画像。为了减少苗苗的煎熬感,张佳把学习拆分为两个体系:一个专用于考试,另一个用于日常生活和兴趣学习。
“可仍旧感觉到孩子的想象力在被吞噬,成为一个标准的孩子。”不久前,苗苗还玩笑:如果考课外知识,她一定是班级第一名。
第一名是社会或学校的标准,也慢慢成为了孩子的标准。
教育的边界在教育者
为何要教育标准的孩子?
Aha学院创始人顾远在11月的“听道讲坛”上分享了近期备受关注的纪录片《极有可能成功》——
导演带着观众追溯了一遍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的起源。
原来,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现代教育制度不过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这种制度最早诞生在德国,那个时候还叫普鲁士,设计这个制度是为了给普鲁士培养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士兵。到了19世纪晚期,一些美国顶尖的企业家到德国取经,把这个制度复制到了美国,为美国的大工业生产输出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
了解了它的起源,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这种教育制度如此地强调统一和标准化:统一的入学年龄、学生要按班级、年级统一划分;学习要按不同学科统一划分;学校要使用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课表、标准化的考试。
顾远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陈丹青在清华美院当教授,上午教油画课,下午想去看看学生画得怎么样了,结果去教室发现一个学生都没有了,因为下午课表上排了别的课,学生放下画笔跑去上那些课了。陈丹青气坏了,因为画油画是不能这么中断的,画布上的颜料干了,这画就没法再改了。这种课程安排完全不符合学习油画的实际情况,而在这所艺术院校,在陈丹青之前居然没有任何人指出来过。
教育者的教育视野,是受教育者的最大边界。
教育的真正改变在于教育者自己的思维方式,就像前任北大校长蒋梦麟说的那样:教育是要培育出一个个活泼泼的人,而不是标准产品。
张佳把顾远的讲座内容分享给了很多人,希望更多家长能拓宽自己的认知边界,因为家长也是教育者,是影响孩子最多,最有希望带给孩子去标准化教育的人。
只有教育者的改变,才能带来教育的革新。
极有可能成功
家长们在寻找新教育的路上,一刻不停。
有条件的,迁徙;条件不够的,自己创造一个理想国。
先去看看,那群迁徙者的其中一个教育目的地吧。
在《极有可能成功》纪录片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学校。
学生围绕各个主题开展不同的项目式学习。项目如何设计,如何实施,项目团队如何组成,谁来做项目团队的领导者,这些都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老师的作用是搭好 “脚手架” ,在孩子们有需要时给予支持和鼓励,而不是让孩子们按照老师设定好的步骤和规矩去完成项目。在这个过程中,会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变化。
有一位女生,在影片开头的时候非常羞怯,不自信;在项目团队里,她决定挑战一下自己,主动担任领导者的角色,老师和同学都提供了信任和支持;随着项目的开展,我们会看到这个女生的成长变化,她开始变得越来越开朗自信,她在享受学习的自由和成长的快乐。学习结束时,她对老师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永远只会是一个追随者,现在我发现自己也可以是一个领导者。”
就是在这样一次次基于学生自主权利和自由探索的教学实践中,孩子们学会了制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学会了在和他人协作的过程中主动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学会了选择、学会了负责,学会了终身学习的能力。
最终,找到通往成功的各种可能,成为真正的自己。
标准化的教育正在逐渐退场。没有离开故土的新教育开拓者,也已经做出了成绩,比如一土学校、探月学院。
一土教育联合创始人李一诺说:在聚集着2000多万人口、名校林立的北京,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在没找到合适孩子的学校的情况下,她果断决定和丈夫一起,自己办学校。她将学校的课程体系概括为“骨骼(国家教学大纲)、肌肉(特色教学方法)、灵魂(个性化培养、内驱力激发)”。
探月学院,一所已在北大附中落地的学校,做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定义学校。探月学院的教学目标是:“在未来社会中,持续追寻独特的自我价值,敢于深入各种挑战与未知,拥抱变化且始终保持开放,并用行动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这里更像 Google的办公室,师生一起沟通、协作,共同完成一个个项目。而探月学院的教师,比如前阿里巴巴品牌营销经理跟学生分享“BAT是如何利用大数据实现科学算命”,剑桥大学物理化学博士教学生“重新设计一堂科学的科学课”。
这只是新教育,或者说未来教育的一角,虽然,大部分家长不敢赌上孩子的18年,但你看到他们的努力,蓬勃,依然欣喜,因为这正是你梦寐以求的教育。
“人生以后的历程,只不过是前面14年所阅读的东西的展开。”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恳切地说:“孩子早期的经验对成长非常重要。当他们成人以后,他们是用孩提时代所获得的东西为根基,继续去构建内心的成人世界。”
看到这里,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张佳也相信之前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孩子的根基在,内心依然丰盈。现在,她把创造孩子的多种可能设为新目标。她正深度专研阅读教育和教育戏剧,以教育者的身份,给苗苗和更多孩子带来成功的多种可能。